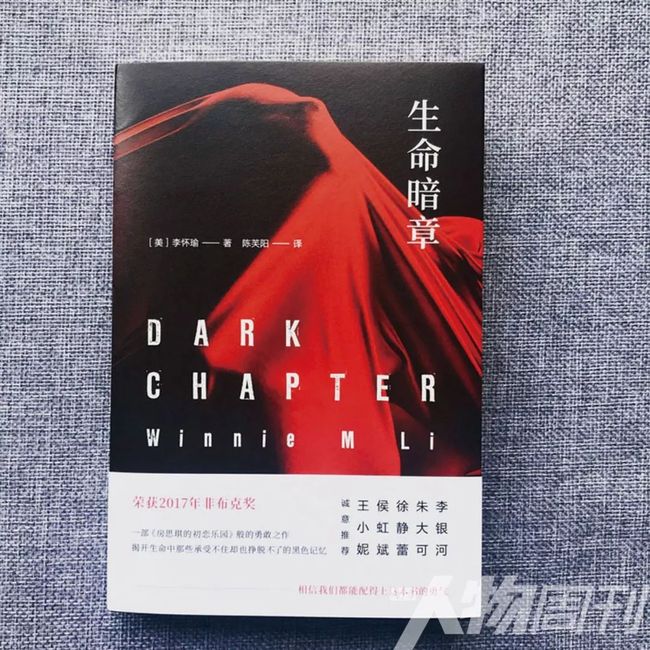遭受性侵的她胜诉了,然后呢?
法庭上的胜利或许能用简单的一纸判决分清黑白,心理上的伤口,却需要长年累月的修复和疗愈。
“痊愈是可能的,它不会瞬间发生,但在将来某个时刻,生活会变得更好。我已经做到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至于要不要向他人透露自己的创伤完全取决于你,你不必把它告诉所有人,并且维护你的隐私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自己”
《生命暗章》作者李怀瑜
伊藤诗织胜诉后,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着两张照片:第一张是伊藤诗织在法庭外,手持“胜诉”大字的白纸;第二张,则是她一身职业正装、冷静地出席记者发布会的场景——她所状告的性侵者山口敬之败诉后召开媒体发布会,而伊藤诗织正以记者的身份端坐于台下。
无独有偶,11年前,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位叫李怀瑜的美籍华裔女性,面对性侵,也选择了站上法庭。
李怀瑜的人生本在人人欣羡的既定轨道上运行:哈佛毕业、在电影产业崭露头角,只是因为一次爱尔兰贝尔法斯特郊区的山间徒步,一个15岁的强奸犯,给她的人生按下了暂停键。
李怀瑜在事件结束后第一时间报警,接受了一轮轮冰冷的取证调查流程,接受心理辅导、服用紧急防艾药物,与袭击她的强奸犯在法庭上当面对质,最终胜诉。
但胜诉之后又如何?
法庭上的胜利或许能用简单的一纸判决分清黑白,心理上的伤口,却需要长年累月的修复和疗愈。
这画面何其熟悉——两年多前,林奕含留给世界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描摹过一位长期被狼师性侵的女孩的内心,那是一片千疮百孔、荒草丛生的泥泞之地。
在类似的精神洼地里,李怀瑜也试图用文字自我救赎——胜诉后,李怀瑜依旧在挣扎。在挣扎中,她以这段遭受性侵的自身经历为基础,写了一本虚构小说,名叫《生命暗章》。
或许比林奕含幸运的是,李怀瑜在长达几年的暂停后,得以重新为自己按下启动键。在书中,她甚至跳出了作为受害者的第一人称视角,以双线结构编织全文,站在性侵施害者的角度,搜集资料、采访,再通过想象书写对方的成长背景与心理。
文字之外,李怀瑜还是行动者和社会创变者。她体认到文字、艺术的疗愈作用,创办Clear Lines Festival艺术节,鼓励用艺术创意项目公开探讨性暴力议题;她选择实名接受媒体采访,登上TED演讲的舞台,试图扭转一贯软弱的性侵受害者形象,告诉公众关于性侵,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除了事件本身带来的伤痛外,公共机构面对性侵的反应机制的滞后、心理援助体系的不完善、媒体舆论的标签化倾向等等问题,往往带来二次伤害,却甚少引起社会真正的反思和体制性的改变。
在此之前,走在各自心理深渊里的人,只能踽踽独行,自我拯救。在《生命暗章》里,李怀瑜这样描写胜诉后的日子:
“慢慢地,她开始有了新的例行公事,虽然少得可怜,但已近乎日程表,这似乎支撑了她空虚的存在。
……
她翻到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她听过好几次这首曲子,想起在新泽西教会礼堂弹奏它的那位钢琴演奏家,当时那些音符是那么诚挚和哀伤地流泻出来。如果她可以学会像那样弹奏,那么她的人生就不会是全然的浪费。
几天之后,她学会了一页半的第二乐章。
瞧,这就是进展。
她不再感觉自己是那么凄惨的失败者,不再感觉完全被夺走了旧有生活。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她还是拥有这一切,拥有这一切。”
《生命暗章》作者李怀瑜在书店与读者交流
“在这所有的报道中,我自己的声音在哪里呢?”
![]()
Q:防范性犯罪是一个社会结构性问题,除了性别权力结构之外,性侵发生的权力结构还涉及阶级、等级、职业、年龄等等,通常是利用位高权重者对位低者的权力压制。你认为造成性侵的结构性问题能改变吗?强调改变媒体、公众对性侵的言说方式,能在哪些方面、什么程度上起到预防或改变的作用?
A:只要存在结构上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差异,就会有潜在的性骚扰或性侵犯等不当行为。不幸的是,这些权力差异广泛地存在于家庭、社交圈、工作场合,如教育机构和工厂中。我们可能无法改变这些机构的架构形式,但可以制定并执行举报性犯罪、相信和支持受害者以及追求正义的程序。
在媒体的报道中,为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她的姓名常常被抹去,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密码——公众对此的想象总是认为她们的生活被毁了、或她们无法谈论强奸。事实上,受害者和幸存者都是可以亲身讲述她们的经历的。因为北爱尔兰有很多关于我被强奸的新闻报道(在报道中,我总被描述成一个中国学生或中国游客),我禁不住想:在这所有的报道中,我自己的声音在哪里呢?这也促使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书写自己的声音。
媒体在报道性暴力案件时需要非常谨慎。他们需要认识到:他们以某种方式刻画受害者时的字眼可能会给受害者及读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在媒体报道中描绘施暴者也是如此,受害者与施暴者在媒体中的形象可以强化公众对性暴力的刻板印象和误解——比如说,哪种女性被强奸,哪种男性是强奸犯。
Q:你在《生命暗章》中提到,受到侵害后你第一时间向执法司法机关、医疗机构寻求帮助,但通过你的文字描述,似乎能感受到你对社会公共系统处理性侵的方式不满意,它显得冰冷而不近人情,缺乏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追求执法效率、人手不足也是现实。你认为在应对处理性侵事件上,社会公共健康系统最核心、最急需的改变分别应该是什么?
A:经历过强奸之后的人生非常艰难。我得到了一些公共服务部门(如警察)出色的照顾。但是在一些部门中(如强奸危机中心和医院)也有过不太好的体验。在许多国家,服务质量会因受害者的居住地有很大的差异,而受害人的康复能力可能会因服务质量而受到影响,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所以这些服务绝对需要改进——但它们往往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往往认为这些服务不重要。事实上,它们的存在对受害者的恢复与治疗至关重要。社会首先需要了解强奸影响受害者各个方面的多种方式。其次,我们的公共服务需要提供给受害者康复的资源,并且使他们方便地获得这些服务而不至于感到羞耻。
最重要的改变是需要去倾听受害者——不仅仅是给予他们信任,并且珍视他们的经历,作为一种专业知识的来源。受害者可以指出公共卫生系统中的缺陷。公共卫生系统应该尽其所能地改善受害者的康复和资源。
Q:《生命暗章》里,对施暴者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心理过程,你的写作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完成的?对“漂旅人”的想象是否以实际的资料或访谈作为基础?如果有,介绍一下具体搜集资料的过程。
A:如果没有Johnny(书中的施暴者)的视角,这本书将会完全不同,我的兴趣也不会这么大。通过以富有同理心的方式书写Johnny,我尝试着打破我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是性侵幸存者的思考边界。我们的社会需要去思考:施暴者也是人类,他们并不是怪物。是他们的经历、教养、性格等造成了他们的性暴力行为。如果我们不愿意尝试着去理解那些促使他们变成施暴者的因素,我们将永远无法避免这类性暴力的发生。
除了他的年龄、家庭背景等,我对施暴者现实生活中的细节一无所知。因此,我将这些事实用作概述,试着去想象其他的部分,以充实Johnny这个立体的角色。我也对“漂旅人”社区(爱尔兰的游牧社区,Johnny来自于此)做了一些研究,参加他们的聚会,和当地的社工交流。另一种研究领域是少年犯与少年性暴力的罪犯,这也意味着我要与法医心理学家、社工、和犯罪青年一起工作的缓刑官员交谈。
李怀瑜在伦敦TED演讲现场
“消除受害者可能会感受到的耻辱”
![]()
Q:想象和书写一个曾带给你巨大伤害的人,最初有感到不适或难以下笔吗?如果有,这个心理障碍是怎样克服的?在TED演讲中,我很惊讶地注意到你用了“my 15-year-old rapist”这样的代称。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词来代称施暴者?你在心理上经历了怎样的语言抉择和纠结过程吗?这是否意味着你开始逐渐接受这件事?
A:我使用“my 15-year-old rapist”这样的代称是因为这就是事实:我被一个强奸犯强奸,他那时15岁。这也表示强奸犯可以很年轻,我认为没有理由用更委婉的词语来描述这些事实。对我而言,我宁愿说自己被强奸了,而不是被性侵了,因为后者包含了可能发生的一系列行为,但是掩盖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现实和它的严重性。使用语言精准地描绘真实是一种力量。而且,当我是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时,我为什么要因为真相而感到羞愧?
Q:你提到这个社会之所以不能更公开地谈论强奸和性侵,和社会建构的羞耻感(Sense of Shame)相关。你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其实是一次公开谈论和探讨的尝试,但这对你来说一定也是一次痛苦的蜕变。写作、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你觉得自己被哪些羞耻感裹挟过?
A:不,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好羞愧的,那并不是我的错。事实上,变成强奸案的受害者仍然让很多人感到羞愧,这点太糟糕了,因为强奸发生的唯一原因是施暴者决定这样去做,而不是因为受害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因此,唯一应该感到羞耻的人是施暴者,我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试图消除受害者可能会感受到的耻辱,并表明我个人,作为个体,并不为我的遭遇感到羞耻。而且,我也愿意在电视媒体、舞台上去谈论我的遭遇。
Q:现在你的父母已经知晓了你这段经历了吗,你是何时决定让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后的反应是?你和他们的沟通过程是怎样的?
A:我等了三年多才告诉父母我的遭遇,因为我不想给他们施加压力、带来痛苦。而且,我住在伦敦,他们住在加州,所以我知道他们在帮助我康复方面不能做什么。如同小说中的薇薇安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疗愈方式是在朋友的支持和自己坚定的信念中获得力量。
我的确知道很多受害者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父母,但是父母对他们的遭遇的反应和反馈(“你本可以避免”的这种评价)其实又一次伤害了他们。
我最终决定告诉我父母时,其实生活已经重建得差不多了。我在新的国家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也在选集中发表了关于我遭遇的文章。所以,我可以十分有底气地告诉他们:“这件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但我现在感觉更好了。”我觉得父母感到震惊,因为我向他们隐瞒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如此可怕的经历(可能自责他们没有察觉),但同时也印象深刻——我用自己的能力痊愈了。他们现在应该很自豪,因为我有了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正在努力重塑社会对性暴力的看法与受害者的形象。
痊愈不会瞬间发生,但在将来某个时刻,生活会变得更好
![]()
Q:《生命暗章》的存在是一种女性声音和经验的证据。在中国,出版社将它与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相类比。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或其他类似主题的文本?你认为这种女性经验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知识”(knowledge),会有怎样的意义、能对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不同文本的个体差异性体现在哪里,它们的价值又是什么?
A:有很多书籍都在探讨强奸。我想到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的小说和短篇小说。她擅长将悬念与性别政治和性暴力的社会学探索相结合。
也有其他的幸存者写了出色的“强奸回忆录”,这些作品在我被强奸后的第一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南希·文纳尔·雷因的《沉默后》、爱丽丝·塞伯德的《幸运》以及最近的乔安娜的《我会找到你》)。如果我写另一本关于强奸经历的回忆录,也许对这个领域不会有什么新的贡献。因此,我真正想探索的是一个年轻作恶者的性格,写出他的观点,并将这个故事与受害者的故事交织。那是我只能在小说中做的事,因为现实中强奸我的人与我完全是陌生人。书写Johnny的视角对我来说是相当有创意的尝试与飞跃。如果说,薇薇安的经历与我的类似,那一部分的写作不需要太多想象力,那Johnny部分的写作完全靠我的想象力。此外,把他们写成小说也给了我自由核对材料的控制权,在我完全感受不到自己是受害者的情况下,写作赋予了我权力。
很多读者和评论家认为Johnny的视角是《生命暗章》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成就。对我来说,承认这些罪行的普遍性同样重要。它不仅仅是关于强奸案中薇薇安和Johnny的故事,还有其他幸存者与施暴者,他们同样需要被倾听与认可。
Q:你反复提到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你的人生,但通过你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时间推进,你感知到的“改变”也不断变化,我相信它有越来越丰富的层次和含义。时过十年有余,你认为它最深刻地改变了你人生的什么?它对你所造成的创伤是否依然存在,还会体现在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A:最近,如果谷歌我的名字,他们会自动检索出我是一个强奸案的幸存者。在公共场所,这种创伤总是与我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因此,我想这改变了其他人最初对我的看法——但同时,他们也看到我是一个作家和行动者,我正在做一些事情来解决性暴力问题。
专业点讲,我的生活完全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轨迹:在公众视野中,我被与反对性暴力的倡导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我仍然像在我走入公众视野之前那样尽力地讲故事。同时,我和以前一样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电影、旅行等活动的热情。但我工作的公共性也给我带来了新的机会、联系和一种新的责任感。
过去几年,我对创伤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我不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随着我的生活不断发展,那些可怕的经历也不再具有那么强的创伤。我更自在、镇定和自信了。但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增长的原因,毕竟距离创伤发生已经11年了。我不太担心一些细微的事,毕竟我已经经历了更糟糕的事——与这个相比,其他事显得也不那么可怕了。但我必须强调,在到达这个状态之前,我经历了漫长的治疗与康复。
Q:你勇敢地袒露了自己的创伤经历,但出于各种原因,许多受害者依然会选择沉默,或决定带着秘密度过人生。对于这些人,你最想告诉他们什么?
A:首先,你不是一个人。遭遇强奸后最困难的事之一是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实际上,有很多受害者与幸存者。另外,这并不是你的错。有错的是施暴者,还有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错。最后,痊愈是可能的,它不会瞬间发生,但在将来某个时刻,生活会变得更好。我已经做到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至于要不要向他人透露自己的创伤完全取决于你,你不必把它告诉所有人,维护你的隐私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自己。
*本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ID:Peopleweekly)已获得转载授权。
END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如想取得授权请联系原公号。如果想找到小南,可以在后台回复「小南」试试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