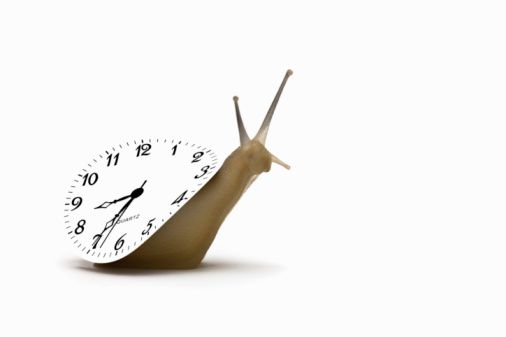文/韩大爷的杂货铺
1.
大学期间的辅导员老师,我们叫他超哥。
才华横溢,嗓音好听文笔过硬,做过省学联主席,各种场合出席无数,却挑不出一次毛病。
相貌英俊,可谓玉树临风,不知迷倒了多少学姐学妹,人中吕布。
以上都是后来的印象,刚入学那会,我可不这么想。
家来自农村,借着升学的机会第一次跨进省城,心里除了对周遭事物抱持着一种新奇感之外,也对一些从前未曾目睹过的处世方式不甚理解,乃至嗤之以鼻。
就拿超哥来说,你见他如此出众,却一丁点傲气都没有,跟学生讲话也是客客气气,极尽温柔体贴之色。我素来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人无完人,形象越是高大全,就越可能有不堪的一面。
顺着这样的心境去考量超哥,目光便也更加刁钻挑剔。皇天不负苦心人,终归还是被我人为地总结出些破绽:柔韧有余、魄力不足、注重细节可以看作斤斤计较、礼数周到可以判为矫情虚伪,缺乏男子气概。阿Q先生的遗风帮我重新找回心理平衡。
再见他常将“请”与“谢谢”挂在嘴边,心中不禁暗忖:谢什么,真够酸。
再见他与谁打交道都是和善得紧,也自顾自地挖苦道:我们的绅士又出门了啊,收买人心。
时值寒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学院的几个老师下班后要将一些办公桌椅抬往别处,人手不够,邀我凑数。
一阵折腾,终于干完,手脚已是木涩僵硬,脸也露在外面,表情便冻得更僵。
其他几位老师取暖过后,渐渐焕发神采,彼此聊天打趣,满屋子除了我这块方圆外,尽是快活的空气,我便更加尴尬些,遥望着那个圈子,不知如何存在。
超哥走过来端给我一杯热茶,坐在我对面没话找话。回想那时的我,对于假惺惺的同情素不买账,便狠心决定要用揶揄的眼光死盯着他的笑眼,看得他不自在为止。却不料升腾的蒸汽每每遮住我这顽劣的视线,他的面庞也愈发朦胧起来。
敷衍了事后,我起身要走,几米外的圈子仍是欢快得很,并没有人意识到或者想要意识到我的离开,行至门口,超哥高八度的嗓门叫定了我的名字。
我本能地回过头去,又撞见他那和善的目光,但全然没有防备,已是来不及冷眼相对了。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又将我的名字结结实实地念了一遍,中间停顿片刻,仿佛在等着其他人的注意力塞进来。安静的空气再度被“辛苦”两个字划破,转瞬便又恢复了安静。
我说声“没事”,抹身移出门外,下楼时猛然意识到自己上扬的嘴角,心里才知道已被他圈粉收买。
2.
大学二年级,为补贴生活开销,寻了一份拼脚力的活计。
天气寒冷,宿舍楼内学生们连取外卖的心思也省了,周边商家看准需求,雇佣外卖人员将饭菜直接送到每间宿舍的门口床前,我就干这活,一月九百块。
起先确实低估了艰辛程度,料想每天都有人把几盒子饭放到楼下,我下楼去取,然后再跑到每个宿舍一扔即可。
干了几天才体会到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挑战:不仅饭口有人订餐,基本上全天任何一个节骨眼上,这楼内都会有某一个饿的难受,打通电话;而且从一楼到七楼也比想象中远很多,像个滚刀肉一样循环往复地跑,让我总算明白了劳动人民为什么对诗词歌赋兴趣不大,因为没时间想。
每天在楼下与我交接口粮的同事是一位打工多年的老大叔。本同处于一片天地,他指甲里有泥而我没有,这仿佛成了一段跨不过去的距离。
格格不入的感觉让我们斗了几天,每逢他打电话喊我下楼拿货,都没个好声气;我投桃报李,见面时也是怒目而视,用粗鲁的肢体语言展现我的入乡随俗。
楼下的气氛让人窝火,楼上就更不怎么样,嗷嗷待哺者们确是把我当做了专业打工仔,一次找零时出了差错,竟脱口而出道:没上过大学到底是不一样。
当时我见这位同窗那不可一世的姿态,心中竟生发出一种惭愧,眼前立着的昏聩小儿,仿佛就是我自己。
自那以后,每逢与指甲里有泥的大叔交接货物,必要道声“谢谢辛苦”,冰雪封路时还要嘱托一句当心脚下。开始大叔尚不明所以,用蛮怪的眼神望着我。日子久了,他也竟儒雅起来,见我飞也似地朝他奔来,往往会摆摆大手,喊声“慢点”,再见我飞也似地离他远去,也会追加一句上楼小心。
打工生涯的最后一日,恰逢参加学院内的演讲大赛,事毕后知道饭点已到,将获奖证书揣在怀里往回奔。行至楼下,大叔已等候多时,见我西装革履,退了半步,又将饭菜递给我,报了门牌号,临走时只说声:人还是那个人,换了身衣服怎就这么气派。
我想前半句是对的,也是错的,便不禁认真地看了他一眼,道了声谢。
皮鞋踏在楼梯上噼啪作响,无巧不成书,我最后一次送的饭,竟还是交到了那位高傲同窗的手上。饭盒与衣衫是如此不协调,搞得他也犹豫起来,不知将眼睛放在饭盒上还是衬衫上。
“你……你也是这栋楼的……学生?大学生?”
我找好零钱,没有回话,下楼走向自己寝室时想着:以前还担不起这个名号,现在已确定是了;但你未必。
3.
每逢过年,父亲总要拿起手机,逼着我挨个给远亲近邻,老师朋友们拨电话,道声好,问个安。
这个流程太过煎熬,父亲与我的处世哲学颇有出入,他是有一说十,我是木讷愚钝,总想着话不可言尽,心里有就好。我和他因为拜年电话的问题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口角。
母亲往往是父子关系最好的斡旋者,她的话更入耳些,见我满肚子不快,劝导我说:打一打是有好处的,感情在于维和。
我不信:实在没什么必要,知道你有这份心的人自会知道,不知道的就让他们不知道。
母亲耐心地笑着,缓缓地说:可人就是这样吧,你不说,他们几乎永远都不知道。还是得说的,还是要说的,多一句,就很不一样。
我抱定此宗旨执行了几次,中间也遇到些坎坷,许久不联系的谈话对象,确实聊起来生疏得很,有时说几句寒暄的话,就卡住了,再没下文。
我想就此作罢,挂掉电话,母亲连忙在一旁挥舞起她那厚重的手,示意不要。我无奈一笑,用唇语跟她讲: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
母亲先是一笑,爱怜地瞧着我,手指略微卷曲,瞧瞧自己的脑袋,她是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我沉下心来,只好挖掘与通话对象的一些人生交集与共同经历作为谈资,哪知本是用来搪塞时间的废话,却越讲越有了生趣,电话那头的甲乙丙丁,一开始也尴尬地笑着,不出片刻,话匣子也缓缓打开。我甚至能切肤地感受到:每当我讲起我们之间发生过一件小事,电话那头惊喜的神色,与拍在大腿上的欢快手掌。
聊至兴起,讲起有一些被倒腾了很多年的拜年话,竟也平添了几分重量,谈及人生相遇,彼此感怀时,也是双向的恩谢。
我挂掉电话,心满意足地看着窗外,鞭炮齐鸣,欢笑架天响。
吃过饺子,陪家人说了会话,闹至凌晨,和衣入睡。
火炕在凛冽的冬日升腾起层层温暖,双目并拢, 心知又长进了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