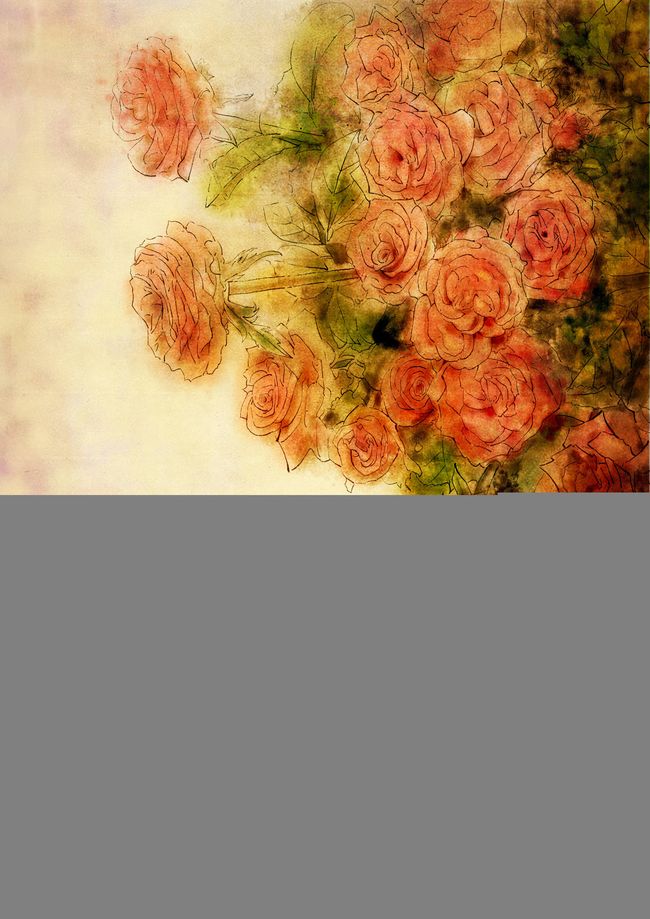如果他年轻10岁,我会主动追他。看着他的睡颜,我冒出这个想法。
大学里某个寒假回家,在武汉转车。逼近年关,又在学生放寒假的时间点,武汉是大站,上车时已是深夜,车厢里却还热闹着。
我拖着行李箱,抓着捂到嘴的围巾,吭哧吭哧地挤上火车,找到自己的床号,然后小心翼翼地避让身后要再往前走的人。一拖一挤一用力,憋得我直冒汗。
等过往的人少了,我甩甩胳膊准备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刚脱了大衣撸起袖管,身后就传来一把极富磁性的男声,“来,我帮你。”
我转头,视线只平及那人的肩膀。以我的身高作参考,目测那位同志,呃,姑且称为C先生吧。身高在185上下。我一抬头,有种艳遇之感——好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阔眉高鼻,一圈淡青色的胡渣,就是老了点。
他轻而易举地把我装了半箱衣服半箱书的行李放上去,拍拍手,说,“你把大衣穿上,要着凉。”
我点头致谢,顺带观察了他就睡在我下铺。
车上信号不好,上网什么的不方便,只能听歌看书侃大山。我就拿手机坐在窗边看电子书。
C先生从贴身的电脑包里拿出一本书,腰背笔挺地坐着看,我偷瞄了几眼,想看看是什么书,不慎被C先生发现了,笑着把书封翻给我看——是毛姆《人生的枷锁》的下册。我之前看过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喜欢得紧,没曾想车上竟能碰见志同道合的——还是个老男人。
他问,“你在看什么?”
我说,“木心的《素履之往》。”
他合上书页,慢悠悠地背木心的《从前慢》,只背了已经烂大街的那几句,但不疾不徐的低音炮,背来相当好听。背完,他说,“就会这么几句,倒是喜欢。”
我说,“难得。很少有男生喜欢读这些书的。”
他说,“我爱人喜欢,她是大学老师,教文学的。”
聊了些有的没的,言谈中能感知他很博学,也有很丰富的人生阅历,跟这样的人聊天总是愉快的,得到的感悟和经验会比读书来得更快。
销售人员推着零食小车和夜宵,每半个小时就过一次。他买了两瓶水,然后说“谢谢”,这让我对他瞬间有了好感——对服务人员的态度能看出一个人的教养——此言非虚。
他拧开其中一瓶水的瓶盖,递给我。他一边喝水一边打电话,拨给他的夫人,问女儿睡了没有,大概那边回答没有,换成了他女儿接电话。不知道小姑娘几岁了,精力旺盛得很,我隔着近两米都能听到她欢腾地叫“爸爸”。
C先生问她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再问她的学业功课,最后柔声哄她睡觉。
你能想象那场景吗?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大高个儿,坐得笔挺,在深夜的火车上温柔地哄电话那头的女儿睡觉。他的眼神落在刚买的水上,一只手捏着瓶身,眼里无比深情。
同样是父亲——有的父亲是这样,而有的,是别样。从头到尾看着那一幕,我不自觉地带了笑,一种苦涩的羡慕。
C先生看了我一眼,我因偷窥被发现的窘迫感迅速躲开视线,他继续打电话,没两分钟就挂了。他问,“吵到你看书了?”
我摇摇头,略微尴尬地脱鞋爬到床上酝酿睡眠。
彼时我患有严重的入眠障碍,有一点光亮一点响声都睡不着。火车摩擦铁轨哐叽哐叽的声音在夜深人静时格外刺耳,躺在床上固体传导的声音更大。我裹了大衣下床,坐在窗边继续看书。
C先生在下铺,靠墙坐着挂着耳机,也还没睡。不便说话,便相互点了点头算是心照不宣地打招呼。
凌晨两点多,我脚也冰透了,还是睡不着,整个人蜷起腿裹在大衣里发愣。C先生移到床头来,戳戳我的胳膊,然后拍拍他的床铺,用气声说,“咱俩换。”
我摇头,他遂把被子扔一截给我,形成一种奇异的造型。他坐在床头,身上搭着三分之一条被子,我坐在窗边,腿上盖着三分之一条被子,还有三分之一的被子遮着床与座位之间的过道上。
看书看得久了,蜷得腿发麻,我搁下手机揉眼,打算走动一下。他合眼靠在床头,不知睡着没有。我蹑手蹑脚地将被子放回他床上,走到两节车厢的交界处活动,有风往里灌。那地方也有睡着的人,铺了纸皮,就那样睡着,洗手池也有人睡着。
我靠在其间,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卫生间的冲水声。C先生出现在身后,刚洗了手,还在甩手上的水,我报以疲倦一笑。他脱下羽绒服,披在我身上,说,“早点睡。”没等我拒绝就转身回去了。
我裹紧衣裳,眼前都是熟睡的人,看着看着也生出一两分困意,赶紧抓住时机回去睡。C先生已睡着,我将他的羽绒服轻轻铺在他的被面上,心中陡然生出暖意。
我喜欢博学幽默的男人,更喜欢这种因为内心强大而对身边的人生出一种体恤式温柔的男人。
我下车时他还没醒,窗外有薄雾,似乎没必要跟他道别,我请乘务员帮忙取下行李,然后等车靠站。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他当过11年兵,军官,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