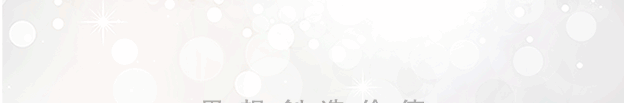“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个“伪命题”
首先,我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即“国家业态”的概念。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国家的谋生之道!我把全世界的国家分为了四种业态:英美为代表的消费需求型为主的国家业态;德日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为主的供给型国家业态;中国为代表的混合型国家业态;和其他资源型为主的国家业态:资源型为主的国家位于最低端,它们往往会成为历次经济危机中被剪羊毛、宰割的对象。
英、美消费需求型业态国家主要是依靠铸币权、金融、资源定价权、规则制定权、话语权等为主来谋生,即所谓的第三、第四产业的大部分都是依靠上述工具和手段支撑而建立起来的;德、日主要依靠高端制造业的供给为主来谋生;中国随着亚投行,“一带一路”的发展,将会是前面两种业态均有的“混合型”业态国家;其他国家则多为资源型国家。
因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向和目标将会是:实现国家业态向更高端转变以及政府机制的改革创新。
具体来讲,一方面,在铸币权、金融、资源定价权、规则制定权、话语权方面向美英为代表的消费“需求型业态”国家转变。主要抓手就是以亚投行为引领的“一带一路”;另一方面向德、日为代表的更高端创新制造业“供给型业态国家”方向提升,向高端供给型业态国家迈进。这就要求在中国国内,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有各自擅长、侧重的竞争方向,并制定总体国家发展差异化、国际竞争性布局。而二三四线城市则要支持北京、上海、深圳来实现同美、英、德、日的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二三四线城市区域经济必须长期保持对东南亚、韩国的可替代性竞争力优势!而要实现这一切,政府执政层面的改革和创新支持是重要保障。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力、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陷入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仅有日本和韩国,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然而,在面对中国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再套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模型来解释就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中国的人口体量太大且地域辽阔、发展极为不均衡。有些地方,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城市。事实上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局部地区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而要让包括西藏、青海等的中国所有地区都进入发达经济体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国情是北、上、深、广为中心的经济体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与其在创新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领域展开竞争;而三、四线城市要始终保持对东南亚等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中国将长期是发达经济体、中等发达经济体、欠发达经济体并存并且逐步向上推进的模式!从而使得低端经济体模式支撑高端经济体模式,并保证在其失去竞争力时不至于衰败;高端经济体又拉动低端经济体长期保持竞争优势。
中国要按照“地域”同时保持对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永续发展而不至于真正掉入“人为的陷阱中”。因为,我认为,一个国家只要经济相对于全球在不间断地增长、前进并且就业充分就不会掉入任何所谓的经济陷阱中。而真正的陷阱是,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的停滞状态。核心问题不是软着陆、硬着陆,而是怕没着陆。都想搞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都想搞房地产、步行街的时候才会真正掉入“人为的陷阱”中。因此,整齐划一式的模仿、攀比是大忌!所以,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个“伪命题”。中国真正要面对的陷阱或者危机是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的危机:具体将会集中体现在“失业率”上。
为什么说“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个“伪命题”,我们首先来看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描述。2006年,世界银行在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说:“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中说:“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但它的前提:“由于缺乏规模经济”,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相符。中国不但具有规模经济,而且还被冠以了“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的引擎”而举世闻名多年。2010年,世界银行在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中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这可能是世行迄今为止最为准确的评价。
因此,我认为,世行的三个报告主要说的是,是否具有竞争力和能否实现永续发展的问题,而非经济发展与收入陷阱的必然性。而国内学术界在提到“中等收入陷阱”时会常常把它与收入挂钩,并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此相关联,人为地形成某种因果的必然性联系。况且,收入的高、中、低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还受到汇率变动和计算方法的影响,并且存在很大的相对性。更为重要的是:世行对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划分依据是“人均”国民收入(GNI),完全没有考虑该国的经济规模,发展均衡度和人口基数等极为重要因素。
例如,中国的北京、上海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已经完全达到甚至超越了很多高收入发达国家经济体,但如果说要让包括西藏、青海等全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者超越发达国家,整个地球可能都将承受不起!所以,我认为,对“混合型业态”并向上提升的中国来讲,“中等收入陷阱”必然是个伪命题。但对于拉美、中东、东南亚等国来讲,又的确是个真命题。因为,他们都属于我前面所说的较为低端的资源型业态国家。我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实现永续发展和超越,与该国的资源禀赋、国民智力、遗传基因、教育程度、勤奋程度、储蓄率等我前面说的“国家业态”以及政府能否确保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存在等因素直接相关联而绝对不是收入。
例如,假设德国现在从二战废墟中重新起步,哪怕从人均收入1000美元起步,也不会有人怀疑它最终会再次进入发达经济体国家行列,不会有人认为德国会步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除非德国出现了类似拉美、东南亚那样的腐败政府,使得它的各种优势禀赋发挥不了,或者难以实现。中国曾经保持了上千年的人类经济发展和文明的绝对领先优势,现在不过是向曾经拥有的上千年辉煌历史地位的自然回归,并且正以大踏步跨越方式实现着赶超式追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的智慧+注重教育+勤劳+高储蓄率。而唯一的阻碍就是和对德国的假设一样:出现类似拉美、东南亚的低效、腐败政府,从而让这种禀赋优势发挥不了或者难以实现。可见,我在前面提到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向和目标:“实现国家业态向更高端转变以及政府机制的改革创新”才是跨越各种陷阱的关键。同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如果不够准确、不够清晰,很容易将国家经济的重大决策引入歧途,从而使自己本该有的自信完全或部分丧失,打乱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
2015 年,我提出了国家业态概念和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个伪命题,之后我把《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向和目标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真伪》等论文寄给了北大厉以宁教授等多名经济学家,2017 年我看到厉以宁教授公开发表文章说: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有关系!我始终认为,如果中国真正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话就不可能完成中等收入人群倍增,难道是要在陷阱上实现倍增吗?
跳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就是实现国家业态的跃升。要知道,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所换取的美元、美债,只是一张张美国政府的低成本“欠条”而已。向美、英、德、日看齐的同时,保持对东南亚、韩国的竞争力,这有赖于国家层面的整体布局,以及更深层次在教育、制度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下功夫!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有所放缓,但难掩其韧性、发展不均衡、规模等优势。中国经济潜力十分巨大,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很多重塑空间:它们是经济发展潜力的核心内容。发达社会已经缺少这样的空间,很多落后且缺少秩序的国家没有那样做的能力。中国因此是经济前景最光明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当类似蒸汽机、汽车、手机这种颠覆性创新产品的出现遇到瓶颈,工业进步被定格在发动机、芯片上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将会缩小,善于模仿、逆向工程追赶的中国正迅速接近着发达国家。因此,时间和机遇都在中国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