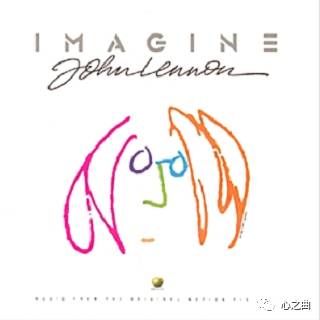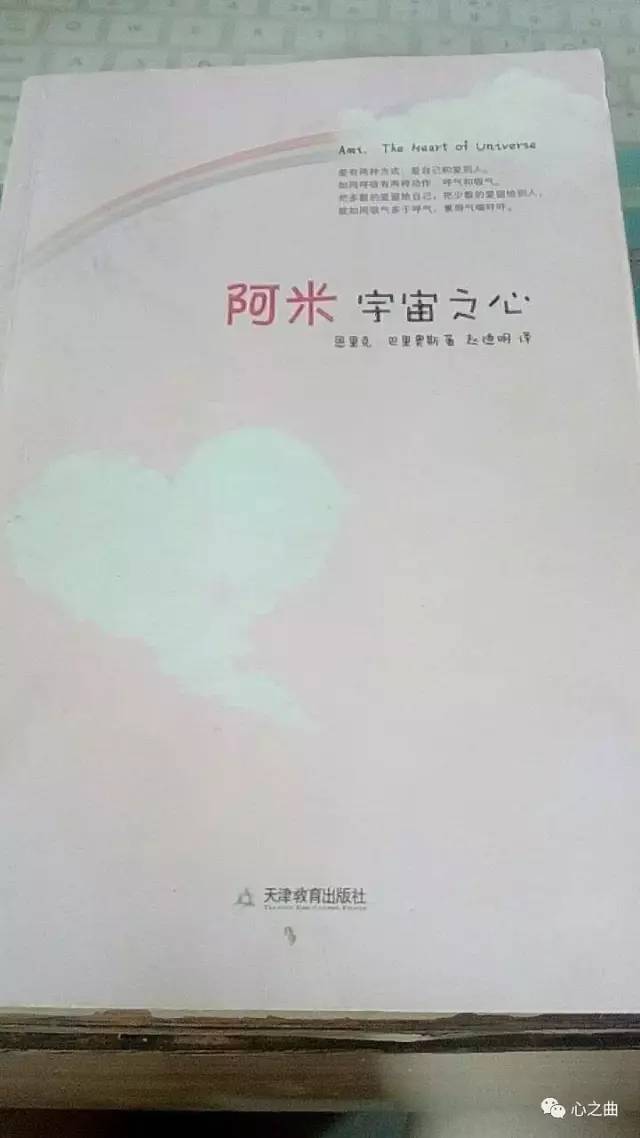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矛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圣经》(以赛亚书2:4)
今年年初的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约翰列侬的歌曲《Imagine》,我喜欢列侬在上世纪60年代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期许,那个“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头顶上只有一片蓝天”的心灵世界,那个“没有国家,没有宗教,大家都没有财产,各位兄弟姐妹都能共享世界的财产”的现实世界,是啊,有人也许会觉得列侬在说梦中痴话,“但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加入我们。”到时候,世界就和平了,我们在大地的国上,建立了天国。
然后我去看网易云音乐上对这首歌的评论,那时看到有人说这首歌说的是“乌托邦”,潜台词是那不可能实现。我听这首歌时虽然没想起“乌托邦”这个概念,但我一见这个词,心里就有一种沮丧之感,可能这是源于人类几十年来对于想象中“乌托邦”的不可实现与虚幻的思维定势吧!刚好最近我看到一篇叙说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在上世纪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整理基督教思想中的弥赛亚主义为乌托邦正名。对于人们对于乌托邦的否定性情结,他总结到:人们对乌托邦的误解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将乌托邦视为“最廉价的幻境”,布洛赫认为“(乌托邦)在最普通的意义上……完全被误解或没有被认识到。乌托邦所指的是某种空洞的废话,……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达到的,并且对一个具有健全的人类理智的人来说,原本是不值得讨论的”。第二层含义是将乌托邦视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无把握、不确定的想象。这导致了大批“无家可归的左翼”并让人们贬低“最终目标”。他说,他提出了“具有浓厚弥赛亚救赎色彩的乌托邦精神”,布洛赫对乌托邦的正名,那充满希望的神学思想让我备受鼓舞,正是他的探索,让“乌托邦”一词摆脱了人们赋予它的否定性思维定势。他有一句名言:“有希望便会有宗教”,尽管“他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基督教神学家,可他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政治神学、希望神学和解放神学,且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布洛赫是一位操着神学语言的无神论革命者、手持圣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抱有救赎情怀的书斋骑士”。[1]列侬和布洛赫活在一个时代,不知列侬对布洛赫的思想有没有了解呢?其实,不管列侬知不知道布洛赫,按照荣格的“同时性原理”,那时列侬的合一之歌,布洛赫的弥赛亚神学思想,都可看作上世纪人类对现代性之绝望的“异口同声”之希望回应。
21世纪已然到来,人类迎来了先知们预言的“千禧年”。以我的观察,不管是修行书中高灵存有对我们世界的预言,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努力,还是这世界已然展现的进步,我们真的离列侬歌曲《Imagine》中期盼的世界越来越近,种种的现实告诉我们——乌托邦是可能实现的——互联网颠覆了人们沟通连接的方式,世界越来越倾向于分享;人工智能将取代人力,未来很多职位将不会存在;马云说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利他的世界;一个企业能否经营持久要看它的创新能力;新一代的孩子们从小就培养了阅读的爱好,教育的重点不是知识,而是思维方式......如同《圣经》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路加:11:2)21世纪,人类将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
我愿意引用我非常喜欢的书——《阿米星星的孩子》,来看看这本书对一个更加进化的世界是怎么描述的:
根据阿米的标准,只有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的星球才算文明发达的星球:第一,必须人人都认识到爱心就是神,知道爱心就是宇宙的基本法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法则;第二,打破国家的界限,组成一个大家庭;第三,把爱心当作是世界一切组织的基本章程。阿米还以家庭为例给我解释了第三点。家庭成员应该怀着爱心分享一切,因为爱心是大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他说,凡是文明发达的世界都是这样生活的。
阿米说地球“就要从进化的第三级过度到第四级了。”
“第一级的星球还没有生命;第二级的星球有生命,但没有人类;第三级上出现了人类;你俩的星球就处于这进化的第三级上。”
“在第四级上,人类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按照宇宙法则生活的大家庭。并非所有的星球都能通过考验。有些星球在考验过程中自我毁灭了。”[2]
为什么阿米说有些星球在进化的考验中毁灭了?因为这些星球发展了高度发达的科技,爱心水平却没有提升到同一高度,他们用科技制造的武器彼此相杀,走向自我毁灭。而《圣经》中有句话给我们描绘了美好的未来:“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矛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4)阿米在谈到人类为宗教导师之名而相争时,说道:“名字,也就是所谓的标签,但是在精神世界里没有身份证,种种界限,区别都在消失”,“一旦人类心中有了爱,便会明白整个宇宙是个大统一体”。[3]标签使我们对他人有了概念性的定义,使我们看不到对方的真相,我们因先入之见而彼此分裂。放下评判,我们本有的爱就会自然涌出。你会感受到,我们原是一家人。
另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明日之神》这样描述未来的宗教:
恰恰相反,它(宗教)将变得更加无处不在。消失得将是教义中那个愤怒,嫉妒,惩罚的神,消失得将是惩罚报复的合理道德性,消失得将是教义的排他性和“优越性”——正是这一点给过去的很多宗教蒙上了阴影。
人类将出现一种向神性表达冲动的新方式,它将与宗教并肩站立。这种表达不会根植于编码化的文本和教义,而是根植于真心追寻神的每个人时时刻刻的体验。[4]
《明日之神》里还有关于财富,资源,教育,人际关系等等话题的“未来建议”,那是一个共用共享,人人平等,爱心至上,活在当下的世界。那是一个我们未来将要实现的上帝之国。
我自己写的论文《宗教灵性复兴——宗教的未来》对我们这个时代所用的称呼为第二轴心时代,第二轴心时代是浙江大学宗教学教授王志成老师对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定义,用以区别和呼应耶稣,老子,孔子所在的第一轴心时代。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写到: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生活就是一切,生活就是上帝”,或许托翁在表达,人就是一切,人的灵性具有神圣性。威廉•戈尔丁在《自由堕落》中说,“生活就如虚无,因为它是一切”,或许威廉在表达,在生活的空旷性空间中,处处都体现着神圣的临在,那,就是生命的一切。在第二轴心时代的灵性复兴中,神圣与世俗融合为一,生活与灵性交融无二,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无神论与有神论在超越的维度彼此和解,全球迎来了新的宗教对话时代,而中国宗教能为世界宗教灵性贡献出什么?这有待于更多的学者加入具体的宗教对话。
最后,以一首一年前我写的英文诗为本文作结:
We are Oneness
Human prefer love and peace,
Yet why religions cause fear?
There are killings,attacks......
Cause people's hearts are sepreated,
Christans seek for God,
Buddhanists seek for Buddha,
Moslem seek for Allah,
Actually we are Oneness,
Just differrent names of One Source,
Imagine a picture:
God, Buddha, Allha sit together,
Talking like friends,
Yes, they are three, but also One,
Can't we human be as One?
It will when we live out of it.
[1]《乌托邦•末世论•希望——恩斯特•布洛赫对基督教神学的文化批判》,陈影,北京语言大学。见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二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国际研讨班青年组论文集
[2]《阿米:宇宙之心》,(委内瑞拉)恩里克.巴里奥斯著,赵德明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3]同上。
[4]《明日之神》,(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赵恒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周小妍,真知追求者,音乐发烧友,文艺小青年。常常写宗教灵性文章,人生路线基本是左手中文,右手英语;左手论文,右手文章。办有个人公众号:心之曲,hearts-melody。真知,灵性,自然。
赞赏二维码
让作者知道,她的文章确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