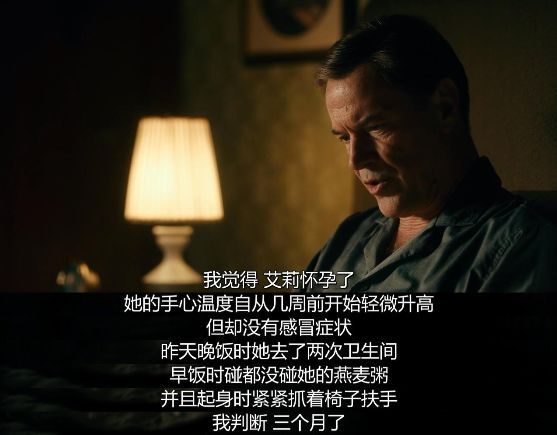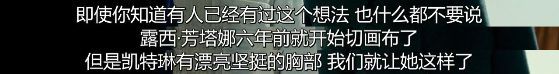想想看。
你独自走在小路上,一个疯子突然跳到你面前。
而且赤身裸体。
一听他说的话,更疯了——
我的名字叫做“真实”,一个叫“谎言”的家伙穿走了我的衣服!
是不是想扭头就走?
别怕。
Sir说的只是一部电影。
看它如何狠狠地扒下谎言的衣服,露出震撼的真实——
《无主之作》
Werk ohne Autor
德国导演冯·多纳斯马。
前后13年,一共拍了三部长片。
处女作即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9.1分占据豆瓣排名No.43的《窃听风暴》。
背景,是冰冷的。
在一个奥威尔式的国家,东德。
高压之下,口出利剑执笔为枪,一双双伺机待发的眼睛注视着相互揣测的人心。
结局,却是温暖的。
一名秘密警察的“良心发现”。
只是因为他听见了、看见了,另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世界。
亲身经历过东德时期的导演多纳斯马,在一场对立的历史中,选择了信念的力量。
然而。
关于《窃听风暴》,也有一个著名的传闻——
拍摄时,一名监狱博物馆馆长拒绝了剧组的请求。
他觉得这个剧本不符史实:
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信念美好,真相不堪,到底应该取舍?
《窃听风暴》倾向前者。
《无主之作》则背道而驰,将历史重新推倒验算,揭示你难以接受的、近乎赤裸的真实。
在三个小时的片长中,历史被推得更远,拉得更长。
1937-1966,几乎囊括近代世界的全部政治风貌:
从二战前夕的纳粹德国,到冷战时期的东德,再到实现了自由的西德。
价值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
但谎言,始终光鲜。
赤裸的真实,被抹杀、被恐吓、被迷惑......无人认领。
别误会。
《无主之作》并不只是一场向谎言的复仇,它其实更想告诉你:
快睁开眼看看。
这样的赤裸,究竟能有多美?
谎言
1937年,德国,德累斯顿。
上图那个光着身子弹钢琴的女孩,叫做伊丽莎白,她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跟一个普通女孩一样,热爱祖国、自由、艺术。
但伊丽莎白却有一双不太一样的眼睛。
她总能看到一点,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看人家的全家福,仅从拍摄的姿势就看出,这段婚姻是场折磨。
或者说,她是在看穿。
那些别人不愿说出口的,并试图隐藏的真相。
但这一切,并非她的热爱。
比起看,她更爱听。
站在一圈公共汽车的中央,请司机们一起鸣笛。
你觉得聒噪,她却感到无比悦耳。
因为她听得出来,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一个音符——小字二组A。
沉迷于这个音符,便决定收集它所有的样子。
可以来自公交车鸣起喇叭,来自不同鸟儿的鸣叫,来自不同钢琴的弹奏......
甚至还可以……用烟灰缸在头上狠狠砸出那个美妙的音符。
为了捕获这样的美,可以不计一切代价。
伊丽莎白坚信,真实即美好。
“不要把目光移开,所有的一切,只要是真实的,就是美好的。”
这也是电影英文名的由来——Never Look Away。
然而在家人眼中,这样的“美”是一种病。
在德国纳粹的眼中,这样的“美”是民族的污垢。
高贵的雅利安血统,决不能受到“缺陷基因”的侵染。
《绝育法》,便是纳粹向德国本族人民进行的一场屠杀——
任何患有遗传疾病的人都将接受外科绝育手术。
如果病患没有任何存在价值,将会被送到统一的集中营,进行人道毁灭。
而杀人的,不是士兵和武器。
而是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手中那支用于诊断的笔。
用来诊断病情的“+/-”,成为了通向地狱的路标。
这才是最疯狂的地方:
匪夷所思的暴行,被赋予了最“科学”的解释。
进而被奉为崇高使命。
这对加减号,就是谎言的漂亮衣服。
它像是遮挡在眼前的手,凶手不会因真相忏悔,无辜者不会因真相恐惧,受害者的脸上都能挂着微笑。
就像,伊丽莎白。
她被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加号。
在被“医生”们带走的时候,她盯着自己最亲昵的侄子库尔特,笑了起来。
她又一次对库尔特说道:“不要看向别处,只要是真实的,就是美好的。”
于是,库尔特在这残忍的一幕面前,放下了遮挡住眼前的手。
和我们一样,年幼的库尔特还听不明白伊丽莎白阿姨的话。
谎言,是虚伪的。
真实,就一定美好吗?
赤裸
放心吧,Sir并没有剧透,以上只是整部电影的序章。
虽然《无主之作》横跨极端的历史时期。
比起揭露历史,将罪恶归结于时代,它更想看到的是人的问题。
整部影片通过记录一名画家的成长,实现了艺术绘画与生活、政治、时代的对话。
故事,所有的表达近乎赤裸。
主人公库尔特继承了伊丽莎白阿姨,对真实的追寻。
从小到大,他一直注视着那些别人捂住双眼的真实——
战争罪行。
盟军的轰炸机,在他的家乡泄下成千上万吨的炸药。
思想钳制。
因为独特的天赋,库尔特就读于东德的艺术院校,想要通过绘画表达自我。
老师却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你的画太危险了,因为里面都是“我、我、我”。
艺术不能表达自我,只能为人民服务。
人性挣扎。
父亲本是一名教师,战时因为求全不情愿地加入了纳粹。
战后,也就免不了被清算、被打压,失去了教师身份,干着最不受待见的工作,承受着歧视的眼光......
最后,他亲手了结了自己的苦难。
所有这些残忍压抑的时刻,库尔特自始至终都没有把目光移向别处。
然而他也日益困惑和惶恐,这真实,真的美吗?
当然,他生命中也体会到了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美。
比如爱情。
严格地说,咳,是肉体与爱情。
库尔特遇见了同校的女孩埃莉。
说真的,如果不是艺术生,还真难在床上说出这么有腔调的情话。
你太美了,这几乎都不浪漫了
你还以为那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看向别处”只是句口号么?
不。
电影的床戏就说到做到了——
目不旁视,纤毫毕现。
导演用镜头实践了这种真实。
△ 嗯,有删减
最重要的并非尺度,而是它被拢上的,一层艺术品般、不沾邪欲的美感。
这种美,叫做自由。
尽管只有这一方天地。
就好比《1984》里那张写着“我爱你”的纸条,在肃杀压抑的环境中掀起了狂风暴雨。
这样的环境中,爱情更像一场反抗。
两个灵魂相缠,更像是一种同谋。
肉体,是最直接、最普世的反抗方式。
但即便隐藏得再深。
总是隔墙有耳。
家长
《无主之作》中,并没有极力用苦难描绘一个时代的悲哀和可笑。
反而在试图拆解所有悲剧的来源。
其中之一,便是埃莉的父亲——
西本德教授(塞巴斯蒂安·科赫 饰),战前是纳粹的妇科医生,正是他为库尔特的阿姨(伊丽莎白)画上的红色加号。
但如今,时代更迭。
脱下了军服,脱下了囚服,效忠于另一权威,便再没人知道他曾做过什么。
他是历史的化身。
几乎只用一场戏,你就能戳破谎言,看清楚他的本质。
当然,也是在床上。
一种鲜明的反差,看不出激情,也察觉不到愉悦。
当妻子用手搭在他手臂上时,他反而将妻子的手臂按住,接着机械性地重复着动作。
暴力,并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妻子的脸上却始终带着笑容。
那是在丈夫面前,礼貌、得体的笑容。
而这样的笑容,仅存在于丈夫的面前。
比起陪伴,更需要忠诚。
比起自由,更需要安稳。
比起真实,更需要的是一家人的整整齐齐。
在西本德教授眼中,自己是一名守护者,也是他口中“最好的男人”。
所有的消息,都躲不过它的眼睛。
他随时掌握着女儿的一举一动,从细微的差别就观察出女儿藏着的“秘密”。
我觉得艾莉怀孕了。
她的手心温度自从几周前开始轻微升高,但却没有感冒症状。昨天晚饭时她去了两次卫生间,早饭时碰都没碰她的燕麦粥,并且起身时紧紧抓着椅子扶手。
我判断,三个月了。
而所有的隐患,都要在第一时间排除。
而让这一切实施的,又是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
这样的谎言,也作用于他自己。
女儿艾莉,原本也叫伊丽莎白,与库尔特的阿姨同名。而他却无法再次面对这个名字,将女儿改名为艾莉。
用一只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将历史置于身后。
对于西本德教授而言,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都是成为“最好男人”的代价。
他不想要喜欢自由吗?
怎么会?
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一家人的自由。
对,让一家人在动荡之中平平稳稳,甚至拥有不错的生活。
讨好时代,与时代共舞。
并做到最好,才有资格去争取物质、地位、权力上的自由。
这样努力换来的自由,你认同吗?
答案或许见仁见智。
但Sir敢肯定的是,这样看似稳固的自由又是脆弱的。
因为它永远不能面对真实。
真实
库尔特一生追寻的真实。
说到底,他也在问什么才是艺术真正的自由?
库尔特的童年,纳粹分子用屠杀消灭自由;青年时代的东德,政府用主义压倒自由。
1962年,库尔特投进了资本主义的西德的怀抱。
自由的风将他环绕,艺术的脚镣也卸下。
他,终于可以“得心应手”了。
真的吗?
如果说,之前的库尔特是画不出那个“我”。
那么再自由的西德,他却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这里充满了太多花哨的现代艺术,暧昧、复杂又难以解释。
或许你跟Sir有一样的感受。
好酷、好厉害、好有态度,但确实不太懂......
或许,正因为太多人不懂,它也可能成为另一种难以面对真实的谎言。
忽略表达重于形式,或许是单纯地博眼球。
到头来,库尔特所盼望的自由创作,不能说是真正的艺术。
只能算是自由买卖。
有态度、有主张的年轻学生,都在询问价格的环节被打回原形。
- 这种艺术品可以买吗?
- 当然可以,这就是艺术的美妙之处
所有绝对的自由的承诺,都是一种迷惑。
就像库尔特放下绘画,尝试去进行现代艺术创作时,可以做得无比出色。
但此时,他又觉得所有表达,都并非他所想。
他真正熟悉的,还是那一板一眼的人物肖像;他真正怀念的,还是那点滴中收录的回忆......
这也是《无主之作》不甚讨喜的地方。
当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于,政治是如何扼杀艺术的时候。
《无主之作》却在问:艺术的障碍仅止于此吗?
电影昭示了一个艺术家诞生所需的两种自由——
在创作束缚松绑的西德,库尔特获得的是外在的自由。
但这不代表,艺术自然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
他还要寻找到自己内在的自由。
那是情感、欲望和自我……
或者说,自由永远不是一种完成时。
即使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你也仍然面临让自己更自由起来的重任。
它从来不会因为环境而做出改变。
电影的尾声,是库尔特效仿自己的阿姨,走进了一个停车场。
他就像伊丽莎白阿姨生前那样,向所有司机请求,在同时按下喇叭。
共同演奏出那个最动听的那个音符——小字二组的A。
在这样的收获、享受、感动中。
达到这样的自由,仿佛是一件最简单的事。
而且,从纳粹到现代,似乎几十年来都一直如此简单。
它不在于你获得了什么。
而在于放下了什么之后,重新获得的自我。
当然,客观的自由就不重要吗?
它当然重要。
它保证着这些自由的人,不被世界判为疯子。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