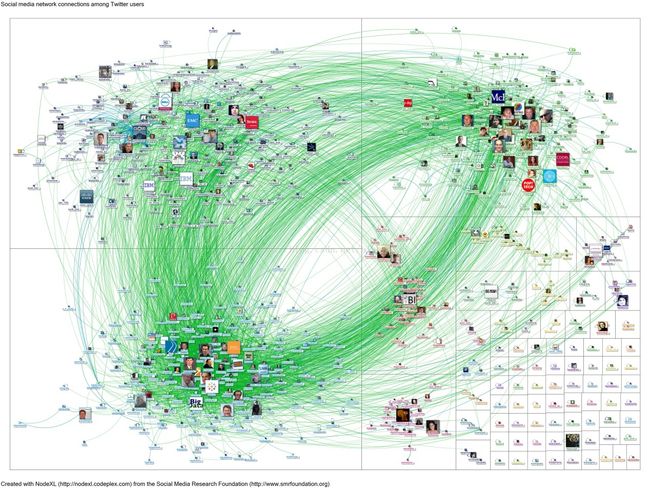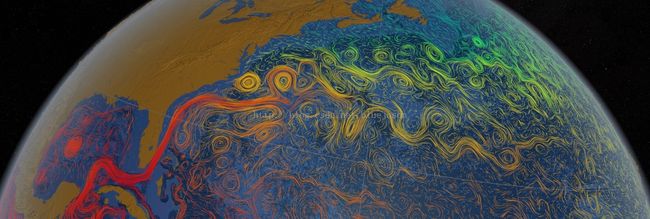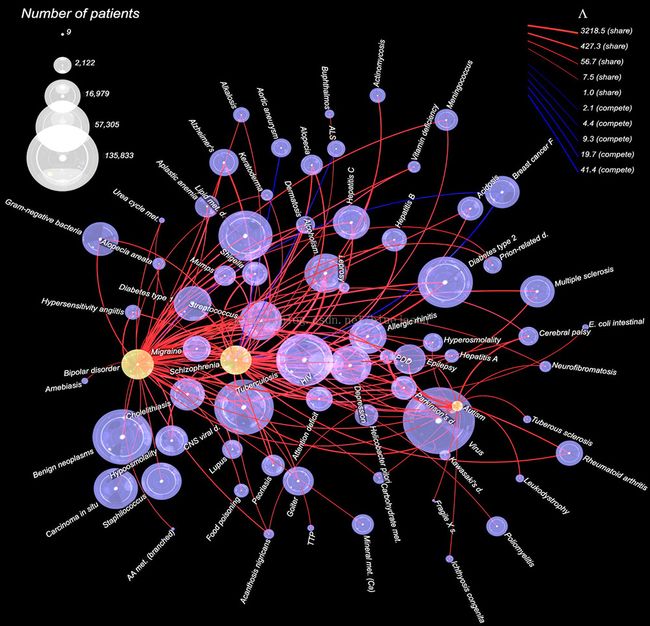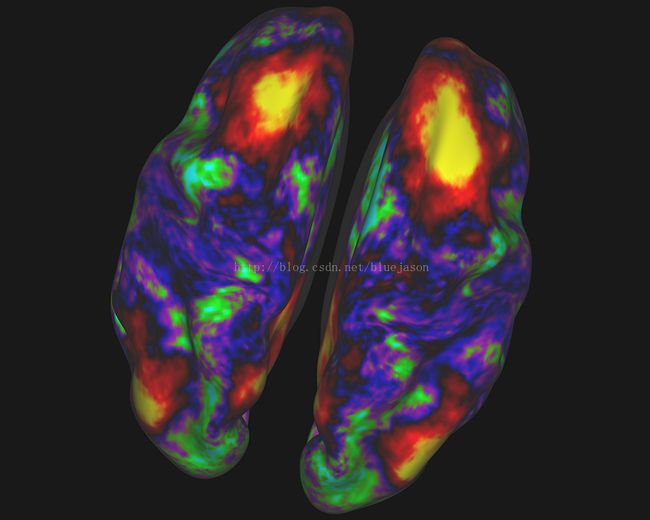- Python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战指南
William数据分析
pythonpython数据
在数据驱动的时代,Python因其简洁的语法、强大的库生态系统以及活跃的社区,成为了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的首选语言。本文将通过一个详细的案例,带领大家学习如何使用Python进行数据分析,并通过可视化来直观呈现分析结果。一、环境准备1.1安装必要库在开始数据分析和可视化之前,我们需要安装一些常用的库。主要包括pandas、numpy、matplotlib和seaborn等。这些库分别用于数据处理、数学
- Pyecharts数据可视化大屏:打造沉浸式数据分析体验
我的运维人生
信息可视化数据分析数据挖掘运维开发技术共享
Pyecharts数据可视化大屏:打造沉浸式数据分析体验在当今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如何将海量数据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出来,成为了数据分析师和企业决策者关注的焦点。Pyecharts,作为一款基于Python的开源数据可视化库,凭借其丰富的图表类型、灵活的配置选项以及高度的定制化能力,成为了构建数据可视化大屏的理想选择。本文将深入探讨如何利用Pyecharts打造数据可视化大屏,并通过实际代码案例
- Day1笔记-Python简介&标识符和关键字&输入输出
~在杰难逃~
Pythonpython开发语言大数据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杰哥开展一个新的专栏,当然,数据分析部分也会不定时更新的,这个新的专栏主要是讲解一些Python的基础语法和知识,帮助0基础的小伙伴入门和学习Python,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开始认真学习啦!一、Python简介【了解】1.计算机工作原理编程语言就是用来定义计算机程序的形式语言。我们通过编程语言来编写程序代码,再通过语言处理程序执行向计算机发送指令,让计算机完成对应的工作,编程
- pyecharts——绘制柱形图折线图
2224070247
信息可视化pythonjava数据可视化
一、pyecharts概述自2013年6月百度EFE(ExcellentFrontEnd)数据可视化团队研发的ECharts1.0发布到GitHub网站以来,ECharts一直备受业界权威的关注并获得广泛好评,成为目前成熟且流行的数据可视化图表工具,被应用到诸多数据可视化的开发领域。Python作为数据分析领域最受欢迎的语言,也加入ECharts的使用行列,并研发出方便Python开发者使用的数据
- nosql数据库技术与应用知识点
皆过客,揽星河
NoSQLnosql数据库大数据数据分析数据结构非关系型数据库
Nosql知识回顾大数据处理流程数据采集(flume、爬虫、传感器)数据存储(本门课程NoSQL所处的阶段)Hdfs、MongoDB、HBase等数据清洗(入仓)Hive等数据处理、分析(Spark、Flink等)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应用(Python、SparkMLlib等)大数据时代存储的挑战(三高)高并发(同一时间很多人访问)高扩展(要求随时根据需求扩展存储)高效率(要求读写速度快)
- 《Python数据分析实战终极指南》
xjt921122
python数据分析开发语言
对于分析师来说,大家在学习Python数据分析的路上,多多少少都遇到过很多大坑**,有关于技能和思维的**:Excel已经没办法处理现有的数据量了,应该学Python吗?找了一大堆Python和Pandas的资料来学习,为什么自己动手就懵了?跟着比赛类公开数据分析案例练了很久,为什么当自己面对数据需求还是只会数据处理而没有分析思路?学了对比、细分、聚类分析,也会用PEST、波特五力这类分析法,为啥
- Python开发常用的三方模块如下:
换个网名有点难
python开发语言
Python是一门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拥有丰富的第三方库,这些库为开发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下是100个常用的Python库,涵盖了多个领域:1、NumPy,用于科学计算的基础库。2、Pandas,提供数据结构和数据分析工具。3、Matplotlib,一个绘图库。4、Scikit-learn,机器学习库。5、SciPy,用于数学、科学和工程的库。6、TensorFlow,由Google开发的开源机
- ES聚合分析原理与代码实例讲解
光剑书架上的书
大厂Offer收割机面试题简历程序员读书硅基计算碳基计算认知计算生物计算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AIGCAGILLMJavaPython架构设计Agent程序员实现财富自由
ES聚合分析原理与代码实例讲解1.背景介绍1.1问题的由来在大规模数据分析场景中,特别是在使用Elasticsearch(ES)进行数据存储和检索时,聚合分析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聚合分析允许用户对数据集进行细分和分组,以便深入探索数据的结构和模式。这在诸如实时监控、日志分析、业务洞察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1.2研究现状目前,ES聚合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大数据平台的核心组件之一。它支持多种类型的聚
- WebMagic:强大的Java爬虫框架解析与实战
Aaron_945
Javajava爬虫开发语言
文章目录引言官网链接WebMagic原理概述基础使用1.添加依赖2.编写PageProcessor高级使用1.自定义Pipeline2.分布式抓取优点结论引言在大数据时代,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收集的重要工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Java作为一门广泛使用的编程语言,在爬虫开发领域也有其独特的优势。WebMagic是一个开源的Java爬虫框架,它提供了简单灵活的API,支持多线程、分布式抓取,以及丰富的
- 免费的GPT可在线直接使用(一键收藏)
kkai人工智能
gpt
1、LuminAI(https://kk.zlrxjh.top)LuminAI标志着一款融合了星辰大数据模型与文脉深度模型的先进知识增强型语言处理系统,旨在自然语言处理(NLP)的技术开发领域发光发热。此系统展现了卓越的语义把握与内容生成能力,轻松驾驭多样化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VisionAI在NLP界的应用领域广泛,能够胜任从机器翻译、文本概要撰写、情绪分析到问答等众多任务。通过对大量文本数据的
- Python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jun778895
python数据分析开发语言
Python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是一个涉及数据处理、分析和以图形化方式展示数据的过程,它对于数据科学家、分析师以及任何需要从数据中提取洞察力的专业人员来说至关重要。以下将详细探讨Python在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方面的应用,包括常用的库、数据处理流程、可视化技巧以及实际应用案例。一、Python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的重要性数据可视化是将数据以图形或图像的形式表示出来,以便人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数据背后的信息和规
- 如何利用大数据与AI技术革新相亲交友体验
h17711347205
回归算法安全系统架构交友小程序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技术正逐渐革新相亲交友体验,为寻找爱情的过程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编辑h17711347205)。通过精准分析和智能匹配,这些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相亲交友系统的效率和用户体验。大数据的力量大数据技术能够收集和分析用户的行为模式、偏好和互动数据,为相亲交友系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通过分析用户的搜索历史、浏览记录和点击行为,系统能够深入了解用户的兴趣和需求,从而提供更
- Python实现关联规则推荐
这孩子谁懂哈
PythonMachineLearningpython关联规则机器学习
1.什么关联规则关联规则(AssociationRules)是反映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关联性,如果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那么,其中一个事物就能通过其他事物预测到。关联规则是数据挖掘的一个重要技术,用于从大量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数据项之间的相关关系。关联规则挖掘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沃尔玛的啤酒与尿布的故事,通过对超市购物篮数据进行分析,即顾客放入购物篮中不同商品之间的关
- 未来软件市场是怎么样的?做开发的生存空间如何?
cesske
软件需求
目录前言一、未来软件市场的发展趋势二、软件开发人员的生存空间前言未来软件市场是怎么样的?做开发的生存空间如何?一、未来软件市场的发展趋势技术趋势: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人工智能将在更多领域得到应用,如智能客服、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等,这将极大地推动软件市场的增长。云计算与大数据:云计算服务将继续普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将更加广泛。企业将更加依赖云计算和大数据来优化运营、提升效率,并
- Hadoop架构
henan程序媛
hadoop大数据分布式
一、案列分析1.1案例概述现在已经进入了大数据(BigData)时代,数以万计用户的互联网服务时时刻刻都在产生大量的交互,要处理的数据量实在是太大了,以传统的数据库技术等其他手段根本无法应对数据处理的实时性、有效性的需求。HDFS顺应时代出现,在解决大数据存储和计算方面有很多的优势。1.2案列前置知识点1.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大量数据集合,
- [转载] NoSQL简介
weixin_30325793
大数据数据库运维
摘自“百度百科”。NoSQL,泛指非关系型的数据库。随着互联网web2.0网站的兴起,传统的关系数据库在应付web2.0网站,特别是超大规模和高并发的SNS类型的web2.0纯动态网站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暴露了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而非关系型的数据库则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NoSQL数据库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大规模数据集合多重数据种类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大数据应用难题。虽然NoSQL流行语
- Kafka详细解析与应用分析
芊言芊语
kafka分布式
Kafka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事件流平台(EventStreamingPlatform),由LinkedIn公司最初采用Scala语言开发,并基于ZooKeeper协调管理。如今,Kafka已经被Apache基金会纳入其项目体系,广泛应用于大数据实时处理领域。Kafka凭借其高吞吐量、持久化、分布式和可靠性的特点,成为构建实时流数据管道和流处理应用程序的重要工具。Kafka架构Kafka的架构主要由
- 分享一个基于python的电子书数据采集与可视化分析 hadoop电子书数据分析与推荐系统 spark大数据毕设项目(源码、调试、LW、开题、PPT)
计算机源码社
Python项目大数据大数据pythonhadoop计算机毕业设计选题计算机毕业设计源码数据分析spark毕设
作者:计算机源码社个人简介:本人八年开发经验,擅长Java、Python、PHP、.NET、Node.js、Android、微信小程序、爬虫、大数据、机器学习等,大家有这一块的问题可以一起交流!学习资料、程序开发、技术解答、文档报告如需要源码,可以扫取文章下方二维码联系咨询Java项目微信小程序项目Android项目Python项目PHP项目ASP.NET项目Node.js项目选题推荐项目实战|p
- 疫情,疫情
东山草
2020年,疫情爆发,至今已近三年,反反复复,此起彼伏。不但没被消灭,还自我发展,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与时俱进的变异着。去年11月,疫情之下,大数据800米范围内,都成为时空伴随者。“你的码儿有没有变颜色”“你绿码还是黄码”成为那段时间的流行语,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全员核酸。段子手整出来一首歌: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800米内我们不曾擦肩而过,你却要我14天相
- python读写CSV文件
bcbobo21cn
.Netpython开发语言机器学习CSV
做数据分析,有时候要分析的数据在CSV文件里;先看一下python读写CSV文件;importpandasaspddf=pd.read_csv('test1.csv')print(df)print('')print(df.head(2))companyname=["A1","B2","E3","F4"]legperson=["lier","yanqi","wangwu","zhangsan"]le
- 软件测试/测试开发/全日制 |利用Django REST framework构建微服务
霍格沃兹-慕漓
django微服务sqlite
霍格沃兹测试开发学社推出了《Python全栈开发与自动化测试班》。本课程面向开发人员、测试人员与运维人员,课程内容涵盖Python编程语言、人工智能应用、数据分析、自动化办公、平台开发、UI自动化测试、接口测试、性能测试等方向。为大家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化的学习体验,课程还增加了名企私教服务内容,不仅有名企经理为你1v1辅导,还有行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针对性地解决学习、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让找
- 在服务器计算节点中使用 jupyter Lab
ranshan567
程序人生
JupyterLab是一个基于网页的交互式开发环境,用于科学计算、数据分析和机器学.jupyterlab是jupyternotebook的下一代产品,集成了更多功能,使用起来更方便.在进行数据分析及可视化时,个人电脑不能满足大数据的分析需求,就需要用到高性能计算机集群资源,然而计算机集群的计算节点往往没有联网功能,所以在计算机集群中使用jupyterLab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具体的步骤如下:
- 大数据真实面试题---SQL
The博宇
大数据面试题——SQL大数据mysqlsql数据库bigdata
视频号数据分析组外包招聘笔试题时间限时45分钟完成。题目根据3张表表结构,写出具体求解的SQL代码(搞笑品类定义:视频分类或者视频创建者分类为“搞笑”)1、表创建语句:createtablet_user_video_action_d(dsint,user_idstring,video_idstring,action_typeint,`timestamp`bigint)rowformatdelimi
- python数据分析知识点大全
编程零零七
python数据分析python开发语言python数据分析数据分析知识点大全python数据分析知识点python教程python基础
Python数据分析知识点大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基础概念与目的数据分析定义:数据分析是指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从数据中挖掘规律、验证猜想、进行预测。Python在数据分析中的优势:Python因其易学性、快速开发、丰富的扩展库(如NumPy、Pandas等)和成熟的框架,成为数据分析领域的
- CV、NLP、数据控掘推荐、量化
海的那边-
AI算法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
下面是对CV(计算机视觉)、NLP(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推荐和量化的简要概述及其应用领域的介绍:1.CV(计算机视觉,ComputerVision)定义:计算机视觉是一门让计算机能够从图像或视频中提取有用信息,并做出决策的学科。它通过模拟人类的视觉系统来识别、处理和理解视觉信息。主要任务:图像分类:识别图像中的物体并分类,比如猫、狗、车等。目标检测:在图像或视频中定位并识别多个对象,如人脸检测
- Flume:大规模日志收集与数据传输的利器
傲雪凌霜,松柏长青
后端大数据flume大数据
Flume:大规模日志收集与数据传输的利器在大数据时代,随着各类应用的不断增长,产生了海量的日志和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对业务的健康监控至关重要,还可以通过深入分析,帮助企业做出更好的决策。那么,如何高效地收集、传输和存储这些海量数据,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挑战。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ApacheFlume,它是如何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一、Flume概述ApacheFlume是一个分布式、可靠、可扩展的日志
- 云服务业界动态简报-20180128
Captain7
一、青云青云QingCloud推出深度学习平台DeepLearningonQingCloud,包含了主流的深度学习框架及数据科学工具包,通过QingCloudAppCenter一键部署交付,可以让算法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快速构建深度学习开发环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模型和算法调优。二、腾讯云1.腾讯云正式发布腾讯专有云TCE(TencentCloudEnterprise)矩阵,涵盖企业版、大数据版、AI
- 数据分析-24-时间序列预测之基于keras的VMD-LSTM和VMD-CNN-LSTM预测风速
皮皮冰燃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文章目录1普通的LSTM模型1.1数据重采样1.2数据标准化1.3切分窗口1.4划分数据集1.5建立模型1.6预测效果2VMD-LSTM模型2.1VMD分解时间序列2.2对每一个IMF建立LSTM模型2.2.1IMF1—LSTM2.2.2IMF2-LSTM2.2.3统一代码2.3评估效果3CNN-LSTM模型3.1数据预处理3.2建立模型3.3效果预测4VMD-CNN-LSTM模型4.1VMD分解
- 大数据毕业设计hadoop+spark+hive知识图谱租房数据分析可视化大屏 租房推荐系统 58同城租房爬虫 房源推荐系统 房价预测系统 计算机毕业设计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
2401_84572577
程序员大数据hadoop人工智能
做了那么多年开发,自学了很多门编程语言,我很明白学习资源对于学一门新语言的重要性,这些年也收藏了不少的Python干货,对我来说这些东西确实已经用不到了,但对于准备自学Python的人来说,或许它就是一个宝藏,可以给你省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别在网上瞎学了,我最近也做了一些资源的更新,只要你是我的粉丝,这期福利你都可拿走。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些东西怎么用,文末抱走。(1)Python所有方向的学习路线(
- 架构评审的自动化与人工智能: 如何提高效率
光剑书架上的书
架构自动化人工智能运维
1.背景介绍架构评审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旨在确保软件架构的质量、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传统的架构评审通常是由人工进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架构评审,从而提高评审的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如何通过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架构评审的效率。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背景介绍核心概念与联系核心算法原理和具体操作
- java责任链模式
3213213333332132
java责任链模式村民告县长
责任链模式,通常就是一个请求从最低级开始往上层层的请求,当在某一层满足条件时,请求将被处理,当请求到最高层仍未满足时,则请求不会被处理。
就是一个请求在这个链条的责任范围内,会被相应的处理,如果超出链条的责任范围外,请求不会被相应的处理。
下面代码模拟这样的效果:
创建一个政府抽象类,方便所有的具体政府部门继承它。
package 责任链模式;
/**
*
- linux、mysql、nginx、tomcat 性能参数优化
ronin47
一、linux 系统内核参数
/etc/sysctl.conf文件常用参数 net.core.netdev_max_backlog = 32768 #允许送到队列的数据包的最大数目
net.core.rmem_max = 8388608 #SOCKET读缓存区大小
net.core.wmem_max = 8388608 #SOCKET写缓存区大
- php命令行界面
dcj3sjt126com
PHPcli
常用选项
php -v
php -i PHP安装的有关信息
php -h 访问帮助文件
php -m 列出编译到当前PHP安装的所有模块
执行一段代码
php -r 'echo "hello, world!";'
php -r 'echo "Hello, World!\n";'
php -r '$ts = filemtime("
- Filter&Session
171815164
session
Filter
HttpServletRequest requ = (HttpServletRequest) req;
HttpSession session = requ.getSession();
if (session.getAttribute("admin") == null) {
PrintWriter out = res.ge
- 连接池与Spring,Hibernate结合
g21121
Hibernate
前几篇关于Java连接池的介绍都是基于Java应用的,而我们常用的场景是与Spring和ORM框架结合,下面就利用实例学习一下这方面的配置。
1.下载相关内容: &nb
- [简单]mybatis判断数字类型
53873039oycg
mybatis
昨天同事反馈mybatis保存不了int类型的属性,一直报错,错误信息如下:
Caused by: java.lang.NumberFormatException: For input string: "null"
at sun.mis
- 项目启动时或者启动后ava.lang.OutOfMemoryError: PermGen space
程序员是怎么炼成的
eclipsejvmtomcatcatalina.sheclipse.ini
在启动比较大的项目时,因为存在大量的jsp页面,所以在编译的时候会生成很多的.class文件,.class文件是都会被加载到jvm的方法区中,如果要加载的class文件很多,就会出现方法区溢出异常 java.lang.OutOfMemoryError: PermGen space.
解决办法是点击eclipse里的tomcat,在
- 我的crm小结
aijuans
crm
各种原因吧,crm今天才完了。主要是接触了几个新技术:
Struts2、poi、ibatis这几个都是以前的项目中用过的。
Jsf、tapestry是这次新接触的,都是界面层的框架,用起来也不难。思路和struts不太一样,传说比较简单方便。不过个人感觉还是struts用着顺手啊,当然springmvc也很顺手,不知道是因为习惯还是什么。jsf和tapestry应用的时候需要知道他们的标签、主
- spring里配置使用hibernate的二级缓存几步
antonyup_2006
javaspringHibernatexmlcache
.在spring的配置文件中 applicationContent.xml,hibernate部分加入
xml 代码
<prop key="hibernate.cache.provider_class">org.hibernate.cache.EhCacheProvider</prop>
<prop key="hi
- JAVA基础面试题
百合不是茶
抽象实现接口String类接口继承抽象类继承实体类自定义异常
/* * 栈(stack):主要保存基本类型(或者叫内置类型)(char、byte、short、 *int、long、 float、double、boolean)和对象的引用,数据可以共享,速度仅次于 * 寄存器(register),快于堆。堆(heap):用于存储对象。 */ &
- 让sqlmap文件 "继承" 起来
bijian1013
javaibatissqlmap
多个项目中使用ibatis , 和数据库表对应的 sqlmap文件(增删改查等基本语句),dao, pojo 都是由工具自动生成的, 现在将这些自动生成的文件放在一个单独的工程中,其它项目工程中通过jar包来引用 ,并通过"继承"为基础的sqlmap文件,dao,pojo 添加新的方法来满足项
- 精通Oracle10编程SQL(13)开发触发器
bijian1013
oracle数据库plsql
/*
*开发触发器
*/
--得到日期是周几
select to_char(sysdate+4,'DY','nls_date_language=AMERICAN') from dual;
select to_char(sysdate,'DY','nls_date_language=AMERICAN') from dual;
--建立BEFORE语句触发器
CREATE O
- 【EhCache三】EhCache查询
bit1129
ehcache
本文介绍EhCache查询缓存中数据,EhCache提供了类似Hibernate的查询API,可以按照给定的条件进行查询。
要对EhCache进行查询,需要在ehcache.xml中设定要查询的属性
数据准备
@Before
public void setUp() {
//加载EhCache配置文件
Inpu
- CXF框架入门实例
白糖_
springWeb框架webserviceservlet
CXF是apache旗下的开源框架,由Celtix + XFire这两门经典的框架合成,是一套非常流行的web service框架。
它提供了JAX-WS的全面支持,并且可以根据实际项目的需要,采用代码优先(Code First)或者 WSDL 优先(WSDL First)来轻松地实现 Web Services 的发布和使用,同时它能与spring进行完美结合。
在apache cxf官网提供
- angular.equals
boyitech
AngularJSAngularJS APIAnguarJS 中文APIangular.equals
angular.equals
描述:
比较两个值或者两个对象是不是 相等。还支持值的类型,正则表达式和数组的比较。 两个值或对象被认为是 相等的前提条件是以下的情况至少能满足一项:
两个值或者对象能通过=== (恒等) 的比较
两个值或者对象是同样类型,并且他们的属性都能通过angular
- java-腾讯暑期实习生-输入一个数组A[1,2,...n],求输入B,使得数组B中的第i个数字B[i]=A[0]*A[1]*...*A[i-1]*A[i+1]
bylijinnan
java
这道题的具体思路请参看 何海涛的微博:http://weibo.com/zhedahht
import java.math.BigInteger;
import java.util.Arrays;
public class CreateBFromATencent {
/**
* 题目:输入一个数组A[1,2,...n],求输入B,使得数组B中的第i个数字B[i]=A
- FastDFS 的安装和配置 修订版
Chen.H
linuxfastDFS分布式文件系统
FastDFS Home:http://code.google.com/p/fastdfs/
1. 安装
http://code.google.com/p/fastdfs/wiki/Setup http://hi.baidu.com/leolance/blog/item/3c273327978ae55f93580703.html
安装libevent (对libevent的版本要求为1.4.
- [强人工智能]拓扑扫描与自适应构造器
comsci
人工智能
当我们面对一个有限拓扑网络的时候,在对已知的拓扑结构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在连通点之后,还存在若干个子网络,且这些网络的结构是未知的,数据库中并未存在这些网络的拓扑结构数据....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设计新的模块和代码包来处理上面的问题
- oracle merge into的用法
daizj
oraclesqlmerget into
Oracle中merge into的使用
http://blog.csdn.net/yuzhic/article/details/1896878
http://blog.csdn.net/macle2010/article/details/5980965
该命令使用一条语句从一个或者多个数据源中完成对表的更新和插入数据. ORACLE 9i 中,使用此命令必须同时指定UPDATE 和INSE
- 不适合使用Hadoop的场景
datamachine
hadoop
转自:http://dev.yesky.com/296/35381296.shtml。
Hadoop通常被认定是能够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方案。 当人们提到“大数据”或是“数据分析”等相关问题的时候,会听到脱口而出的回答:Hadoop! 实际上Hadoop被设计和建造出来,是用来解决一系列特定问题的。对某些问题来说,Hadoop至多算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对另一些问题来说,选择Ha
- YII findAll的用法
dcj3sjt126com
yii
看文档比较糊涂,其实挺简单的:
$predictions=Prediction::model()->findAll("uid=:uid",array(":uid"=>10));
第一个参数是选择条件:”uid=10″。其中:uid是一个占位符,在后面的array(“:uid”=>10)对齐进行了赋值;
更完善的查询需要
- vim 常用 NERDTree 快捷键
dcj3sjt126com
vim
下面给大家整理了一些vim NERDTree的常用快捷键了,这里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快捷键了,希望文章对各位会带来帮助。
切换工作台和目录
ctrl + w + h 光标 focus 左侧树形目录ctrl + w + l 光标 focus 右侧文件显示窗口ctrl + w + w 光标自动在左右侧窗口切换ctrl + w + r 移动当前窗口的布局位置
o 在已有窗口中打开文件、目录或书签,并跳
- Java把目录下的文件打印出来
蕃薯耀
列出目录下的文件文件夹下面的文件目录下的文件
Java把目录下的文件打印出来
>>>>>>>>>>>>>>>>>>>>>>>>>>>>>>>>>>>>>>>>
蕃薯耀 2015年7月11日 11:02:
- linux远程桌面----VNCServer与rdesktop
hanqunfeng
Desktop
windows远程桌面到linux,需要在linux上安装vncserver,并开启vnc服务,同时需要在windows下使用vnc-viewer访问Linux。vncserver同时支持linux远程桌面到linux。
linux远程桌面到windows,需要在linux上安装rdesktop,同时开启windows的远程桌面访问。
下面分别介绍,以windo
- guava中的join和split功能
jackyrong
java
guava库中,包含了很好的join和split的功能,例子如下:
1) 将LIST转换为使用字符串连接的字符串
List<String> names = Lists.newArrayList("John", "Jane", "Adam", "Tom");
- Web开发技术十年发展历程
lampcy
androidWeb浏览器html5
回顾web开发技术这十年发展历程:
Ajax
03年的时候我上六年级,那时候网吧刚在小县城的角落萌生。传奇,大话西游第一代网游一时风靡。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了网吧老板两块钱想申请个号玩玩,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注,册,账,号。
彼时网吧用的512k的带宽,注册的时候,填了一堆信息,提交,页面跳转,嘣,”您填写的信息有误,请重填”。然后跳转回注册页面,以此循环。我现在时常想,如果当时a
- 架构师之mima-----------------mina的非NIO控制IOBuffer(说得比较好)
nannan408
buffer
1.前言。
如题。
2.代码。
IoService
IoService是一个接口,有两种实现:IoAcceptor和IoConnector;其中IoAcceptor是针对Server端的实现,IoConnector是针对Client端的实现;IoService的职责包括:
1、监听器管理
2、IoHandler
3、IoSession
- ORA-00054:resource busy and acquire with NOWAIT specified
Everyday都不同
oraclesessionLock
[Oracle]
今天对一个数据量很大的表进行操作时,出现如题所示的异常。此时表明数据库的事务处于“忙”的状态,而且被lock了,所以必须先关闭占用的session。
step1,查看被lock的session:
select t2.username, t2.sid, t2.serial#, t2.logon_time
from v$locked_obj
- javascript学习笔记
tntxia
JavaScript
javascript里面有6种基本类型的值:number、string、boolean、object、function和undefined。number:就是数字值,包括整数、小数、NaN、正负无穷。string:字符串类型、单双引号引起来的内容。boolean:true、false object:表示所有的javascript对象,不用多说function:我们熟悉的方法,也就是
- Java enum的用法详解
xieke90
enum枚举
Java中枚举实现的分析:
示例:
public static enum SEVERITY{
INFO,WARN,ERROR
}
enum很像特殊的class,实际上enum声明定义的类型就是一个类。 而这些类都是类库中Enum类的子类 (ja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