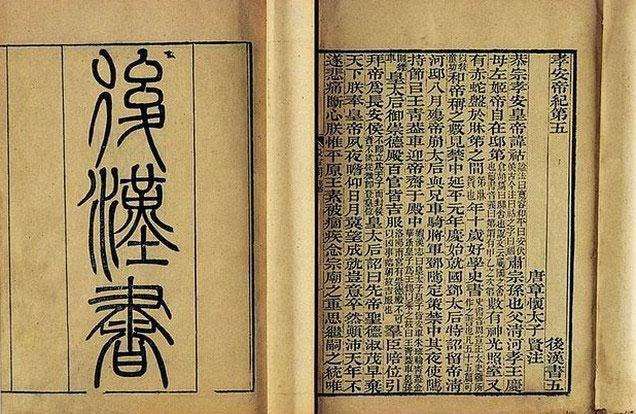- python实现接口自动化
一只小H呀の
python自动化开发语言
代码实现自动化相关理论代码编写脚本和工具实现脚本区别是啥?代码:优点:代码灵活方便缺点:学习成本高工具:优点:易上手缺点:灵活度低,有局限性。总结:功能脚本:工具自动化脚本:代码代码接口自动化怎么做的?第一步:python+request+unittest;具体描述?第二步:封装、调用、数据驱动、日志、报告;详细举例:第三步:api\scripts\data\log\report\until…脚本
- 探索Python中的集成方法:Stacking
Echo_Wish
Python笔记Python算法python开发语言
在机器学习领域,Stacking是一种高级的集成学习方法,它通过将多个基本模型的预测结果作为新的特征输入到一个元模型中,从而提高整体模型的性能和鲁棒性。本文将深入介绍Stacking的原理、实现方式以及如何在Python中应用。什么是Stacking?Stacking,又称为堆叠泛化(StackedGeneralization),是一种模型集成方法,与Bagging和Boosting不同,它并不直
- 高等数学 1.8 函数的连续性与间断点
MowenPan1995
高等数学笔记笔记学习
文章目录一、函数的连续性增量的概念函数连续的定义左连续与右连续的概念二、函数的间断点三种情形间断点举例一、函数的连续性增量的概念设变量uuu从它的一个初值u1u_1u1变到终值u2u_2u2,终值与初值的差u2−u1u_2-u_1u2−u1就叫做变量uuu的增量,记作Δu\DeltauΔu,即Δu=u2−u1\Deltau=u_2-u_1Δu=u2−u1增量Δu\DeltauΔu可以是正的,也可以
- struts1+struts2项目兼容升级到了spring boot 2.7
和稀泥
strutsspringbootjava
原项目比较复杂,集成了各种框架(struts1struts2spring3等),趁工作之余练练手,学习一下springboot。大概花了一周时间才调通。一、调整jar版本,寻找合适的版本。第一步、首先原项目JDK6,要用springbootJDK肯定要升级了。原来的struts2也有漏洞了,也要升级。在不升级其他框架的情况下。jdk2117都可以运行,索性选择jdk21,反正是练手。第二步、str
- 【机会约束、鲁棒优化】机会约束和鲁棒优化研究优化【ccDCOPF】研究(Matlab代码实现)
科研_G.E.M.
matlab概率论开发语言
个人主页欢迎来到本博客❤️❤️博主优势:博客内容尽量做到思维缜密,逻辑清晰,为了方便读者。⛳️座右铭: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本文目录如下:目录1概述机会约束、鲁棒优化与ccDCOPF研究综述1.机会约束规划(ChanceConstrainedProgramming,CCP)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2.鲁棒优化(RobustOptimization,RO)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3.机会约束与鲁棒优化的协同方法
- 24远景能源-动力,10月最后一周面试!【NTAKYsW】
2301_79125642
java
大模型公司收实习啦,入局好机会,全是大佬不卷后端研发实习生简历投递请联系我,牛客会屏蔽邮箱日常实习:面向全体在校生,为符合岗位要求的同学提供为期3个月及以上的项目实践机会。公司介绍下午移动笔试,晚上联通笔试我看到好多投移动都去面试了,但是我没有面试也没有任何消息,而且智联校园上面hr也没有查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随便发的笔试吗...应该投的是什么AI研究中心联通许愿美团商分octl:一面-10.
- golang是如何回收goroutine的
double12gzh
golanggolang
目录1.写在前面2.生命周期3.必备条件1.写在前面微信公众号:[double12gzh]关注容器技术、关注Kubernetes。问题或建议,请公众号留言。本文是基于golang1.13Goroutines易于创建,堆栈小,上下文切换快。由于这些原因,开发人员喜欢它们,并经常使用它们。然而,一个程序如果产生许多这样生命周期很短的goroutine,那将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创建和销毁它们。2.生命周
- 对象的行为-状态影响行为,行为影响状态
Java版蜡笔小新
java学习开发语言
小白Java学习记录4一周掌握Java入门知识学习内容:对象的行为学习产出:你可以传值给方法d.bark(3);方法会运用形参。调用的一方会传入实参。实参是传给方法的值。当传入放后就成了形参。参数跟局部(local)变量是一样的。它有类型与名称,可以在方法内运用。重点是:如果某个方法需要参数,你就一定得传东西给它。那个东西得是适当类型的值。Dogd=newDog();d.bark(3);voidb
- 【IT大学生必会的】 10 种图表线性回归
.Boss.
深度学习开发语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
这段时间,不少同学提到了一些图表的问题。每次在使用matplotlib画图,运用这些图表说明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模糊的,比如说什么时候画什么图合适?其实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来就行。今天的话,我这里举例在线性回归中,最常用的一些图表,应该可以cover绝大多数情况了。其他算法模型适用的图表,咱们在后面再给大家进行总结~至于数据集,表现方式,大家可以根据我给出的代码继续调整即可!那么,在
- 某个业务采用【规则引擎】重构大幅降低耗时
sunnyboy_4
java规则引擎
需求分析需求:由于业务的计算规则比较复杂,经过几年的规则迭代。后续维护维护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花了2周时间进行重构。本次采用Liteflow规则引擎进行重构,好处在于规则配置在xml配置文件中可以清晰的梳理业务的流向,在每个规则节点只负责各自的业务。将复杂的业务对象化,方便后续的维护与更新。项目已经经过生产数据验证。2、业务流程图,这是根据规则引擎编写的,方便后续定位3、这个方案的优点可以动态组合模
- 【职业规划】分享003 -- 什么是职业规划师?
杏子 | 职位规划师
职业与个人发展经验分享
【职业规划】分享003–重新认识职业规划师最近常被问起职业,我说自己在做独立职业规划师。可能很多职场朋友对这个角色还不太熟悉,今天想和大家聊聊这份工作的价值。就像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健康,职业规划师专注解决职业困惑。如果你:▷每天重复机械工作却看不到成长▷想转型却不知从何下手▷面对职业选择总是犹豫不决那么就需要专业的职业规划师来帮你诊断问题,为你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拿我自己的职业历程来举例:2014
- 比较分析:Windsurf、Cody、Cline、Roo Cline、Copilot 和 通义灵码
张3蜂
开源编程语言与开发技术选型与架构设计copilotc#AI编程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发者工具变得越来越智能化,特别是在代码生成、辅助编程等领域,市面上涌现了多种AI驱动的工具。本文将从开源性、集成能力、功能覆盖范围、支持的编程语言、生态兼容性、成本、学习曲线、响应速度、离线支持以及与.NETCore的适配性等十个维度对以下几种产品进行比较:Windsurf、Cody、Cline、RooCline、Copilot和通义灵码。1.开源性Windsurf:
- C/C++学习路线概述
DustWind丶
C/C++c++
根据如下视频和文章总结:想做C语言/C++开发?这些才是你该学的东西!C语言/C++直通企业级开发的详细学习路线节选:肝了半个月,我整理出了这篇嵌入式开发学习学习路线+知识点梳理目录1C/C++学习概述1.1C语言的基础知识1.2C++的基础知识2C/C++编程学习四大件2.1数据结构和算法2.2操作系统2.3计算机网络2.3.1计算机网络分层2.3.2典型协议(以TCP/IP四层模型举例)2.4
- golang-嵌套结构体
lmryBC49
golang开发语言后端
结构体嵌套golang中没有类,他通过结构体来实现其他编程语言中类的相关功能。具名结构体基本语法基本语法golang的结构体嵌套特别简单。type结构体类型1struct{字段类型1字段类型2}//这样就实现了结构体的嵌套type结构体类型2struct{字段类型1字段类型2字段结构体类型1}举例packagestruct_knowledgeimport"fmt"typeWorkerstruct{
- MySQL学习路线
蜡笔小新星
MySQL数据库mysql学习经验分享
本专栏纯干货订阅专栏不迷路以下是一个详细的MySQL学习路线,适合从初学者到中高级用户的逐步学习。整个路线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了必要的知识点和学习材料。第一阶段:基础知识(1-2周)目标:了解数据库的基本概念,熟悉MySQL的基本用法。学习内容:数据库基础什么是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数据库的类型(关系型数据库与非关系型数据库)SQL(结构化查询语言)概述MySQL入门MySQL的
- 常见经典目标检测算法
109702008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目标检测人工智能
ChatGPT目标检测(ObjectDetection)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目的是识别数字图像中的不同对象,并给出它们的位置和类别。近年来,许多经典的目标检测算法被提出并广泛应用。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经典目标检测算法:1.R-CNN(RegionswithCNNfeatures):R-CNN通过使用区域提议方法(如选择性搜索)首先生成潜在的边界框,然后使用卷积神经网络(CNN)提取特征,
- Python 静态方法和类方法
a540366413
Pythonpython
静态方法我们知道在其他语言中静态方法一般使用static修饰,静态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不需要new出对象,直接通过类名就可以访问,也可以通过对象访问。需要使用staticmethod装饰器装饰方法举例:classA:@staticmethoddefstaticfunc():print("A")A.staticfunc()#A类方法类方法和静态方法类似,也可以直接通过类名访问,不过要使用classmet
- Python 正则表达式小结1
大收藏家
Python正则表达式python
[声明]:本文参考了白夜黑雨老师的网页讲解。如有侵权,请与我联系!!!Python正则表达式小结11.正则表达式验证2.特殊元字符及含义3匹配某种字符类型4.正则表达式举例大收藏家说1.正则表达式验证提供两个网站用于正则表达式的验证,可以敲入文本与正则表达式。通过该网站,验证正则表达式的正确性。非常好用!英文网站中文网站2.特殊元字符及含义元字符含义.表示要匹配除了换行符之外的任何单个字符*星号-
- vllm安装踩坑
蒸土豆的技术细节
人工智能
今天是2024/7/18.vllm0.5.2最近一周出了个不好搞的新issue,会遇到torch.ops._C没有rms_norm,或者没有reshape_and_cache_flash这两个属性的问题。完整报错如下:AttributeError:‘_OpNamespace’‘_C_cache_ops’objecthasnoattribute‘reshape_and_cache_flash’Att
- AI图像技术:真实与虚假的博弈
XianxinMao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
标题:AI图像技术:真实与虚假的博弈文章信息摘要:随着AI生成图像技术的快速发展,虚假信息的传播风险急剧增加,引发了社会对信息真实性的广泛担忧。AI生成的图像几乎与真实照片无法区分,可能被用于制造虚假新闻、恶意攻击和商业欺诈,导致社会信任危机。为应对这一挑战,Meta开发了StableSignature技术,通过在AI生成图像中嵌入不可见且防篡改的水印,有效识别和追踪图像来源。这项技术具有鲁棒性、
- Redis高频面试题解析干货,结合核心原理、高频考点和回答技巧
dblens 数据库管理和开发工具
redisredis数据库缓存
一、Redis核心数据结构与实战场景高频问题:Redis有哪些数据结构?分别适合什么场景?回答模板:基础结构(必答):String(缓存、计数器)、Hash(对象存储)、List(队列、栈)、Set(标签、去重)、ZSet(排行榜)扩展加分:Bitmaps(日活统计)、HyperLogLog(UV去重)、GEO(地理位置)场景举例(体现实战能力):例1:用ZSet实现电商销量排行榜,ZINCRBY
- 基于Python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智能化决策的关键要素
AI天才研究院
DeepSeekR1&大数据AI人工智能大模型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编程实践开发语言架构设计
文章目录基于Python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智能化决策的关键要素11.背景介绍2.核心概念与联系数据收集与预处理模型构建与训练决策规则生成与优化决策结果评估与反馈3.核心算法原理具体操作步骤数据挖掘算法机器学习算法优化算法4.数学模型和公式详细讲解举例说明线性回归模型最小二乘法5.项目实践:代码实例和详细解释说明6.实际应用场景金融领域医疗领域供应链管理智能制造7.工具和资源推荐编程语言和开发
- 洛谷每日1题-------Day25__P1424 小鱼的航程(改进版)
__雨夜星辰__
洛谷每日1题算法c++数据结构学习笔记
题目描述有一只小鱼,它平日每天游泳250公里,周末休息(实行双休日),假设从周x开始算起,过了n天以后,小鱼一共累计游泳了多少公里呢?输入格式输入两个正整数x,n,表示从周x算起,经过n天。输出格式输出一个整数,表示小鱼累计游泳了多少公里。输入输出样例输入#1复制310输出#1复制2000说明/提示数据保证,1≤x≤7,1≤n≤106。题解#includeusingnamespacestd;int
- 芒格的“思维格栅“:构建全面的投资分析框架
AGI大模型与大数据研究院
DeepSeekai
芒格的"思维格栅":构建全面的投资分析框架关键词:芒格、思维格栅、投资分析框架、跨学科思维、投资决策摘要:本文深入探讨了芒格的“思维格栅”理论及其在构建全面投资分析框架中的应用。首先介绍了“思维格栅”理论的背景和重要性,接着阐述了其核心概念与联系,包括跨学科思维的原理和架构。通过详细讲解核心算法原理和具体操作步骤,结合数学模型和公式进行举例说明,帮助读者理解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投资分析。随后通过项
- 金融风控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优化
智能计算研究中心
其他
内容概要金融风控算法的透明化研究面临模型复杂性提升与监管合规要求的双重挑战。随着深度学习框架在特征提取环节的广泛应用,算法可解释性与预测精度之间的平衡成为核心议题。本文从联邦学习架构下的数据协作机制出发,结合特征工程优化与超参数调整技术,系统性分析逻辑回归、随机森林等传统算法在召回率、F1值等关键指标上的表现差异。研究同时探讨数据预处理流程对风控决策鲁棒性的影响,并提出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特征权重可视
- 完全 背包
ShiYi22
算法
题目二维数组解法1、确定dp数组以及下标的含义dp[i][j]表示从下标为[0-i]的物品,每个物品可以取无限次,放进容量为j的背包,价值总和最大是多少。2、确定递推公式依然拿dp[1][4]的状态来举例:求取dp[1][4]有两种情况:放物品1还是不放物品1如果不放物品1,那么背包的价值应该是dp[0][4]即容量为4的背包,只放物品0的情况。如果放物品1,那么背包要先留出物品1的容量,目前容量
- Qwen2-Audio:通义千问音频大模型技术解读
kakaZhui
音视频AIGC人工智能pythonchatgpt
引言:从llm到mlm(audio)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发展日新月异,它们在文本理解、生成、推理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能力。然而,交互模态不仅仅依赖于文字,语音、语调、环境音等听觉信息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内容。阿里巴巴通义千问团队,推出了Qwen-Audio系列模型,这里我们一起看下最新版本Qwen2-Audio。Qwen2-Audio不仅能够理解各种音频信号,还能根据语音指令做出文本回应,甚至可以进
- LeetCode 第30题:串联所有单词的子串
Gemini技术窝
leetcode算法数据结构java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道非常有趣的字符串处理题目——LeetCode第30题:串联所有单词的子串。这个问题就像是在寻找字符串中的藏宝图,每个单词都是一个线索,我们需要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找到它们在字符串中的位置。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解锁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吧!文章目录问题描述解题思路高效代码实现详细讲解代码逻辑图解过程举例说明例子1:简单例子例子2:无匹配项例子3:重复单总结问题描述首先,让
- 项目复盘:卓越项目经理的炼金术——将经验转化为组织黄金的终极法则
一、项目复盘的时空坐标:生命周期的涅槃时刻在NASA的项目管理体系中,复盘被称为"经验汲取引擎",位于项目生命周期末端却影响未来所有项目起点。真正的复盘不是终点悼词,而是组织进化的基因重组。阶段复盘:敏捷开发每2周举行迭代复盘,如特斯拉软件团队通过156次迭代复盘将自动驾驶误判率降低83%终局复盘:波音787项目历时7年的终局复盘形成《复合材料应用手册》,成为航空业标准跨期复盘:华为建立"五年战略
- 项目经理的情商革命:从流程管家到团队灵魂的进化之路
在硅谷某头部AI公司的项目复盘会上,技术总监突然摔掉手中的报告:“这种反人类的进度要求,你们PM除了会催进度还懂什么?”会议室陷入死寂时,项目经理Lisa平静起身:“我理解各位连续加班三周的疲惫,上周四发现Tom在工位睡着时,我就该叫停这个冲刺——这是我的失职。现在请大家一起重新评估优先级,我申请将上线日期延后两周。”这段对话后,团队自愿启动“996攻坚”,最终提前3天交付。这个真实案例揭示了一个
- JAVA中的Enum
周凡杨
javaenum枚举
Enum是计算机编程语言中的一种数据类型---枚举类型。 在实际问题中,有些变量的取值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例如,一个星期内只有七天 我们通常这样实现上面的定义:
public String monday;
public String tuesday;
public String wensday;
public String thursday
- 赶集网mysql开发36条军规
Bill_chen
mysql业务架构设计mysql调优mysql性能优化
(一)核心军规 (1)不在数据库做运算 cpu计算务必移至业务层; (2)控制单表数据量 int型不超过1000w,含char则不超过500w; 合理分表; 限制单库表数量在300以内; (3)控制列数量 字段少而精,字段数建议在20以内
- Shell test命令
daizj
shell字符串test数字文件比较
Shell test命令
Shell中的 test 命令用于检查某个条件是否成立,它可以进行数值、字符和文件三个方面的测试。 数值测试 参数 说明 -eq 等于则为真 -ne 不等于则为真 -gt 大于则为真 -ge 大于等于则为真 -lt 小于则为真 -le 小于等于则为真
实例演示:
num1=100
num2=100if test $[num1]
- XFire框架实现WebService(二)
周凡杨
javawebservice
有了XFire框架实现WebService(一),就可以继续开发WebService的简单应用。
Webservice的服务端(WEB工程):
两个java bean类:
Course.java
package cn.com.bean;
public class Course {
private
- 重绘之画图板
朱辉辉33
画图板
上次博客讲的五子棋重绘比较简单,因为只要在重写系统重绘方法paint()时加入棋盘和棋子的绘制。这次我想说说画图板的重绘。
画图板重绘难在需要重绘的类型很多,比如说里面有矩形,园,直线之类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将里面的图形加入一个队列中,这样在重绘时就
- Java的IO流
西蜀石兰
java
刚学Java的IO流时,被各种inputStream流弄的很迷糊,看老罗视频时说想象成插在文件上的一根管道,当初听时觉得自己很明白,可到自己用时,有不知道怎么代码了。。。
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时,我习惯性的从头开始理逻辑,会问自己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把这些简单的问题想明白了,再看代码时才不会迷糊。
IO流作用是什么?
答:实现对文件的读写,这里的文件是广义的;
Java如何实现程序到文件
- No matching PlatformTransactionManager bean found for qualifier 'add' - neither
林鹤霄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No matching PlatformTransactionManager bean found for qualifier 'add' - neither qualifier match nor bean name match!
网上找了好多的资料没能解决,后来发现:项目中使用的是xml配置的方式配置事务,但是
- Row size too large (> 8126). Changing some columns to TEXT or BLOB
aigo
column
原文: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15585602/change-limit-for-mysql-row-size-too-large
异常信息:
Row size too large (> 8126). Changing some columns to TEXT or BLOB or using ROW_FORMAT=DYNAM
- JS 格式化时间
alxw4616
JavaScript
/**
* 格式化时间 2013/6/13 by 半仙
[email protected]
* 需要 pad 函数
* 接收可用的时间值.
* 返回替换时间占位符后的字符串
*
* 时间占位符:年 Y 月 M 日 D 小时 h 分 m 秒 s 重复次数表示占位数
* 如 YYYY 4占4位 YY 占2位<p></p>
* MM DD hh mm
- 队列中数据的移除问题
百合不是茶
队列移除
队列的移除一般都是使用的remov();都可以移除的,但是在昨天做线程移除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没有将遍历出来的全部移除, 代码如下;
//
package com.Thread0715.com;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public class Threa
- Runnable接口使用实例
bijian1013
javathreadRunnablejava多线程
Runnable接口
a. 该接口只有一个方法:public void run();
b. 实现该接口的类必须覆盖该run方法
c. 实现了Runnable接口的类并不具有任何天
- oracle里的extend详解
bijian1013
oracle数据库extend
扩展已知的数组空间,例:
DECLARE
TYPE CourseList IS TABLE OF VARCHAR2(10);
courses CourseList;
BEGIN
-- 初始化数组元素,大小为3
courses := CourseList('Biol 4412 ', 'Psyc 3112 ', 'Anth 3001 ');
--
- 【httpclient】httpclient发送表单POST请求
bit1129
httpclient
浏览器Form Post请求
浏览器可以通过提交表单的方式向服务器发起POST请求,这种形式的POST请求不同于一般的POST请求
1. 一般的POST请求,将请求数据放置于请求体中,服务器端以二进制流的方式读取数据,HttpServletRequest.getInputStream()。这种方式的请求可以处理任意数据形式的POST请求,比如请求数据是字符串或者是二进制数据
2. Form
- 【Hive十三】Hive读写Avro格式的数据
bit1129
hive
1. 原始数据
hive> select * from word;
OK
1 MSN
10 QQ
100 Gtalk
1000 Skype
2. 创建avro格式的数据表
hive> CREATE TABLE avro_table(age INT, name STRING)STORE
- nginx+lua+redis自动识别封解禁频繁访问IP
ronin47
在站点遇到攻击且无明显攻击特征,造成站点访问慢,nginx不断返回502等错误时,可利用nginx+lua+redis实现在指定的时间段 内,若单IP的请求量达到指定的数量后对该IP进行封禁,nginx返回403禁止访问。利用redis的expire命令设置封禁IP的过期时间达到在 指定的封禁时间后实行自动解封的目的。
一、安装环境:
CentOS x64 release 6.4(Fin
- java-二叉树的遍历-先序、中序、后序(递归和非递归)、层次遍历
bylijinnan
java
import java.util.Linked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Stack;
public class BinTreeTraverse {
//private int[] array={ 1, 2, 3, 4, 5, 6, 7, 8, 9 };
private int[] array={ 10,6,
- Spring源码学习-XML 配置方式的IoC容器启动过程分析
bylijinnan
javaspringIOC
以FileSystemXmlApplicationContext为例,把Spring IoC容器的初始化流程走一遍:
ApplicationContext context = new FileSystemXmlApplicationContext
("C:/Users/ZARA/workspace/HelloSpring/src/Beans.xml&q
- [科研与项目]民营企业请慎重参与军事科技工程
comsci
企业
军事科研工程和项目 并非要用最先进,最时髦的技术,而是要做到“万无一失”
而民营科技企业在搞科技创新工程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技术的先进性,而对先进技术带来的风险考虑得不够,在今天提倡军民融合发展的大环境下,这种“万无一失”和“时髦性”的矛盾会日益凸显。。。。。。所以请大家在参与任何重大的军事和政府项目之前,对
- spring 定时器-两种方式
cuityang
springquartz定时器
方式一:
间隔一定时间 运行
<bean id="updateSessionIdTask" class="com.yang.iprms.common.UpdateSessionTask" autowire="byName" />
<bean id="updateSessionIdSchedule
- 简述一下关于BroadView站点的相关设计
damoqiongqiu
view
终于弄上线了,累趴,戳这里http://www.broadview.com.cn
简述一下相关的技术点
前端:jQuery+BootStrap3.2+HandleBars,全站Ajax(貌似对SEO的影响很大啊!怎么破?),用Grunt对全部JS做了压缩处理,对部分JS和CSS做了合并(模块间存在很多依赖,全部合并比较繁琐,待完善)。
后端:U
- 运维 PHP问题汇总
dcj3sjt126com
windows2003
1、Dede(织梦)发表文章时,内容自动添加关键字显示空白页
解决方法:
后台>系统>系统基本参数>核心设置>关键字替换(是/否),这里选择“是”。
后台>系统>系统基本参数>其他选项>自动提取关键字,这里选择“是”。
2、解决PHP168超级管理员上传图片提示你的空间不足
网站是用PHP168做的,反映使用管理员在后台无法
- mac 下 安装php扩展 - mcrypt
dcj3sjt126com
PHP
MCrypt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加密算法扩展库,它包括有22种算法,phpMyAdmin依赖这个PHP扩展,具体如下:
下载并解压libmcrypt-2.5.8.tar.gz。
在终端执行如下命令: tar zxvf libmcrypt-2.5.8.tar.gz cd libmcrypt-2.5.8/ ./configure --disable-posix-threads --
- MongoDB更新文档 [四]
eksliang
mongodbMongodb更新文档
MongoDB更新文档
转载请出自出处: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174104
MongoDB对文档的CURD,前面的博客简单介绍了,但是对文档更新篇幅比较大,所以这里单独拿出来。
语法结构如下:
db.collection.update( criteria, objNew, upsert, multi)
参数含义 参数
- Linux下的解压,移除,复制,查看tomcat命令
y806839048
tomcat
重复myeclipse生成webservice有问题删除以前的,干净
1、先切换到:cd usr/local/tomcat5/logs
2、tail -f catalina.out
3、这样运行时就可以实时查看运行日志了
Ctrl+c 是退出tail命令。
有问题不明的先注掉
cp /opt/tomcat-6.0.44/webapps/g
- Spring之使用事务缘由(3-XML实现)
ihuning
spring
用事务通知声明式地管理事务
事务管理是一种横切关注点。为了在 Spring 2.x 中启用声明式事务管理,可以通过 tx Schema 中定义的 <tx:advice> 元素声明事务通知,为此必须事先将这个 Schema 定义添加到 <beans> 根元素中去。声明了事务通知后,就需要将它与切入点关联起来。由于事务通知是在 <aop:
- GCD使用经验与技巧浅谈
啸笑天
GC
前言
GCD(Grand Central Dispatch)可以说是Mac、iOS开发中的一大“利器”,本文就总结一些有关使用GCD的经验与技巧。
dispatch_once_t必须是全局或static变量
这一条算是“老生常谈”了,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强调一次,毕竟非全局或非static的dispatch_once_t变量在使用时会导致非常不好排查的bug,正确的如下: 1
- linux(Ubuntu)下常用命令备忘录1
macroli
linux工作ubuntu
在使用下面的命令是可以通过--help来获取更多的信息1,查询当前目录文件列表:ls
ls命令默认状态下将按首字母升序列出你当前文件夹下面的所有内容,但这样直接运行所得到的信息也是比较少的,通常它可以结合以下这些参数运行以查询更多的信息:
ls / 显示/.下的所有文件和目录
ls -l 给出文件或者文件夹的详细信息
ls -a 显示所有文件,包括隐藏文
- nodejs同步操作mysql
qiaolevip
学习永无止境每天进步一点点mysqlnodejs
// db-util.js
var mysql = require('mysql');
var pool = mysql.createPool({
connectionLimit : 10,
host: 'localhost',
user: 'root',
password: '',
database: 'test',
port: 3306
});
- 一起学Hive系列文章
superlxw1234
hiveHive入门
[一起学Hive]系列文章 目录贴,入门Hive,持续更新中。
[一起学Hive]之一—Hive概述,Hive是什么
[一起学Hive]之二—Hive函数大全-完整版
[一起学Hive]之三—Hive中的数据库(Database)和表(Table)
[一起学Hive]之四-Hive的安装配置
[一起学Hive]之五-Hive的视图和分区
[一起学Hive
- Spring开发利器:Spring Tool Suite 3.7.0 发布
wiselyman
spring
Spring Tool Suite(简称STS)是基于Eclipse,专门针对Spring开发者提供大量的便捷功能的优秀开发工具。
在3.7.0版本主要做了如下的更新:
将eclipse版本更新至Eclipse Mars 4.5 GA
Spring Boot(JavaEE开发的颠覆者集大成者,推荐大家学习)的配置语言YAML编辑器的支持(包含自动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