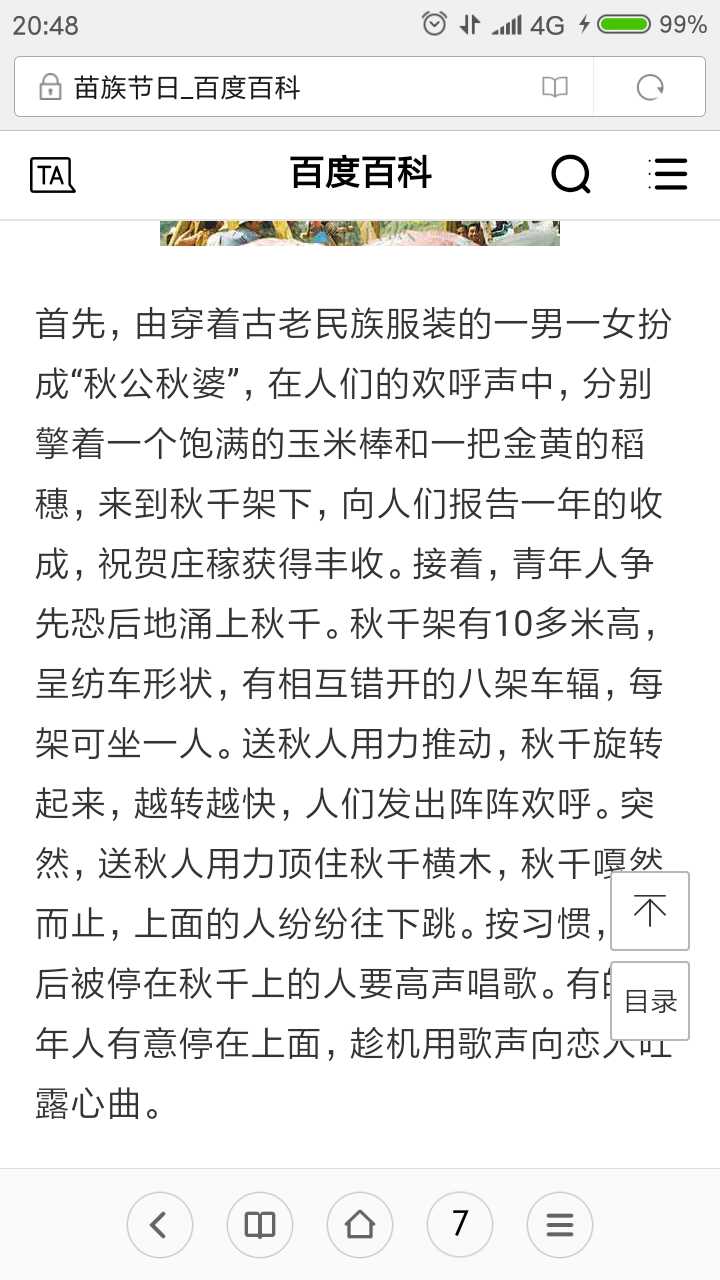舒公子自觉:人生何乐?击节当歌,对酒当酌是也。
于是他果断地禀明父母云游四方去了。
这位舒公子呢,就是舒子彻。
舒子彻云游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他想去,还因为某姓楚的无耻孔雀不要脸地拐来个小媳妇,秦家那书呆子又鲜少出门,于是,本是姓楚的享受的掷果盈车成了他的烦心事。
惹不起,咱躲得起呀。
去江南看水,到塞北看雪,寻山林养性,觅江海狂歌,乐淘淘驰骋天地去也!
嗯,舒公子想得挺美。
可惜事实没有那么美。
还没驰骋得一半,舒公子便摔断了腿。
如今在杨家混吃混喝的舒公子只觉得,人生还真是奇妙。
这一切,得从舒子彻离家说起。
平心说,除了脸白一些人懒一些,舒子彻医术还不错。
医术不错的舒某人先晃荡着到了江南,赏了一番小桥流水,然后听人说起苗岭,突然想起那地方似乎长了挺多药材的,于是高高兴兴地准备去看一看。
倒不是有什么名贵药材非那里不可,不过是兴之所至,便准备去了。
这地方山连着山,水牵着水,有密密茫茫的林子和叽叽喳喳的鸟儿。舒子彻到的季节,早晨起来的时候,通常会看到云雾拦腰把山折断了似的,宛如云间风里。
刚到的时候,他住在一间小客栈,闲来无事,帮人把把脉,偶尔兴起,上山采釆药。
舒子彻摔断腿,就因为他某次的“兴之所至”。
说来十分的不英雄,他其实只是去采药,一不小心踩空了。
他只记得踩空了,掉下去,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顺着那斜坡往下滑,一路磕磕碰碰,于是,他十分不争气地晕过去了。
似乎是下雨了,脸上有点点的水滴。他试着睁开眼,却先是听到了伴着叮铃铃清脆的小铃铛声音的甜笑,继而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影子,衣服上头上都是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眼睛再睁开些,是一个苗家小姑娘,正笑着盯着他看,脸颊上一双浅浅的小酒窝,看起来无比的甜。
那姑娘看到他睁开眼睛,便开始喊:“他醒了,醒了,没死呢!”声音很清脆,像林间的百灵鸟。
后来入住了杨家的舒子彻才听说,原来那日,几个姑娘玩到了水边,正逗着笑着打水仗,跑着跑着,便看到了一个躺在水边的人,还很不幸的洒了些水在那人身上。
那个不幸的人就是他。
酒窝姑娘和她的小伙伴们找了帮手,把舒子彻拖到了她家里,找了大夫给他裹了伤,央着哥哥给他洗了脸换了衣服,这才发现这花脸猫长得挺白。
这花脸猫其他的地方倒多是擦伤,只是有条腿摔断了,哪儿也去不了。
他很干脆,这家人也很干脆,便听了他摊些伙食费在这里住着提议,收留了这只断腿花脸猫。
既然都住下了,舒子彻怎么也得认识一下自己蹭吃蹭喝的是谁,于是知道了这家人姓杨,那姑娘的父亲叫做杨治杰,哥哥叫做杨春华,姑娘叫做杨春谣。至于母亲的名字,当然是不能直接问的。
其实姑娘的名字,他还是后来一点才知道的,开始的时候,他跟着人家唤“阿瑶”。
伤筋动骨一百天,不能蹦不能跳的日子实在无聊,于是舒子彻托杨春华帮他买了一堆书,预备效仿秦书呆。
杨春谣来给这只行动不便的花脸猫送药的时候,他正躺在一张小榻上看书,懒懒散散的模样,也不知道看进去了多少。
杨小姑娘是个好学的,招呼了舒子彻吃药之后,很认真地问了他看的是什么书。
舒子彻笑了笑,说了书名。
小姑娘神色认真:“你教我认字好不好?”
舒公子自然对闺阁女子要读书学字没有什么成见,欣然答应,然后提笔,先写了姑娘的名字,让她跟着学。
姑娘看着舒夫子大笔一挥写的“杨春瑶”,咯咯地笑了:“原来夫子也会错呀,我可是会写我的名字的呢。”
说完,她拿过舒子彻手中的笔,认认真真地写了“杨春谣”三个字,然后笑着说:“是这样呢。”
舒子彻看着眼前这个笑得甜甜的、声音清脆好听的小丫头,蓦然觉得,春谣很应景,春天的歌谣,大约就是这样子了。
舒夫子还算尽心,在伤筋动骨一百天未满之际,便想着为这小书生谋福利,说他看的书有些晦涩,要出门给她买几本新的。
其实这事儿,小书生自己就可以解决,不过是舒公子待不住了想出去晃荡,于是哄人家小书生说:“你哪知道什么好赖,万一人家骗你怎么办?”然后不容反驳地,蹦哒着出了门,急得人小书生赶紧跟上,生怕这人出了个好歹。
舒夫子被小书生领着到了集市上,还没买着书呢,便被一些平日里见不着的小玩意儿吸引了,活脱脱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东走走西窜窜,若不是腿还伤着,指不定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杨小书生一脸迷茫:“夫子,说好的买书呢?”
舒夫子摆摆手:“不急不急,总能买到的嘛。”
小书生没再言语,继续看着他蹦哒,皱着眉思量,这伤会不会被他蹦哒得重一些?
这事儿当然不在舒夫子的思量范围内,人乐呵着呢。好不容易晃荡到了一个书摊,顺手拎起一本,扔向那跟在后面的小姑娘,说:“拿好,以后咱就学这个了。”
等到舒夫子正正经经地要教教这小书生的时候,却发现她拿出来的是一本《诗经》,舒夫子瞟了一眼,觉得实在不适合用来启蒙,却也懒得再挑,觉得没什么地教了起来。
诗三百开篇便是“关关雎鸠”。恰好,教这篇的时候,正逢着赶秋节,舒夫子欢天喜地地去凑热闹,待到杨春华给他解释完这节日的时候,他回头,便看到一个坐在高高秋千上的小青年正对着他那小徒弟唱起歌来,于是他懒懒散散地笑:“这便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了。”
小姑娘脸上飞来一抹红,瞪了这不着调的夫子一眼便跑开了。
小姑娘跑了,这不着调的夫子却没跑,笑嘻嘻地拿着一碗苗家自酿的米酒,朝着好几个抛来秋波的小姑娘眨了眼。
回去的时候,舒夫子已然微醺,却没忘了教徒弟这事,也不论教到了哪里,顺手一翻便念了起来。
小姑娘看他念这句的时候,眸子里像是嵌了满天星辰,看得她呆呆地跟着念:“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舒子彻跟她解释的时候,心头突然爬上来一双甜甜的酒窝,他笑着摇摇头,想着怕是酒喝多了,于是打发了小徒弟,要自个儿醒醒酒。
酒是没有醒,反是借着酒劲,顺势写了这篇“野有蔓草”,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最后缀上了小徒弟的名字。
等到舒子彻睡醒的时候,便偷偷把那篇字藏了起来,一副没事人的样子,继续有事没事瞎晃荡,偶尔得闲,教小姑娘念诗经。
当然,在赶秋节露过面之后,许多姑娘便知道了杨家住着这么位好看的人,于是,本着好看的人当大家看的道理,这些更大胆的小姑娘常常拎了条腰带或是拿了块手帕就过来,要围观这位折了腿依旧好看的夫子,吵嚷着要当小徒弟。
这事儿闹得舒夫子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腰带手帕的,铁定不能收,这他还是知道的,可是教人念书这事儿,总不怎么好推脱。
正思量着怎么办的时候,自家小徒弟便气鼓鼓地给他送了药来,一副“我很气不要跟我说话”的样子,一言不发。
端了药的舒子彻隔着药碗,看着这气鼓鼓的小丫头,很想往她脸颊戳一戳,于是他果真放下碗,伸手戳了一下。小姑娘很生气,拍开他的爪子,碗也没要就走了。
舒子彻笑笑,想着哪位不长眼的竟惹了这位小祖宗,害他无端受了牵连。
等到该念书的时候了,小姑娘还没来,舒子彻便一瘸一拐地去找。
他已经在这儿住了两个多月,这会儿已经好了七七八八,不用蹦哒了。
小姑娘没有开门,隔着门,语气不善地说:“你走吧,我另寻个夫子去,反正你也好了,打哪儿来,便到哪儿去吧。”
无端吃了闭门羹,舒子彻只好讪讪地回了屋。
舒子彻正没趣地收拾着桌子,寻思着怎么再哄一哄那小姑娘,突然一阵风似的,门便被推开了,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头,同冲进来的小姑娘大眼瞪小眼。
小姑娘一脸纠结,终于一咬牙,问道:“夫子你会看病的吧?”
舒子彻疑惑地点点头。
小姑娘又一咬牙:“那你给我看看成不成?我觉得我病了。”
舒子彻看着这面色红润的小姑娘,没瞧出哪儿有什么病,于是招呼她坐下,伸手搭上了她的脉搏。
舒大夫很疑惑,这小姑娘点儿事也没有,怎么会以为生病好玩,上赶着说自己病了呢?于是他好言安慰:“没事的,你没生病,回去休息吧,别多想,嗯?”
小姑娘急得快要哭出来:“可是,我怎么觉得我病了呀?还是那种黑心烂肺的病。”
舒公子、舒大夫、舒夫子以及姓舒的,此刻通通手足无措,有种挠心挠肝的感觉,声音不自觉地低了几分:“嗯?怎么会?”
小姑娘语气里含了哽咽:“爹爹说,来的都是客人,对客人,应当热情友好些,可是……可是,我这些日子,见着那些姐姐妹妹,就觉得心里很堵,恨不能把她们都轰回去才好……”
小姑娘的眼眶已经红了,舒子彻愣了好大一会儿,她不等回答,便又自己说起来:“夫子,若是姐姐妹妹们瞧着我哪块刺绣或是哪个发饰好看,我给她也是行的……可是夫子……我却很小气……我想着……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夫子……”
舒子彻起身预备给她倒杯水,听到这里没回过神来,手被烫了一下,才发现杯子已经满了。
小姑娘没有发现异常,自顾自地说下去:“其实本来,夫子若是收了谁的东西,想着便是可以喝喜酒了……我以前挺喜欢喝喜酒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却偏偏不喜欢喝夫子的喜酒……”
舒子彻还愣着,突然见小姑娘眼泪掉了下来,他心里一揪,自然地伸手接着了那滴眼泪,然后,抬手擦干了她的眼泪,顺势坐下,把小姑娘搂进怀里:“别哭啊,阿谣不小气的,阿谣很好。”
“我只做你一个人的夫子,也不让你喝我的喜酒,”他看着还有些纠结的小姑娘,揉了揉她的头发,心软得要命,“我只收你的东西,然后,我们请她们喝我们的喜酒,好不好?”
小姑娘瞪大眼睛看着他,他叹了口气,摸出了一张纸,声音温和:“其实,我从挺早以前就这么想了。”
“大约,从看到那甜的要命的酒窝开始。”
小姑娘打开那张纸,是她这位夫子微醺时教的诗句,说是对一个姑娘一见倾心。
一个不负责任的“番外”:
后来,舒公子志得意满,拐带了媳妇儿回去时,姓楚的孔雀出来接他,两人天南地北,随后哈哈大笑,心里想着:气死那姓秦的书呆子!
一个不负责任的后记:
关于“赶秋节”,来自于百度,不过百度“苗族节日”跟百度“赶秋节”似乎不太一样。最后,用的是前者,如有不妥,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