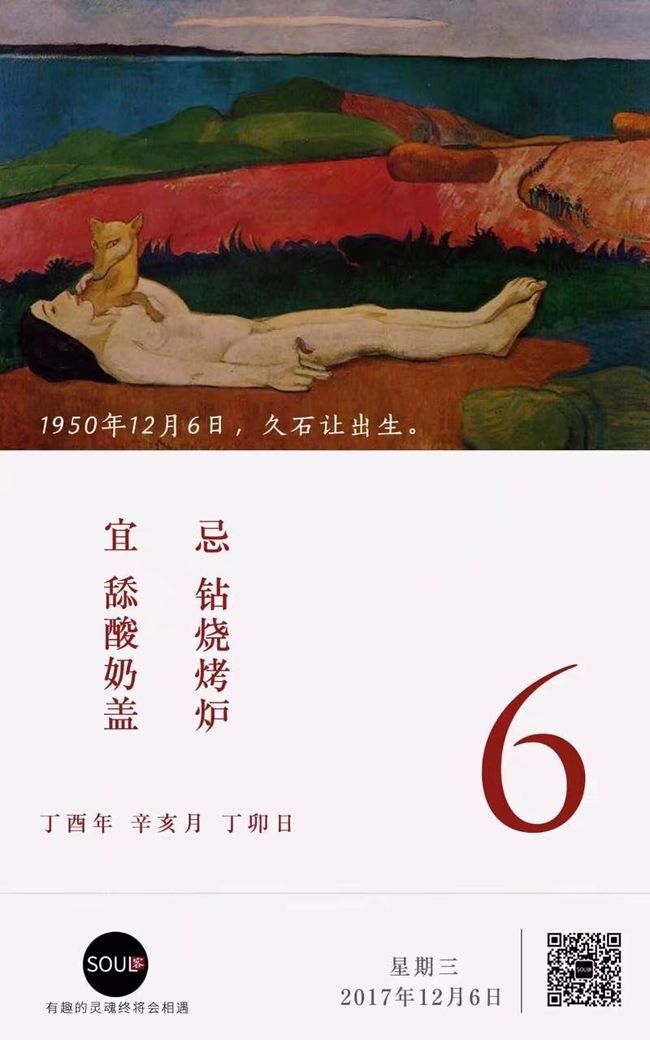- android系统selinux中添加新属性property
辉色投像
1.定位/android/system/sepolicy/private/property_contexts声明属性开头:persist.charge声明属性类型:u:object_r:system_prop:s0图12.定位到android/system/sepolicy/public/domain.te删除neverallow{domain-init}default_prop:property
- 铭刻于星(四十二)
随风至
69夜晚,绍敏同学做完功课后,看了眼房外,没听到动静才敢从书包的夹层里拿出那个心形纸团。折痕压得很深,都有些旧了,想来是已经写好很久了。绍敏同学慢慢地、轻轻地捏开折叠处,待到全部拆开后,又反复抚平纸张,然后仔细地一字字默看。只是开头的三个字是第一次看到,让她心漏跳了几拍。“亲爱的绍敏:从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说,怕影响你学习。六年级的时候听说有人跟你表白,你接受了,我很难过,但
- 底层逆袭到底有多难,不甘平凡的你准备好了吗?让吴起给你说说
造命者说
底层逆袭到底有多难,不甘平凡的你准备好了吗?让吴起给你说说我叫吴起,生于公元前440年的战国初期,正是群雄并起、天下纷争不断的时候。后人说我是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是兵家代表人物。评价我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因变法得罪守旧贵族,被人乱箭射死。我出生在卫国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从年轻时候起就不甘平凡
- 10月|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读书笔记-01
Tracy的小书斋
本书的作者是俞敏洪,大家都很熟悉他了吧。俞敏洪老师是我行业的领头羊吧,也是我事业上的偶像。本日摘录他书中第一章中的金句:『一个人如果什么目标都没有,就会浑浑噩噩,感觉生命中缺少能量。能给我们能量的,是对未来的期待。第一件事,我始终为了进步而努力。与其追寻全世界的骏马,不如种植丰美的草原,到时骏马自然会来。第二件事,我始终有阶段性的目标。什么东西能给我能量?答案是对未来的期待。』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便
- 谢谢你们,爱你们!
鹿游儿
昨天家人去泡温泉,二个孩子也带着去,出发前一晚,匆匆下班,赶回家和孩子一起收拾。饭后,我拿出笔和本子(上次去澳门时做手帐的本子)写下了1\2\3\4\5\6\7\8\9,让后让小壹去思考,带什么出发去旅游呢?她在对应的数字旁边画上了,泳衣、泳圈、肖恩、内衣内裤、tapuy、拖鞋……画完后,就让她自己对着这个本子,将要带的,一一带上,没想到这次带的书还是这本《便便工厂》(晚上姑婆发照片过来,妹妹累得
- 2021年12月19日,春蕾教育集团团建活动感受——黄晓丹
黄错错加油
感受:1.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游戏环节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得到了锻炼,也增长了不少知识。2.游戏过程中,我们贡献的是个人力量,展现的是团队的力量。它磨合的往往不止是工作的熟悉,更是观念上契合度的贴近。3.这和工作是一样的道理。在各自的岗位上,每个人摆正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才能,并团结一致劲往一处使,才能实现最大的成功。新知:1.团队精神需要不断地创新。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人们
- 《投行人生》读书笔记
小蘑菇的树洞
《投行人生》----作者詹姆斯-A-朗德摩根斯坦利副主席40年的职业洞见-很短小精悍的篇幅,比较适合初入职场的新人。第一部分成功的职业生涯需要规划1.情商归为适应能力分享与协作同理心适应能力,更多的是自我意识,你有能力识别自己的情并分辨这些情绪如何影响你的思想和行为。2.对于初入职场的人的建议,细节,截止日期和数据很重要截止日期,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请老板为你所有的任务进行优先级排序。和老板喝咖啡的好
- 《策划经理回忆录之二》
路基雅虎
话说三年变六年,飘了,飘了……眨眼,2013年5月,老吴回到了他的家乡——油城从新开启他的工作幻想症生涯。很庆幸,这是一家很有追求,同时敢于尝试的,且实力不容低调的新星房企——金源置业(前身泰源置业)更值得庆幸的是第一个盘就是油城十路的标杆之一:金源盛世。2013年5月,到2015年11月,两年的陪伴,迎来了一场大爆发。2000个筹,5万/筹,直接回笼1个亿!!!这……让我开始认真审视这座看似五线
- Long类型前后端数据不一致
igotyback
前端
响应给前端的数据浏览器控制台中response中看到的Long类型的数据是正常的到前端数据不一致前后端数据类型不匹配是一个常见问题,尤其是当后端使用Java的Long类型(64位)与前端JavaScript的Number类型(最大安全整数为2^53-1,即16位)进行数据交互时,很容易出现精度丢失的问题。这是因为JavaScript中的Number类型无法安全地表示超过16位的整数。为了解决这个问
- 绘本讲师训练营【24期】8/21阅读原创《独生小孩》
1784e22615e0
24016-孟娟《独生小孩》图片发自App今天我想分享一个蛮特别的绘本,讲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是属于这个群体,80后的独生小孩。这是一本中国绘本,作者郭婧,也是一个80厚。全书一百多页,均为铅笔绘制,虽然为黑白色调,但并不显得沉闷。全书没有文字,犹如“默片”,但并不影响读者对该作品的理解,反而显得神秘,梦幻,給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作者在前蝴蝶页这样写到:“我更希望父母和孩子一起分享这本书,使他
- 我校举行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暨名师专业工作室工作交流活动
李蕾1229
为促进我校教师专业发展,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带头作用,11月6日下午,我校举行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暨名师专业工作室工作交流活动。图片发自App会议由教师发展处李蕾主任主持,首先,由范校长宣读新老教师结对名单及双方承担职责。随后,两位新调入教师陈玉萍、莫正杰分别和他们的师傅鲍元美、刘召彬老师签订了师徒结对协议书。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师徒拥抱、握手。有了师傅就有了目标有了方向,相信两位新教师在师
- 向内而求
陈陈_19b4
10月27日,阴。阅读书目:《次第花开》。作者:希阿荣博堪布,是当今藏传佛家宁玛派最伟大的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仁波切颇具影响力的弟子之一。多年以来,赴海内外各地弘扬佛法,以正式授课、现场开示、发表文章等多种方法指导佛学弟子修行佛法。代表作《寂静之道》、《生命这出戏》、《透过佛法看世界》自出版以来一直是佛教类书籍中的畅销书。图片发自App金句:1.佛陀说,一切痛苦的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自身及外
- 2021-08-26
影幽
在生活中,女人与男人的感悟往往有所不同。人生最大的舞台就是生活,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表演都无法躲避。在生活中,遇事不要急躁,不要急于下结论,尤其生气时不要做决断,要学会换位思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复杂的事情尽量简单处理,千万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永远不要扭曲,别人善意,无药可救。昨天是张过期的支票,明天是张信用卡,只有今天才是现金,要善加利用!执着的攀登者不必去与别人比较自己的
- 高级编程--XML+socket练习题
masa010
java开发语言
1.北京华北2114.8万人上海华东2,500万人广州华南1292.68万人成都华西1417万人(1)使用dom4j将信息存入xml中(2)读取信息,并打印控制台(3)添加一个city节点与子节点(4)使用socketTCP协议编写服务端与客户端,客户端输入城市ID,服务器响应相应城市信息(5)使用socketTCP协议编写服务端与客户端,客户端要求用户输入city对象,服务端接收并使用dom4j
- 抖音乐买买怎么加入赚钱?赚钱方法是什么
测评君高省
你会在抖音买东西吗?如果会,那么一定要免费注册一个乐买买,抖音直播间,橱窗,小视频里的小黄车买东西都可以返佣金!省下来都是自己的,分享还可以赚钱乐买买是好省旗下的抖音返佣平台,乐买买分析社交电商的价值,乐买买属于今年难得的副业项目风口机会,2019年错过做好省的搞钱的黄金时期,那么2022年千万别再错过乐买买至于我为何转到高省呢?当然是高省APP佣金更高,模式更好,终端用户不流失。【高省】是一个自
- 2018-07-23-催眠日作业-#不一样的31天#-66小鹿
小鹿_33
预言日:人总是在逃避命运的路上,与之不期而遇。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名词,叫做自证预言;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定律叫做,墨菲定律;在灵修派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则,叫做吸引力法则。这3个领域的词,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在告诉人们一个现象:你越担心什么,就越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同样的道理,你越想得到什么,就应该要积极地去创造什么。无论是自证预言,墨菲定律还是吸引力法则,对人都有正反2个维度的影响
- 本周第二次约练
2cfbdfe28a51
中原焦点团队中24初26刘霞2021.12.3约练161次,分享第368天当事人虽然是带着问题来的,但是咨询过程中发现,她是经过自己不断地调整和努力才走到现在的,看到当事人的不容易,找到例外,发现资源,力量感也就随之而来。增强画面感,或者说重温,会给当事人带来更深刻的感受。
- 今日联对0306
诗图佳得
自对联:烟销皓月临江浒,水漫金山荡塔裙。一一肖士平2020.3.6.1、试对肖老师联:烟销皓月临江浒,夜笼寒沙梦晚舟。耀哥求正2、试对萧老师联:烟销浩月临江浒,雾散乾坤解汉城。秀霞习作请各位老师校正3、自对联:烟销皓月临江浒,水漫金山荡塔裙。一一肖士平2020.3.6.4、试对肖老师垫场联:烟销皓月临江浒,雾锁寒林缈葉丛。小智求正[抱拳]5、试对肖老师联:烟销皓月临江浒;风卷乱云入峰巅。一一五品6
- 每日一题——第八十九题
互联网打工人no1
C语言程序设计每日一练c语言
题目:在字符串中找到提取数字,并统计一共找到多少整数,a123xxyu23&8889,那么找到的整数为123,23,8889//思想:#include#include#includeintmain(){charstr[]="a123xxyu23&8889";intcount=0;intnum=0;//用于临时存放当前正在构建的整数。boolinNum=false;//用于标记当前是否正在读取一个整
- 怎么起诉借钱不还的人?怎样起诉欠款不还的人?
影子爱学习
怎么起诉借钱不还的人?怎样起诉欠款不还的人?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我们可以匹配专业律师。例如:婚姻家庭(离婚纠纷)、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债权债务、房产(继承)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人身损害、公司相关法律事务(法律顾问)等咨询推荐手机/微信:15633770876【全国案件皆可】借钱不还起诉对方需要哪些资料起诉欠钱不还的,一般需要的材料包括以下这些:借据、收据、欠条、付款凭证等证据,以及向
- 2019-12-22-22:30
涓涓1016
今天是冬至,写下我的日更,是因为这两天的学习真的是能量的满满,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让我看到了这两年这几年的过程中我所接受那些痛苦的来源。一切的根源和痛苦都来自于人生,家庭,而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你这个灵魂在那一刻选择他们作为你的爸爸和妈妈来的,所以你得接受他,你得接纳他,他就是因为他的存在而给你的学习和成长带来这些痛苦,那其实是你必然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你去接纳的
- Python教程:一文了解使用Python处理XPath
旦莫
Python进阶python开发语言
目录1.环境准备1.1安装lxml1.2验证安装2.XPath基础2.1什么是XPath?2.2XPath语法2.3示例XML文档3.使用lxml解析XML3.1解析XML文档3.2查看解析结果4.XPath查询4.1基本路径查询4.2使用属性查询4.3查询多个节点5.XPath的高级用法5.1使用逻辑运算符5.2使用函数6.实战案例6.1从网页抓取数据6.1.1安装Requests库6.1.2代
- 谁家酒器最绝唱,藏在酒厂人未知?景阳冈酒厂先秦藏品大揭秘
李虓酒评论
文/王赛时中国的酒器酒具历史久远,举世闻名。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到世界各国的大型博物馆,都以能够收藏中国古代酒具而夸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山东阳谷景阳冈酒厂,默默地收藏了两千件中国酒器。这些酒器,就封藏在景阳冈的酒道馆里。其中有一些青铜酒器,一睡就是三、四千年,堪称无声国宝,堪作无字史书!今天,我将引领诸位首先窥视一下景阳冈酒道馆的9件先秦藏品,你自己来说震撼不震撼。提示:这只是景
- 基于社交网络算法优化的二维最大熵图像分割
智能算法研学社(Jack旭)
智能优化算法应用图像分割算法php开发语言
智能优化算法应用:基于社交网络优化的二维最大熵图像阈值分割-附代码文章目录智能优化算法应用:基于社交网络优化的二维最大熵图像阈值分割-附代码1.前言2.二维最大熵阈值分割原理3.基于社交网络优化的多阈值分割4.算法结果:5.参考文献:6.Matlab代码摘要:本文介绍基于最大熵的图像分割,并且应用社交网络算法进行阈值寻优。1.前言阅读此文章前,请阅读《图像分割:直方图区域划分及信息统计介绍》htt
- 今又重阳
芮峻
今又重阳图片发自App白露成霜菊花黄,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登高远望,君不见,那来时路上少年,青丝已染雪霜。落日一点一点西坠,谁有力量,托住使其回往。转眼缺了大半,又能怎样?江天两茫茫。给我一壶烈酒,我要敬那斜阳,看谁先醉?笑指西天红了一片,借点酒力,老夫聊发一次少年狂。老严.2019年重阳节.杭州
- 2020.11.19
隆非凡
日精进,今日体验:在维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把源头找到,在进行下一步开始。不要停留在一个点上,合理调整心态,把当下事做好。
- 18-115 一切思考不能有效转化为行动,都TM是扯淡!
成长时间线
7月25号写了一篇关于为什么会断更如此严重的反思,然而,之后日更仅仅维持了一周,又出现了这次更严重的现象。从8月2号到昨天8月6号,5天!又是5天没有更文!虽然这次断更时间和上次一样,那为什么说这次更严重?因为上次之后就分析了问题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按理说应该会好转,然而,没过几天严重断更的现象再次出现,想想,经过反思,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与改变,这让我有些担忧。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我就真的
- 2018/02/12
Tracy_zhang
人生并不在于获取,更在于放得下。放下一粒种子,收获一棵大树;放下一处烦恼,收获一个惊喜;放下一种偏见,收获一种幸福;放下一种执著,收获一种自在。放下既是一种理性抉择,也是一种豁达美。只要看得开放得下,何愁没有快乐的春莺在啼鸣,何愁没有快乐的泉溪在歌唱,何愁没有快乐的鲜花绽放!
- 郎朗大婚娶公主:所有光环的背后,都是十年如一日的自律
简小尘
近日,关于郎朗大婚的新闻上了热搜,看了新娘的照片,既有天使般的面容,更有魔鬼般的身材,关键是人家还身世好,又有才华,这真的是让所有男人羡慕嫉妒恨哪。有些人不禁会想,“凭什么郎朗的人生就象开挂了一样,可我却每天都活得这么狼狈!”其实,每个开挂的人生背后,都是苦行僧般的自律。01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练琴不能只靠兴趣,更需要自律!我们先来看一下朗朗在小时候的作息时间表:早晨5:45起床,练琴1小时。中午
- 《中华小厨师》单行VS爱藏:姜是老的辣,书是新的好
cicoky
《汉书·郦食其传》有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吃饱饭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而吃好饭却是每一个人的最终追求。于是,厨师这一职业孕育而生,其渊源之久,甚至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奴隶时代。职业本身无贵贱,但职业能力却有高低之分。所以一家餐馆生意好不好,厨师的水平决定一切,而站在所有厨师顶端的就被称之为“特级厨师”。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个关于“特级厨师刘昴星”的故事。连载历程1995年第4
- java线程Thread和Runnable区别和联系
zx_code
javajvmthread多线程Runnable
我们都晓得java实现线程2种方式,一个是继承Thread,另一个是实现Runnable。
模拟窗口买票,第一例子继承thread,代码如下
package thread;
public class Thread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hread1 t1 = new Thread1(
- 【转】JSON与XML的区别比较
丁_新
jsonxml
1.定义介绍
(1).XML定义
扩展标记语言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用于标记电子文件使其具有结构性的标记语言,可以用来标记数据、定义数据类型,是一种允许用户对自己的标记语言进行定义的源语言。 XML使用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文档类型定义来组织数据;格式统一,跨平台和语言,早已成为业界公认的标准。
XML是标
- c++ 实现五种基础的排序算法
CrazyMizzz
C++c算法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辅助函数,交换两数之值
template<class T>
void mySwap(T &x, T &y){
T temp = x;
x = y;
y = temp;
}
const int size = 10;
//一、用直接插入排
- 我的软件
麦田的设计者
我的软件音乐类娱乐放松
这是我写的一款app软件,耗时三个月,是一个根据央视节目开门大吉改变的,提供音调,猜歌曲名。1、手机拥有者在android手机市场下载本APP,同意权限,安装到手机上。2、游客初次进入时会有引导页面提醒用户注册。(同时软件自动播放背景音乐)。3、用户登录到主页后,会有五个模块。a、点击不胫而走,用户得到开门大吉首页部分新闻,点击进入有新闻详情。b、
- linux awk命令详解
被触发
linux awk
awk是行处理器: 相比较屏幕处理的优点,在处理庞大文件时不会出现内存溢出或是处理缓慢的问题,通常用来格式化文本信息
awk处理过程: 依次对每一行进行处理,然后输出
awk命令形式:
awk [-F|-f|-v] ‘BEGIN{} //{command1; command2} END{}’ file
[-F|-f|-v]大参数,-F指定分隔符,-f调用脚本,-v定义变量 var=val
- 各种语言比较
_wy_
编程语言
Java Ruby PHP 擅长领域
- oracle 中数据类型为clob的编辑
知了ing
oracle clob
public void updateKpiStatus(String kpiStatus,String taskId){
Connection dbc=null;
Statement stmt=null;
PreparedStatement ps=null;
try {
dbc = new DBConn().getNewConnection();
//stmt = db
- 分布式服务框架 Zookeeper -- 管理分布式环境中的数据
矮蛋蛋
zookeeper
原文地址: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opensource/os-cn-zookeeper/
安装和配置详解
本文介绍的 Zookeeper 是以 3.2.2 这个稳定版本为基础,最新的版本可以通过官网 http://hadoop.apache.org/zookeeper/来获取,Zookeeper 的安装非常简单,下面将从单机模式和集群模式两
- tomcat数据源
alafqq
tomcat
数据库
JNDI(Java Naming and Directory Interface,Java命名和目录接口)是一组在Java应用中访问命名和目录服务的API。
没有使用JNDI时我用要这样连接数据库:
03. Class.forName("com.mysql.jdbc.Driver");
04. conn
- 遍历的方法
百合不是茶
遍历
遍历
在java的泛
- linux查看硬件信息的命令
bijian1013
linux
linux查看硬件信息的命令
一.查看CPU:
cat /proc/cpuinfo
二.查看内存:
free
三.查看硬盘:
df
linux下查看硬件信息
1、lspci 列出所有PCI 设备;
lspci - list all PCI devices:列出机器中的PCI设备(声卡、显卡、Modem、网卡、USB、主板集成设备也能
- java常见的ClassNotFoundException
bijian1013
java
1.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org.apache.commons.logging.LogFactory 添加包common-logging.jar2.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javax.transaction.Synchronization
- 【Gson五】日期对象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bit1129
反序列化
对日期类型的数据进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时,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1. 序列化时,Date对象序列化的字符串日期格式如何
2. 反序列化时,把日期字符串序列化为Date对象,也需要考虑日期格式问题
3. Date A -> str -> Date B,A和B对象是否equals
默认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import com
- 【Spark八十六】Spark Streaming之DStream vs. InputDStream
bit1129
Stream
1. DStream的类说明文档:
/**
* A Discretized Stream (DStream), the basic abstraction in Spark Streaming, is a continuous
* sequence of RDDs (of the same type) representing a continuous st
- 通过nginx获取header信息
ronin47
nginx header
1. 提取整个的Cookies内容到一个变量,然后可以在需要时引用,比如记录到日志里面,
if ( $http_cookie ~* "(.*)$") {
set $all_cookie $1;
}
变量$all_cookie就获得了cookie的值,可以用于运算了
- java-65.输入数字n,按顺序输出从1最大的n位10进制数。比如输入3,则输出1、2、3一直到最大的3位数即999
bylijinnan
java
参考了网上的http://blog.csdn.net/peasking_dd/article/details/6342984
写了个java版的:
public class Print_1_To_NDigit {
/**
* Q65.输入数字n,按顺序输出从1最大的n位10进制数。比如输入3,则输出1、2、3一直到最大的3位数即999
* 1.使用字符串
- Netty源码学习-ReplayingDecoder
bylijinnan
javanetty
ReplayingDecoder是FrameDecoder的子类,不熟悉FrameDecoder的,可以先看看
http://bylijinnan.iteye.com/blog/1982618
API说,ReplayingDecoder简化了操作,比如:
FrameDecoder在decode时,需要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全:
public class IntegerH
- js特殊字符过滤
cngolon
js特殊字符js特殊字符过滤
1.js中用正则表达式 过滤特殊字符, 校验所有输入域是否含有特殊符号function stripscript(s) { var pattern = new RegExp("[`~!@#$^&*()=|{}':;',\\[\\].<>/?~!@#¥……&*()——|{}【】‘;:”“'。,、?]"
- hibernate使用sql查询
ctrain
Hibernate
import java.util.Iterator;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hibernate.Hibernate;
import org.hibernate.SQLQuery;
import org.hibernate.Session;
import org.hibernate.Transa
- linux shell脚本中切换用户执行命令方法
daizj
linuxshell命令切换用户
经常在写shell脚本时,会碰到要以另外一个用户来执行相关命令,其方法简单记下:
1、执行单个命令:su - user -c "command"
如:下面命令是以test用户在/data目录下创建test123目录
[root@slave19 /data]# su - test -c "mkdir /data/test123"
- 好的代码里只要一个 return 语句
dcj3sjt126com
return
别再这样写了:public boolean foo() { if (tru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Android动画效果学习
dcj3sjt126com
android
1、透明动画效果
方法一:代码实现
public View onCreateView(LayoutInflater inflater, ViewGroup container, 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View rootView = inflater.inflate(R.layout.fragment_main, container, fals
- linux复习笔记之bash shell (4)管道命令
eksliang
linux管道命令汇总linux管道命令linux常用管道命令
转载请出自出处:
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105461
bash命令执行的完毕以后,通常这个命令都会有返回结果,怎么对这个返回的结果做一些操作呢?那就得用管道命令‘|’。
上面那段话,简单说了下管道命令的作用,那什么事管道命令呢?
答:非常的经典的一句话,记住了,何为管
- Android系统中自定义按键的短按、双击、长按事件
gqdy365
android
在项目中碰到这样的问题:
由于系统中的按键在底层做了重新定义或者新增了按键,此时需要在APP层对按键事件(keyevent)做分解处理,模拟Android系统做法,把keyevent分解成:
1、单击事件:就是普通key的单击;
2、双击事件:500ms内同一按键单击两次;
3、长按事件:同一按键长按超过1000ms(系统中长按事件为500ms);
4、组合按键:两个以上按键同时按住;
- asp.net获取站点根目录下子目录的名称
hvt
.netC#asp.nethovertreeWeb Forms
使用Visual Studio建立一个.aspx文件(Web Forms),例如hovertree.aspx,在页面上加入一个ListBox代码如下:
<asp:ListBox runat="server" ID="lbKeleyiFolder" />
那么在页面上显示根目录子文件夹的代码如下:
string[] m_sub
- Eclipse程序员要掌握的常用快捷键
justjavac
javaeclipse快捷键ide
判断一个人的编程水平,就看他用键盘多,还是鼠标多。用键盘一是为了输入代码(当然了,也包括注释),再有就是熟练使用快捷键。 曾有人在豆瓣评
《卓有成效的程序员》:“人有多大懒,才有多大闲”。之前我整理了一个
程序员图书列表,目的也就是通过读书,让程序员变懒。 写道 程序员作为特殊的群体,有的人可以这么懒,懒到事情都交给机器去做,而有的人又可
- c++编程随记
lx.asymmetric
C++笔记
为了字体更好看,改变了格式……
&&运算符: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int a=-1,b=4,k;
k=(++a<0)&&!(b--
- linux标准IO缓冲机制研究
音频数据
linux
一、什么是缓存I/O(Buffered I/O)缓存I/O又被称作标准I/O,大多数文件系统默认I/O操作都是缓存I/O。在Linux的缓存I/O机制中,操作系统会将I/O的数据缓存在文件系统的页缓存(page cache)中,也就是说,数据会先被拷贝到操作系统内核的缓冲区中,然后才会从操作系统内核的缓冲区拷贝到应用程序的地址空间。1.缓存I/O有以下优点:A.缓存I/O使用了操作系统内核缓冲区,
- 随想 生活
暗黑小菠萝
生活
其实账户之前就申请了,但是决定要自己更新一些东西看也是最近。从毕业到现在已经一年了。没有进步是假的,但是有多大的进步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
毕业的时候班里12个女生,真正最后做到软件开发的只要两个包括我,PS:我不是说测试不好。当时因为考研完全放弃找工作,考研失败,我想这只是我的借口。那个时候才想到为什么大学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学习技术,增强自己的实战能力,以至于后来找工作比较费劲。我
- 我认为POJO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windshome
javaPOJO编程J2EE设计
这篇内容其实没有经过太多的深思熟虑,只是个人一时的感觉。从个人风格上来讲,我倾向简单质朴的设计开发理念;从方法论上,我更加倾向自顶向下的设计;从做事情的目标上来看,我追求质量优先,更愿意使用较为保守和稳妥的理念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