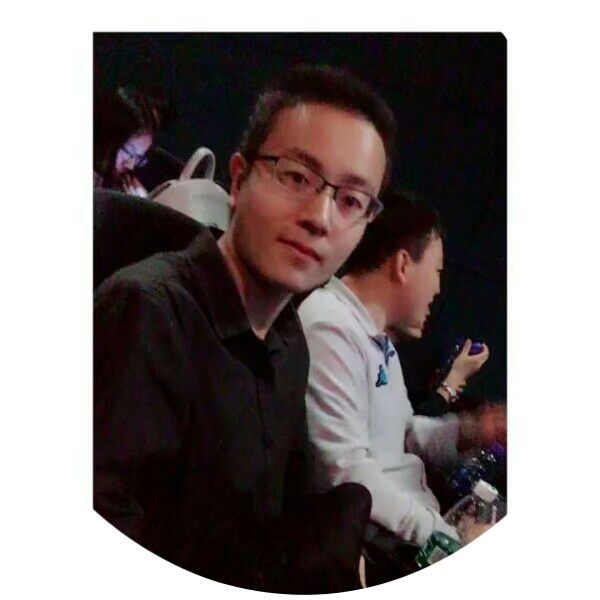我是疾病的试验田,她在田里肆意播种,不管所有的疮孔。屋漏偏逢连夜雨,跟沈静还在冷战,过山车就已经迫不及待带我冲向更深处的谷底。
脖子左侧的淋巴在谋划着一场大爆发,在一夜里发炎的脖子像是怀孕的肚子,哗啦啦地变大。小城医院的彩超把她跟甲状腺的关系撇清,遍布的红色淋巴让整个鉴定报告图显得格外刺眼,实际上它叫白细胞,噬咬病菌的家伙,当它过多时,自己就成了致命的病菌。
舍友说:“不会是淋巴癌吧?赶紧去大医院检查,我之前有个同学也是得了淋巴癌,最后动手术之后需要从喉咙开个口子才能吃东西,还是流食,喂进去一勺,还从口子里流出来半勺。”
他的“也”字让我莫名地不安,这种有强烈画面感的描述带来的是无尽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撕裂的疼痛也让一切感受在加剧。
小城的医院建议到设备更好的医院去进一步检查,妈赶紧从外地赶到我身边,带着我去了名医院寻找名设备和名医,她后来说在火车上眼泪就没停过,快到我身边了才把眼泪擦干净,这些眼泪要等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
如果名医院人不多那就对不起它的“名”,如果名医院重点医治的疾病不复杂也成就不了它的“名”,这就是“名”背后的东西—天没亮就开始排的长队、明明很痛苦却因为别人更痛苦所以只有几分钟匆忙的医患对话、患者病情在漫长等待中更严重而病人家属也被拖病的无奈······
到医院的那一天已经挂不上号,我和妈住了地下旅馆,遇到一个跟我同龄的女孩子,父母陪着,因为是老乡所以家长间就聊得多一些。那女孩儿患了乳腺癌,听到癌,我还是忍不住看了她一眼,高挑白皙清秀,当相貌甚好的人患上了癌症,我本该因为这种落差或者说是命运捉弄而感到惋惜,但我并没有,我没什么感受,疼痛面前坚强的人选择抗争,软弱的人选择麻木,一切情感的麻木。
第二天大家就散了,排队挂号,排队候医,排队取药,我想我的病还算不尴不尬—淋巴脓肿,名机器和名医的效率值得夸赞。
那个城市的那幢写着“医院”的大楼里,我靠着大厅的柱子,蹲坐,举目无亲,只有妈。头斜向左侧,只有压着鼓起的疱才能缓解一丁点疼,无论正着还是向右摆都会加剧撕裂感。我看着跑到取药队伍最前面的女人试图跟窗口前站着的估计也排了很久的人商量着什么,她很焦急,脸是红的,眼泪是透明的,膝盖是弯曲的,好像准备着最后不得已时的下跪乞怜。她为什么要这样可怜呢?为什么求别人呢?为什么甚至准备跪下来以省掉排队的时间呢?为什么呢?为什么?······
医院很冷,不是温度的冷,是从骨髓、神经散发出来的冷,冷让脖子的痛更加干涩,让心情枯萎。妈取完药回来,很焦急,脸是红的,眼泪是透明的,膝盖弯曲着扶起我,径直往车站走,走到发现刚好赶上最后一班客车的最后发车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吗?
“老孩儿,走,我们回家,这边医院没有多余的地方挂点滴,不过医生开了药,回家在附近的医疗点把这药注射进点滴里给你挂。”名医院没给我排队挂点滴的机会。
可惜,医院的药配上家乡的点滴并没有阻止病情的恶化,脖子越肿越大,撕裂的感觉也越来越重,疾病不需要休息,她会在你想睡觉的时候告诉你疼痛的真谛,失眠只是这真谛中微不足道的副产品。遇到这种情况,能大叫就大叫出来吧,不要像我一样蜷缩地咬着嘴唇,出血了也没有察觉。
二姐知道了情况,赶紧联系在县医院做医生的大学同学,托她找了老专家来腾出时间重点治疗我,从小医院到大医院再到小医院,我并不敢抱太大希望,因为后面的失望会让我绝望。倒是妈,溺水前抓着一根稻草就绝对会不顾一切地相信事情会有转机,我的双脚是被她的信念牵着走的。
老专家询问了我的情况,仔细研看我脖子上的肿块,浏览之前的就诊资料,尤其关注名机器拍出的图像,诊断结果跟名医一样—淋巴脓肿,当即决定第二天给我做手术。我当然求之不得,整天脖子看起来像长了个大瘤子一样,着实丑陋又难受。
“手术要尽快做,只要把里面的脓头给弄干净就好了,接着就是消炎和恢复,你们今天就住院吧。”老专家看起来平静而有把握,这让所有人在大战前都感到丝丝安慰。
“医生,我儿子问题不大吧?”妈还是直截了当地问出来了。
“病情目前来看问题不大,只不过孩子感到很疼,所以要尽快把手术做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
“好好好,我们马上住院,马上住院。医生,谢谢您,谢谢您,真的谢谢您,没有您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妈重复着感谢,然后跟二姐和二姐同学一起送老专家离开,据说老专家下午要赶去参加什么会。二姐和姐夫也在前面不断询问她那同学有关“淋巴脓肿”和手术的信息,我在后面安静地听着,想着,相比我这种在医学名单上不大不小的病,名医院有更危险复杂的病人要面对,直到我变成那个更危险复杂的病人,幸亏二姐托了关系。以前我看不起那些托关系走后门的人,现在自己成了既得利益者,这种面对伤痛甚至生死时公平与利益之间的心理矛盾此刻虽然掩埋起来,但它在一个敏感的人心里早晚要分裂斗争,最终达成平衡,也就是种更成熟的虚伪。无论人脉,权力,还是金钱,没有就批判、讨厌,有了就变了嘴脸,大概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当你没有你批判讽刺的东西(财富、人脉、权力···)时,话语中总免不了酸腐的味道。
马上办手续住院,搬进病房。县医院还是在老专家的光环之后展示出了它的拮据,加上卫生间才二十多平方的病房里有三个床位,左腿静脉曲张的阿姨,阑尾炎的姑娘,还有歪脖子的我。湿热的空气,不能用的空调,不多的空旷上站着多多的家属。没关系,这些我都不在乎,我面对的根本不是眼前环境的窘迫,视网膜上的成像带不来什么大脑皮层的感受,只有,只有日渐炽热的淋巴细胞盘踞了我的脖子。
临近床位的姑娘无法躲避地看了我几眼,毕竟房间就那么大,床位就那么近。她还没做手术,这是她做手术之后我才回想起来的。我盖着被子,向左侧躺,闭着眼睛,故意看不见所有人,也假装所有人都看不见我。
等到傍晚人们离开,陪床的亲人也去买饭,病房里的安静又让人觉察到喧闹之外的另一种不适。巧的是,病床上疼痛的人似乎都不喜欢手机、书什么的。
“你得了什么病呀?”姑娘似乎不想保持尴尬的寂静,先问起我这个同龄人。
“淋巴脓肿。”我费力转向右侧,脸依然是疼痛的冷漠,不是不想礼貌地笑,只是笑会牵扯到脖子左侧的肌肉让疼痛加剧,于是连回答也尽量简短。
“我是阑尾炎,明天割阑尾。”
“我也是明天手术。”
“你叫什么呀?”
“骆血。”
“我叫嫣文,姹紫嫣红的嫣,文章的文。”她似乎意识到我说话时脸有些抽搐,眼睛也是半睁着,所以就没有接着说下去,只是保持着向左侧躺的姿势,在我闭上眼睛之前她的眼睛还是睁开的。
夜晚,每张病床上都挤着两个人,我和我妈,嫣文和她妈,阿姨和丈夫,反正没人好意思在病房剩下的狭小空间上放置自己的陪床椅。我的嘴唇在不自觉的发抖,耳朵里出现淋巴细胞滋滋生长的声音,白细胞猛烈地发动着战争,我看不见,只能在幻觉中听见。疼痛到了一定的极限值,就能睡着了,不对,就能晕过去了。
第二天的手术终于到了,害怕是必然的,会不会更痛?会不会出意外?会不会死在手术台?会不会······反正都已经进了手术室躺在手术台,是死是活谁知道呢?只是看着简陋的皮垫手术台,没有电视上的那些高端设备,心里更加紧张,况且我左手还打着点滴,万一我等一下怕疼一用力把针头弄断怎么办?想着想着,麻醉师已经给我打了局部麻醉,作用很快,脖子那一块的痛觉神经很快被麻痹了。听到手术刀、镊子和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手术器具互相碰撞的声音,紧张更是迅速蔓延整个大脑。直到刀子划开皮肤的那一刻,紧张反而减弱了,我听见有液体落进容器的声音,不敢看也不能看,只能想象出那应该是一堆泛着丝丝血红色、白色和棕黄色的脓液,金属器具继续将里面残留的给刮干净,类似于锅铲铲干净粘在锅底的粥,镊子夹着棉球顶在脓肿位置的深处,犀利而又温和地把喉咙中的气道压得狭窄,呼吸变得困难,我屏住大部分呼吸,默念“轻呼···轻吸···轻呼···轻吸···”,僵直着脖子,不敢喊叫,不敢动弹,只是用右手死死地握紧单薄的皮垫床沿,害怕自己的一点点动作会影响医生的精细操作,甚至害怕自己一动那镊子就会刺穿脖子的肌肉进入气管,光是想想就觉得惊悚。直到不知几分钟后镊子离开,棉球在脖子里吮吸无法用金属器具硬刮的脓液,我的右手才松弛下来。医生给伤口抹了抹消毒的药水,贴上纱布什么的,然后告诉我手术结束了。我满脸是汗,全身都汗湿了,唯独脖子和左手手背没有汗的痕迹。整个手术其实没有多长时间,只是身在其中感觉一切如此缓慢,缓慢地如同时间静止。
“手术进行地不错,还得住院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后期消炎情况。”老专家平静地对我妈讲。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您辛苦了,辛苦了。”妈边扶着我边感谢着眼前的恩人边推着挂点滴袋的架子。
“孩子在手术中很坚强,虽然打麻醉了,但是手术过程中为了把脓液处理干净,镊子对喉咙还是会有一些较强的压迫,那段时间呼吸会比较困难,孩子都忍住了,没叫没动也没哭嘛。”
“对,我家小孩儿很坚强。”妈附和着医生的鼓励,挤出疲惫中的一点笑。
我整个人在冷汗中站着,虚脱,满脸苍白,什么话都不想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十多天的颠簸造就了筋骨毕现,减肥就是这么容易,只是生病之前我也不胖。
走回病房,躺在床上,睁开眼睛的力气都不想用,蜷缩着听医生的术后指导,点头“嗯”地回复需要回答的问题。
等我再次醒来就已经下午,向右侧看发现嫣文不在,我知道她去“割肉”了。妈发现我醒了,赶紧喂我吃了些东西,把午饭补回来,身体很争气,胃口似乎也好了一些。我开始感受起自己脖子左侧手术的地方,有纱布绷带覆盖,所以我只能想象:纱布浸满红色和棕白色,一层松弛皱皱的浅褐色皮肤覆盖在脓肿处,里面还有无法除净的掺杂血色的棕白色脓液。大脑中有如此刺激的画面感,我仍然若无其事地吃下所有让我有胃口的食物,没感到任何的恶心。
吃完不久,病房门口就出现一群人急匆匆地推着滑轮床小跑向嫣文的床边,伴随着有医生喊:“所有男士先出去一会儿,所有男士先出去一会儿。”我很识趣地起床慢步离开了,一个人站在外面听到里面说什么给病人插导尿管,这让我形成一种“割阑尾也很痛苦”的印象。等被允许进去,看到她闭着眼睛,无声的眼泪从两侧滑下形成痕迹的样子,印象更加深刻。无论如何,住医院不会是什么舒服的事情。手术后,最好一切安静,什么都不想做,不想说话,不想睁眼,不想动弹,她和我一样。等到麻药退去,这些感觉又都重复了一遍,唯独增添了尖锐的刺痛。
难受消逝需要一觉,一夜过后昨天就消失了。只有我的淋巴细胞不甘心,一夜没睡重新繁衍出一个小脓疱,医生过来询问了两句就说脓头没有除干净,还得马上做一次小手术。因为被医生重点关注,所以医院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高效,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就再一次上了手术台,这一次除了疱比上次小一些,其余的情境基本跟上次一样,我的忐忑不安还没有充分蔓延手术就已经结束了。
我自己推着架子就走回了病房,一脸镇定,不是真的镇定,只是不习惯把慌张表现出来,尤其还要表现给其他人看。
“还得继续住院观察几天消炎的效果,不过不用担心,病会好起来的。”医生安慰着我和妈。
“嗯嗯嗯。”我并不确定地回复着,谁知道一觉醒来会不会又来一个脓疱呢?
妈也明显改变昨天的欣喜情绪,愁眉苦脸起来,不过还是不失礼貌地表达了对医生的感谢:“真的麻烦您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等医生离开,父母们开始在床尾的凳子上唠起嗑来。嫣文拿出口香糖嚼了起来,虽然医生说她可以试着走一走,但她仍然不太敢移动肚子,怕影响了缝合的伤口造成疼痛,所以就没法刷牙什么的。
“吃吗?”她倒出两粒递给我。
“不吃,谢啦。”同屋了几天,这个时候我才仔细地看看她,及肩的头发,没有任何化学合成品遮盖的圆润脸,干净朴素,灵动柔弱。这样的情境蛮触动我,我们看着彼此,她的眼睛里有我,我的眼睛里有她,都脆弱朦胧地看着,没有多余的能量支持自己想些什么,只是看着,仅仅是看着。没有羞赧,没有红晕,没有尴尬,都不想挪开视线,或许是没有力气,或许是懒,或许是觉得对方的脸值得浪费大把的时间好好看看。
“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吧。”嫣文边轻轻说边拿起枕边的手机准备保存。
面对不过分的主动,我向来不太会拒绝。
双方都留了号码。这种机缘以后会联系也很正常,不管以后是成为共有一段回忆的朋友,还是交际甚少散落天涯的过客,很多关系都是在微妙的可能性下萌芽并且发展,如果不留联系方式,那才扼杀了所有的可能性,未知也会因此而无聊透顶。
到了家长们都结伴出去买午饭的时候,病房就只剩下她和我,左腿静脉曲张的阿姨已经离开医院回家养病了。
“我想出去散散步,能扶一下我吗?”嫣文的语气虚弱中带着淡淡的期望。
我没有回答,直接下床走到她的床边把她扶起穿鞋,宽松的条纹衣没掩盖住她整体的丰腴,这其实让我觉得温和亲近,舒适的感受可能与她身材跟我妈很像有关。
我左手搀着她一步一步缓缓地走,她左手推着架子,我们在廊厅里的步伐像年迈的夫妻依偎而行。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气氛也不会因为安静而尴尬,没有话题就不说呗,没有多余的力气就不想多余的事情。
我们走到尽头的窗户边,一起看着窗外,风吹起她的头发,我沿着风的方向看着她,有一种自然的散乱的美感。她能感觉到我的目光,不过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姿势,没有转过来四目相对,这对彼此来说都恰得其分,我欣赏着她,她欣赏着我欣赏她的模糊景象,这份建立在同一病房上的同龄友谊或者情感连接足够让我们拥有短暂的默契。
两天后,嫣文就要回家休养了,她跟我告别,语气表情中并没有透露出明显的不舍,也或许我没有捕捉到。我的病情那几天稳定了很多,做完相关术后检查,医生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后,我也出院回家了。
当我回到家中安静下来,回想起自己一个人蹲坐在医院大厅柱子旁的情境,冰冷依旧穿过时间刺进骨髓里,我真切地觉得自己很可能会死,低沉的思绪盘踞着整个灵魂,不过痛苦时没法思考,只有在摆脱疼痛后的短暂冷静中,理性才会凝练经历与感受,才会升华和铭刻记忆。意识到生的脆弱,躯体的脆弱,信念的脆弱,我突然觉得要趁机写遗书,谁知道这次见面会不会后会无期?谁知道这次拥抱会不会是临终遗言?谁知道这些文字会不会是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连接?虽然我还年轻,虽然我暂时从病魔手中逃出,但还是觉得无常,世事无常,我亦无常,所以还是写一写吧,即使是当做对自己岁月的总结也好。奇怪的很,遗书写起来异常顺畅,像是准备好了一样。
附录:
《致活着的人》
不知道,这封信被看到时我是怎么离开的,最好不是DIY。如果是DIY,家人尤其是爸妈会哭得很恐怖吧。本来想劝你们不要哭,我知道没用,不在乎了,反正我看不到了,我害怕看到你们哭的场景,不想看你们哭,但是尽情哭吧,哭吧······把悲伤发泄出来,把愤怒发泄出来,把所有情绪都发泄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活得充实,可能我知道,只是我不愿意承认。有关生命意义的思考让我头晕目眩,是的,我在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上彷徨了,我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而且现实让我不断加深没有意义的印象,现在它成为真理指导我的毁灭。
我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在意的人和事,可是敲下这些字的时候,发现还是有留恋。
爸,妈,其实我从小到大都对你们有怨气,我知道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抚养我成人很辛苦,也知道父爱母爱很伟大,但我就总是忘不掉你们从小到大在家经常吵架甚至动手的情境,那种旷日持久不仅忘不掉,而且让我一直隐隐排斥着自己天性中对你们的爱。我不婚的念头就是这样扎根的,而且就算结婚,我也不想要孩子,所以干脆还是不婚,这样更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说这些不是想让你们愧疚,你们没错,你们没错,你们没错,我知道生活不易,争吵难免,只怪我太敏感抑郁质了,生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们,离开后让你们知道也许大家都能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争吵。其实一直以来我都问自己是不是爱你们,我有过迟疑的,尤其在学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治疗的流程中包括回溯童年经历)以后。后来我发现,之所以自己有迟疑,是因为“爱”这个字本身过于模糊,过度概括,根本表达不了在我看来复杂、持久的情感。但在表达情感上,我们都习惯于用行动,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表达这份情感,知道的是这份情感一定是积极的、让我开心的、让我留恋的。
爸,妈,一定要相信离开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知道这样很自私,但无论生活本真的面目,还是疾病,虚无,懦弱···都让我觉得生不如死。我早就没法为别人而活了,即使是为了你们也做不到。妈,你说,我是你和爸婚姻维系到现在唯一的原因。大家都说劝和不劝离,我不想劝和,也不想劝离,只想说,有离的自由,也有继续的自由,这自由不在于别人怎么想,而在于你们自己对于这段婚姻的真正想法。分开,还是继续,都这么些年了,相信不会一时冲动做出决定。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支持你。
三姐,从小我跟你打打闹闹最多,相处的时间也最多,感情可能也最深。最近老是不断地想起家中盖新房、哥哥准备结婚那年,我每周五放学后跑到你班级门口,你用重点班的生活费补助来补充我的生活费。还有五年级时因为早自习提前下,我去你教室窗口取瓷缸给你买早餐。很怀念,很感激的。
大姐,二姐,妈总问我更爱三个姐中的哪个姐,我总说都爱,这不是应付的措辞,而是思考很久的答案。爱的原因不同,但量都是一样大大的。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对我很好很好很好,在我受欺负的时候会帮我,在我退缩的时候会推我,在我缺什么的时候会不遗余力地给我。写到这,眼泪让我的情绪接近崩溃,我想,我还是要写下去,很多事情如果不写,就是会消失,就是会忘记。
哥,我知道你对我也很好,爸妈和你之间有一层我说不清看不懂的隔膜,复杂的家庭构成让很多问题变得不可解,不可解也不必解,隔膜别变厚了就好。
小孩儿们,你们的老爹(小叔)、老舅可能没法再看你们了,我喜欢你们,很喜欢你们,特别喜欢你们。
沈静、K、嫣文······勿念。
我的电脑开机密码室友知道,其他密码三姐能猜得出来,她一直都猜得出来。
我有一个遗憾,也是我的心愿,我希望会哭的人不要哭太久,不要太悲伤,无论谁走了,生活都要继续,包袱不要太重,不要对一个人感情深到没他/她活不下去,这样生活会太累。
也许我只是到另一个世界呢,虽然不能证明另一个世界存在,但也没人能证明另一个世界不存在呀。
再见······
假设自己即将告别人世,写着写着发现生活并非一潭死水毫无生机,仿佛还有很多可以弥补的遗憾,自己还是有很多在意的人、事,活着的意义还是没被全部扼杀,心情通透舒畅很多。这种方式有点像写讣告,在自己的坟墓前念给自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