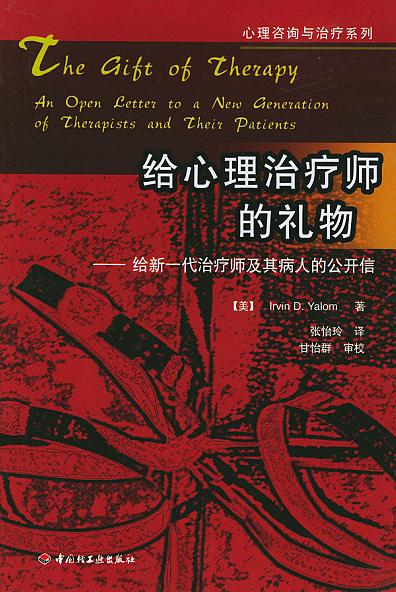·第二章 避免直接下诊断
今天的心理治疗学生面对的是对诊断的过度强调。医疗保健系统的管理者要求治疗师迅速地给出诊断,然后进行一个与诊断匹配的短程焦点治疗。这听起来不错,符合逻辑而且有效率。但是和现实实在是没什么关系,这不过是实现科学准确性的一种虚幻的努力,既不现实也不受欢迎。
虽然在有生理因素在内的严重情况(例如,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情感障碍、颞叶癫痫、药物毒性、因为毒性物质或变性因素或者传染性物质引发的躯体或者脑部疾患)下,诊断毫无疑问对治疗上的考虑起关键作用,但是,在日常的心理治疗中,面对困扰较为轻微的病人来说,诊断经常会起反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治疗是一个渐进的深入展开的过程,治疗师应当尽量全面深入地了解病人。诊断会限制治疗师的视角,而且会影响治疗师把病人当作人来建立关系的能力。一旦作出某种诊断,我们倾向于选择性地忽略病人不符合诊断的方面,相应地过度注意那些可能会证实我们最初诊断的特征。而且,诊断可以作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过程。治疗师把病人看作“边缘型”或者是“歇斯底里型”,并与他(或她)建立关系,可能会促进和推动病人表现出这些相应特质。实际上,对于因为医生的治疗而影响临床表征形成的这个问题已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得到重视,包括现在对多重人格障碍的争论以及压抑早期性虐待经历的相关记忆的问题。同时,也要记住,DSM人格障碍的类目诊断信度是很低的。
而且治疗师还没有注意到在第一次面谈后作出DSM—Ⅳ的诊断比经过多次面谈对病人有了更多了解之后要容易得多。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奇怪的科学吗?我的一个同事对他的精神科实习生问的一个问题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你在接受治疗或者你考虑接受治疗,你觉得你的治疗师能够用哪一种DSM—Ⅳ的诊断来充分形容一个像你这样复杂的人,”
在心理治疗领域,我们需要很好的客观性,但是不需要过多。如果我们把DSM诊断系统看得过重,我们必然会损害到人性,损害到治疗本身的自发性、创造性和不确定性。请记住那些参与制定已被推翻的诊断体系的临床心理学家和现在DSM委员会成员一样有能力、骄傲和自信。
第三章作为旅途伙伴的治疗师的病人
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描写了一个乡村牧师在听过几十年人们的忏悔之后总结了他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的人类天性——“首先,人们要比想像中更不开心;其次,没有一个完全成长的人”。每个人,既包括治疗师也包括病人,都注定要体验生命的美好,也要体验其不可避免的暗黑之处:幻灭、衰老、疾病、孤独、丧失、无意义、痛苦的选择和死亡。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这一点的描述最为彻底和阴暗:
在青年早期,当我们沉思着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活,我们就像戏院的孩子等着帷幕拉起,坐在那里兴高采烈,急切地等待着戏剧的开始。幸而我们不知道真的将要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能够预知,那么某种程度上孩子就像是被诅咒的囚犯,被判告给生命,而不是死亡,而且对于这个判告的意义毫无意识。
还有:
我们就像田地里的羔羊,在屠夫的眼皮底下玩耍。屠夫选了一只又一只作为他的牺牲者。在我们的好日子里我们根本就无法意识到命运可能为我们储藏的不幸——疾病、穷困、损毁、失去远见或者理性。
虽然叔本华的观点因为他的个人不幸而被渲染得格外阴暗,但是我们很难否认每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体生命所内蕴的绝望。我的妻子和我有些时候会自我娱乐,想像一组具有相似特征的人在—起开晚宴,例如一群垄断者、或者极端的自恋者、或者我们认识的被动——攻击性的人,或者相反,邀请一群我们遇到过的真正快乐的人参加“快乐”晚宴。虽然对于其他的小组,我们能毫无困难地找到一组我们认识的具有某种怪异特征的人坐满晚宴桌子,但是对于快乐的人,我们从未能想到一满桌人。每一次我们发现了几个性格上乐观快乐的人,然后把他或她放在候选人名单上,继续搜寻的结果总发现某一个快乐的客人最终会受到某种生活困境的打击,通常是严重的疾病或者是孩子和配偶的罹病。
这个悲剧性的但又是现实的对待生命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到我这里来寻求帮助的病人。虽然有很多词汇用来描述治疗关系(病人/治疗师,来访者/咨询师,被分析者/分析者、病人/促进者,以及最后也是最让人厌恶的——使用者/提供者),这些词中却没有一个准确地表达了我对治疗关系的认识。我倾向于把病人和我自己看成“旅途的伙伴”,这个词消除了“你们”(被痛苦折磨的人)和“我们”(治疗师)之间的区分。在我的培训中,我经常会听到所谓完全被分析了的治疗师这种说法,但是当我在生命之路上前行,与许多我的治疗师同事建立起亲密的关系,遇到领域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曾经被邀请为我的前治疗师和老师提供帮助,而且我自己成为了老师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这个说法的神秘本质。没有任何一个治疗师,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不被存在的内含悲剧影响。
我最喜欢的治疗小说是黑塞的《卢迪老师》(Magister Ludi),里面有两位生活在圣经时代的著名医治者约塞夫(Joseph)和戴恩(Dion)。虽然他们两人的工作都十分有效,但是两个人工作的方法却大有不同。年轻的医治者约塞夫通过宁静的、受神感召的倾听治疗。朝圣者们信任约塞夫。痛苦和焦虑在倾入他的耳内之后就像水消失在沙漠中一样,悔过者在离开的时候觉得倾空了、平静了。另一方面,年长的医治者戴恩积极地面对那些来寻求帮助的人。他感觉到他们没有被忏悔的罪恶。他是一个伟大的法官、惩戒者、斥责者和矫正者。他通过积极的干预进行帮助。他把悔过者像儿童一样对待,提供建议,分配苦行进行惩罚,要求去朝圣,或者要求敌人彼此和解。
这两位医治者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作为竞争者工作了许多年,直到约塞夫的心灵开始烦恼,坠入了黑暗的绝望,经常为自杀的念头困扰。他用自己的治疗方法不能治愈自己,于是他出发去南方找戴恩寻求帮助。
在朝圣的路上,一天晚上约塞夫走到一个绿洲休息,在那儿他和一个年老的旅行者进行了交谈。当约塞夫描述了他此行的目的之后,年长的旅行者自荐作为他的向导帮助他寻找戴恩。之后,在他们长长的旅途中,年长的旅行者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约塞夫,他就是戴恩,约塞夫寻找的人。
戴恩毫不犹豫地邀请年轻的、陷入绝望的竞争者到他家去。在那里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了许多年。戴恩开始请约塞夫作一个仆佣,之后让他做学生,最后两人成为同事。多年以后,戴恩病得很重,就要死去了,他把年轻的同事叫到床前聆听忏悔。他谈到了约塞夫早先经历的可怕的心灵疾病以及他寻找年长的戴恩寻求帮助的旅程。他谈到当约塞夫发现他的旅伴和向导竟然就是戴恩时,约塞夫是如何感到这件事就像一个奇迹。
现在他就要死了,到了说出关于这个奇迹的事实的时候了。戴恩承认在那个时候与约塞夫的相遇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奇迹,因为他当时也陷入绝望之中。他也感到空虚和心灵死亡,同样他无法帮助自己,于是动身去寻求帮助。在绿洲相遇的那一晚他正在寻找叫做约塞夫的伟大医治者的路上。
----------------------------------------------------
黑塞的故事总是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感动我。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深刻揭示了给予和接受帮助、诚实和欺骗、医治者和病人的意义。两个人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获得帮助。年轻的医治者通过被培养、照顾、教授、辅导和教养获得帮助。而年长的医治者通过从追随者那里获得的子女似的爱、尊重和安慰获得帮助。
但是现在回顾这个故事,我怀疑是否这两位受伤的医治者本能够更多地帮助彼此。也许他们错过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更加真诚的、更有力量的变化。也许真正的治疗在濒死的病床上才出现,当他们彼此袒露他们都是旅客、都只是人的时候才出现。20年的保守秘密虽然有所帮助,但是可能阻碍了更深层次帮助的出现。如果戴恩濒死时的表白发生在20年前,如果医治者和追寻者一起共同面对并没有答案的问题,会发生些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和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相呼应,里尔克建议说:“耐心对待所有尚未解决的事情,努力去爱问题本身。”我要加上另一句:“也要努力去爱提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