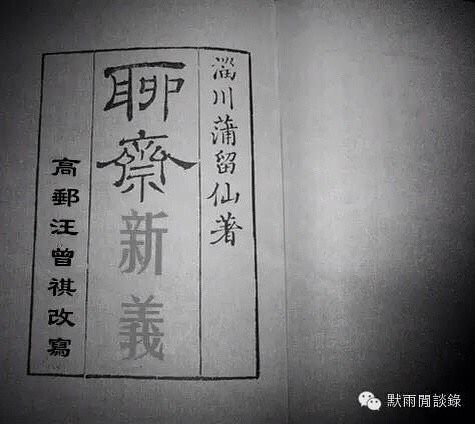- 情绪觉察日记第37天
露露_e800
今天是家庭关系规划师的第二阶最后一天,慧萍老师帮我做了个案,帮我处理了埋在心底好多年的一份恐惧,并给了我深深的力量!这几天出来学习,爸妈过来婆家帮我带小孩,妈妈出于爱帮我收拾东西,并跟我先生和婆婆产生矛盾,妈妈觉得他们没有照顾好我…。今晚回家见到妈妈,我很欣赏她并赞扬她,妈妈说今晚要跟我睡我说好,当我们俩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握着妈妈的手对她说:妈妈这几天辛苦你了,你看你多利害把我们的家收拾得
- 芦花鞋一四
许叶晗
又是在一个寒冷的夏日里,青铜和葵花决定今天一起去卖芦花鞋,奶奶亲手给他们做了一碗热乎乎的粥对他们说:“就靠你们两挣生活费了这碗粥赶紧趁热喝了吧!”于是青铜和葵花喝完了奶奶给她们做的粥,就准备去镇上卖卢花鞋,这回青铜和葵花穿着新的芦花鞋来到了镇上。青铜这回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卖,用手势表达对葵花说:“这回有好多人在抢我们生意呢!我们必须得吆喝起来。”葵花点了点头。可是谁知他们也大声的叫,卖芦花喽!卖芦花
- 关于沟通这件事,项目经理不需要每次都面对面进行
流程大师兄
很多项目经理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项目中由于事情太多,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召开会议,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有效地管理项目中的利益相关者?当然,不建议电子邮件也不需要开会的话,建议可以采取下面几种方式来形成有效的沟通,这几种方式可以帮助你努力的通过各种办法来保持和各方面的联系。项目经理首先要问自己几个问题,项目中哪些利益相关者是必须要进行沟通的?可以列出项目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清单,同时也整理出项目中哪些
-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间关系与区别
ℒℴѵℯ心·动ꦿ໊ོ꫞
人工智能学习深度学习python
一、机器学习概述定义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ML)是一种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利用统计学和计算算法来训练模型,使计算机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并自动进行预测或决策。机器学习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样本,识别其中的模式和规律,从而对新的数据进行判断。其核心在于通过训练过程,让模型不断优化和提升其预测准确性。主要类型1.监督学习(SupervisedLearning)监督学习是指在训练数据集中包含输入
- android系统selinux中添加新属性property
辉色投像
1.定位/android/system/sepolicy/private/property_contexts声明属性开头:persist.charge声明属性类型:u:object_r:system_prop:s0图12.定位到android/system/sepolicy/public/domain.te删除neverallow{domain-init}default_prop:property
- 【iOS】MVC设计模式
Magnetic_h
iosmvc设计模式objective-c学习ui
MVC前言如何设计一个程序的结构,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叫做"架构模式"(architecturalpattern),属于编程的方法论。MVC模式就是架构模式的一种。它是Apple官方推荐的App开发架构,也是一般开发者最先遇到、最经典的架构。MVC各层controller层Controller/ViewController/VC(控制器)负责协调Model和View,处理大部分逻辑它将数据从Mod
- 一百九十四章. 自相矛盾
巨木擎天
唉!就这么一夜,林子感觉就像过了很多天似的,先是回了阳间家里,遇到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儿。特别是小伙伴们,第二次与自己见面时,僵硬的表情和恐怖的气氛,让自己如坐针毡,打从心眼里难受!还有东子,他现在还好吗?有没有被人欺负?护城河里的小鱼小虾们,还都在吗?水不会真的干枯了吧?那对相亲相爱漂亮的太平鸟儿,还好吧!春天了,到了做窝、下蛋、喂养小鸟宝宝的时候了,希望它们都能够平安啊!虽然没有看见家人,也
- UI学习——cell的复用和自定义cell
Magnetic_h
ui学习
目录cell的复用手动(非注册)自动(注册)自定义cellcell的复用在iOS开发中,单元格复用是一种提高表格(UITableView)和集合视图(UICollectionView)滚动性能的技术。当一个UITableViewCell或UICollectionViewCell首次需要显示时,如果没有可复用的单元格,则视图会创建一个新的单元格。一旦这个单元格滚动出屏幕,它就不会被销毁。相反,它被添
- element实现动态路由+面包屑
软件技术NINI
vue案例vue.js前端
el-breadcrumb是ElementUI组件库中的一个面包屑导航组件,它用于显示当前页面的路径,帮助用户快速理解和导航到应用的各个部分。在Vue.js项目中,如果你已经安装了ElementUI,就可以很方便地使用el-breadcrumb组件。以下是一个基本的使用示例:安装ElementUI(如果你还没有安装的话):你可以通过npm或yarn来安装ElementUI。bash复制代码npmi
- 地推话术,如何应对地推过程中家长的拒绝
校师学
相信校长们在做地推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市场专员反馈家长不接单,咨询师反馈难以邀约这些家长上门,校区地推疲软,招生难。为什么?仅从地推层面分析,一方面因为家长受到的信息轰炸越来越多,对信息越来越“免疫”;而另一方面地推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营销话术没有提高,无法应对家长的拒绝,对有意向的家长也不知如何跟进,眼睁睁看着家长走远;对于家长的疑问,更不知道如何有技巧地回答,机会白白流失。由于回答没技巧和专业
- 谢谢你们,爱你们!
鹿游儿
昨天家人去泡温泉,二个孩子也带着去,出发前一晚,匆匆下班,赶回家和孩子一起收拾。饭后,我拿出笔和本子(上次去澳门时做手帐的本子)写下了1\2\3\4\5\6\7\8\9,让后让小壹去思考,带什么出发去旅游呢?她在对应的数字旁边画上了,泳衣、泳圈、肖恩、内衣内裤、tapuy、拖鞋……画完后,就让她自己对着这个本子,将要带的,一一带上,没想到这次带的书还是这本《便便工厂》(晚上姑婆发照片过来,妹妹累得
- C语言如何定义宏函数?
小九格物
c语言
在C语言中,宏函数是通过预处理器定义的,它在编译之前替换代码中的宏调用。宏函数可以模拟函数的行为,但它们不是真正的函数,因为它们在编译时不会进行类型检查,也不会分配存储空间。宏函数的定义通常使用#define指令,后面跟着宏的名称和参数列表,以及宏展开后的代码。宏函数的定义方式:1.基本宏函数:这是最简单的宏函数形式,它直接定义一个表达式。#defineSQUARE(x)((x)*(x))2.带参
- 微服务下功能权限与数据权限的设计与实现
nbsaas-boot
微服务java架构
在微服务架构下,系统的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控制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和微服务数量的增加,如何保证不同用户和服务之间的访问权限准确、细粒度地控制,成为设计安全策略的关键。本文将讨论如何在微服务体系中设计和实现功能权限与数据权限控制。1.功能权限与数据权限的定义功能权限:指用户或系统角色对特定功能的访问权限。通常是某个用户角色能否执行某个操作,比如查看订单、创建订单、修改用户资料等。数据权限:
- 理解Gunicorn:Python WSGI服务器的基石
范范0825
ipythonlinux运维
理解Gunicorn:PythonWSGI服务器的基石介绍Gunicorn,全称GreenUnicorn,是一个为PythonWSGI(WebServerGatewayInterface)应用设计的高效、轻量级HTTP服务器。作为PythonWeb应用部署的常用工具,Gunicorn以其高性能和易用性著称。本文将介绍Gunicorn的基本概念、安装和配置,帮助初学者快速上手。1.什么是Gunico
- 2021年12月19日,春蕾教育集团团建活动感受——黄晓丹
黄错错加油
感受:1.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游戏环节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得到了锻炼,也增长了不少知识。2.游戏过程中,我们贡献的是个人力量,展现的是团队的力量。它磨合的往往不止是工作的熟悉,更是观念上契合度的贴近。3.这和工作是一样的道理。在各自的岗位上,每个人摆正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才能,并团结一致劲往一处使,才能实现最大的成功。新知:1.团队精神需要不断地创新。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人们
- Cell Insight | 单细胞测序技术又一新发现,可用于HIV-1和Mtb共感染个体诊断
尐尐呅
结核病是艾滋病合并其他疾病中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结核病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Mtb)感染引起,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由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type1,HIV-1)感染引起。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张国良团队携手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吴靓团队,共同研究得出单细胞测序
- c++ 的iostream 和 c++的stdio的区别和联系
黄卷青灯77
c++算法开发语言iostreamstdio
在C++中,iostream和C语言的stdio.h都是用于处理输入输出的库,但它们在设计、用法和功能上有许多不同。以下是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区别1.编程风格iostream(C++风格):C++标准库中的输入输出流类库,支持面向对象的输入输出操作。典型用法是cin(输入)和cout(输出),使用>操作符来处理数据。更加类型安全,支持用户自定义类型的输入输出。#includeintmain(){in
- 《投行人生》读书笔记
小蘑菇的树洞
《投行人生》----作者詹姆斯-A-朗德摩根斯坦利副主席40年的职业洞见-很短小精悍的篇幅,比较适合初入职场的新人。第一部分成功的职业生涯需要规划1.情商归为适应能力分享与协作同理心适应能力,更多的是自我意识,你有能力识别自己的情并分辨这些情绪如何影响你的思想和行为。2.对于初入职场的人的建议,细节,截止日期和数据很重要截止日期,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请老板为你所有的任务进行优先级排序。和老板喝咖啡的好
- Linux下QT开发的动态库界面弹出操作(SDL2)
13jjyao
QT类qt开发语言sdl2linux
需求:操作系统为linux,开发框架为qt,做成需带界面的qt动态库,调用方为java等非qt程序难点:调用方为java等非qt程序,也就是说调用方肯定不带QApplication::exec(),缺少了这个,QTimer等事件和QT创建的窗口将不能弹出(包括opencv也是不能弹出);这与qt调用本身qt库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思路:1.调用方缺QApplication::exec(),那么我们在接口
- 绘本讲师训练营【24期】8/21阅读原创《独生小孩》
1784e22615e0
24016-孟娟《独生小孩》图片发自App今天我想分享一个蛮特别的绘本,讲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是属于这个群体,80后的独生小孩。这是一本中国绘本,作者郭婧,也是一个80厚。全书一百多页,均为铅笔绘制,虽然为黑白色调,但并不显得沉闷。全书没有文字,犹如“默片”,但并不影响读者对该作品的理解,反而显得神秘,梦幻,給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作者在前蝴蝶页这样写到:“我更希望父母和孩子一起分享这本书,使他
- 店群合一模式下的社区团购新发展——结合链动 2+1 模式、AI 智能名片与 S2B2C 商城小程序源码
说私域
人工智能小程序
摘要:本文探讨了店群合一的社区团购平台在当今商业环境中的重要性和优势。通过分析店群合一模式如何将互联网社群与线下终端紧密结合,阐述了链动2+1模式、AI智能名片和S2B2C商城小程序源码在这一模式中的应用价值。这些创新元素的结合为社区团购带来了新的机遇,提升了用户信任感、拓展了营销渠道,并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完美融合。一、引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区团购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在满足消费者日常需
- 我校举行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暨名师专业工作室工作交流活动
李蕾1229
为促进我校教师专业发展,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带头作用,11月6日下午,我校举行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暨名师专业工作室工作交流活动。图片发自App会议由教师发展处李蕾主任主持,首先,由范校长宣读新老教师结对名单及双方承担职责。随后,两位新调入教师陈玉萍、莫正杰分别和他们的师傅鲍元美、刘召彬老师签订了师徒结对协议书。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师徒拥抱、握手。有了师傅就有了目标有了方向,相信两位新教师在师
- 消息中间件有哪些常见类型
xmh-sxh-1314
java
消息中间件根据其设计理念和用途,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常见类型:点对点消息队列(Point-to-PointMessagingQueues):在这种模型中,消息被发送到特定的队列中,消费者从队列中取出并处理消息。队列中的消息只能被一个消费者消费,消费后即被删除。常见的实现包括IBM的MQSeries、RabbitMQ的部分使用场景等。适用于任务分发、负载均衡等场景。发布/订阅消息模型(Pub/Sub
- ArcGIS栅格计算器常见公式(赋值、0和空值的转换、补充栅格空值)
研学随笔
arcgis经验分享
我们在使用ArcGIS时通常经常用到栅格计算器,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我日常中经常用到的几个公式,供大家参考学习。将特定值(-9999)赋值为0,例如-9999.Con("raster"==-9999,0,"raster")2.给空值赋予特定的值(如0)Con(IsNull("raster"),0,"raster")3.将特定的栅格值(如1)赋值为空值,其他保留原值SetNull("raster"==
- 水平垂直居中的几种方法(总结)
LJ小番茄
CSS_玄学语言htmljavascript前端csscss3
1.使用flexbox的justify-content和align-items.parent{display:flex;justify-content:center;/*水平居中*/align-items:center;/*垂直居中*/height:100vh;/*需要指定高度*/}2.使用grid的place-items:center.parent{display:grid;place-item
- 本周第二次约练
2cfbdfe28a51
中原焦点团队中24初26刘霞2021.12.3约练161次,分享第368天当事人虽然是带着问题来的,但是咨询过程中发现,她是经过自己不断地调整和努力才走到现在的,看到当事人的不容易,找到例外,发现资源,力量感也就随之而来。增强画面感,或者说重温,会给当事人带来更深刻的感受。
- 放下是一段成长的修行
小莳玥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生和死。一件事已经做完了,另一件你还急什么呢?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是心,都有喜怒哀乐,这些再正常不过了。别总抱怨自己活得累,过得辛苦。永远记住:舒坦是留给死人的。苦,才是生活;累,才是工作;变,才是命运;忍,才是历练;容,才是智慧;静,才是修养;舍,才会得到;做,才会拥有。人生,活得太清楚,才是最大的不明白。有些事,看得很清,却说不清;有些人,了解很深,却猜不透;有些
- 回溯 Leetcode 332 重新安排行程
mmaerd
Leetcode刷题学习记录leetcode算法职场和发展
重新安排行程Leetcode332学习记录自代码随想录给你一份航线列表tickets,其中tickets[i]=[fromi,toi]表示飞机出发和降落的机场地点。请你对该行程进行重新规划排序。所有这些机票都属于一个从JFK(肯尼迪国际机场)出发的先生,所以该行程必须从JFK开始。如果存在多种有效的行程,请你按字典排序返回最小的行程组合。例如,行程[“JFK”,“LGA”]与[“JFK”,“LGB
- Python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战指南
William数据分析
pythonpython数据
在数据驱动的时代,Python因其简洁的语法、强大的库生态系统以及活跃的社区,成为了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的首选语言。本文将通过一个详细的案例,带领大家学习如何使用Python进行数据分析,并通过可视化来直观呈现分析结果。一、环境准备1.1安装必要库在开始数据分析和可视化之前,我们需要安装一些常用的库。主要包括pandas、numpy、matplotlib和seaborn等。这些库分别用于数据处理、数学
- 每日一题——第八十四题
互联网打工人no1
C语言程序设计每日一练c语言
题目:编写函数1、输入10个职工的姓名和职工号2、按照职工由大到小顺序排列,姓名顺序也随之调整3、要求输入一个职工号,用折半查找法找出该职工的姓名#define_CRT_SECURE_NO_WARNINGS#include#include#defineMAX_EMPLOYEES10typedefstruct{intid;charname[50];}Empolyee;voidinputEmploye
- 对股票分析时要注意哪些主要因素?
会飞的奇葩猪
股票 分析 云掌股吧
众所周知,对散户投资者来说,股票技术分析是应战股市的核心武器,想学好股票的技术分析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重点学习的,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要记住三个要素:成交量、价格趋势、振荡指标。
一、成交量
大盘的成交量状态。成交量大说明市场的获利机会较多,成交量小说明市场的获利机会较少。当沪市的成交量超过150亿时是强市市场状态,运用技术找综合买点较准;
- 【Scala十八】视图界定与上下文界定
bit1129
scala
Context Bound,上下文界定,是Scala为隐式参数引入的一种语法糖,使得隐式转换的编码更加简洁。
隐式参数
首先引入一个泛型函数max,用于取a和b的最大值
def max[T](a: T, b: T) = {
if (a > b) a else b
}
因为T是未知类型,只有运行时才会代入真正的类型,因此调用a >
- C语言的分支——Object-C程序设计阅读有感
darkblue086
applec框架cocoa
自从1972年贝尔实验室Dennis Ritchie开发了C语言,C语言已经有了很多版本和实现,从Borland到microsoft还是GNU、Apple都提供了不同时代的多种选择,我们知道C语言是基于Thompson开发的B语言的,Object-C是以SmallTalk-80为基础的。和C++不同的是,Object C并不是C的超集,因为有很多特性与C是不同的。
Object-C程序设计这本书
- 去除浏览器对表单值的记忆
周凡杨
html记忆autocompleteform浏览
&n
- java的树形通讯录
g21121
java
最近用到企业通讯录,虽然以前也开发过,但是用的是jsf,拼成的树形,及其笨重和难维护。后来就想到直接生成json格式字符串,页面上也好展现。
// 首先取出每个部门的联系人
for (int i = 0; i < depList.size(); i++) {
List<Contacts> list = getContactList(depList.get(i
- Nginx安装部署
510888780
nginxlinux
Nginx ("engine x") 是一个高性能的 HTTP 和 反向代理 服务器,也是一个 IMAP/POP3/SMTP 代理服务器。 Nginx 是由 Igor Sysoev 为俄罗斯访问量第二的 Rambler.ru 站点开发的,第一个公开版本0.1.0发布于2004年10月4日。其将源代码以类BSD许可证的形式发布,因它的稳定性、丰富的功能集、示例配置文件和低系统资源
- java servelet异步处理请求
墙头上一根草
java异步返回servlet
servlet3.0以后支持异步处理请求,具体是使用AsyncContext ,包装httpservletRequest以及httpservletResponse具有异步的功能,
final AsyncContext ac = request.startAsync(request, response);
ac.s
- 我的spring学习笔记8-Spring中Bean的实例化
aijuans
Spring 3
在Spring中要实例化一个Bean有几种方法:
1、最常用的(普通方法)
<bean id="myBean" class="www.6e6.org.MyBean" />
使用这样方法,按Spring就会使用Bean的默认构造方法,也就是把没有参数的构造方法来建立Bean实例。
(有构造方法的下个文细说)
2、还
- 为Mysql创建最优的索引
annan211
mysql索引
索引对于良好的性能非常关键,尤其是当数据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索引的对性能的影响越发重要。
索引经常会被误解甚至忽略,而且经常被糟糕的设计。
索引优化应该是对查询性能优化最有效的手段了,索引能够轻易将查询性能提高几个数量级,最优的索引会比
较好的索引性能要好2个数量级。
1 索引的类型
(1) B-Tree
不出意外,这里提到的索引都是指 B-
- 日期函数
百合不是茶
oraclesql日期函数查询
ORACLE日期时间函数大全
TO_DATE格式(以时间:2007-11-02 13:45:25为例)
Year:
yy two digits 两位年 显示值:07
yyy three digits 三位年 显示值:007
- 线程优先级
bijian1013
javathread多线程java多线程
多线程运行时需要定义线程运行的先后顺序。
线程优先级是用数字表示,数字越大线程优先级越高,取值在1到10,默认优先级为5。
实例:
package com.bijian.study;
/**
* 因为在代码段当中把线程B的优先级设置高于线程A,所以运行结果先执行线程B的run()方法后再执行线程A的run()方法
* 但在实际中,JAVA的优先级不准,强烈不建议用此方法来控制执
- 适配器模式和代理模式的区别
bijian1013
java设计模式
一.简介 适配器模式:适配器模式(英语:adapter pattern)有时候也称包装样式或者包装。将一个类的接口转接成用户所期待的。一个适配使得因接口不兼容而不能在一起工作的类工作在一起,做法是将类别自己的接口包裹在一个已存在的类中。 &nbs
- 【持久化框架MyBatis3三】MyBatis3 SQL映射配置文件
bit1129
Mybatis3
SQL映射配置文件一方面类似于Hibernate的映射配置文件,通过定义实体与关系表的列之间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使用<select>,<insert>,<delete>,<update>元素定义增删改查的SQL语句,
这些元素包含三方面内容
1. 要执行的SQL语句
2. SQL语句的入参,比如查询条件
3. SQL语句的返回结果
- oracle大数据表复制备份个人经验
bitcarter
oracle大表备份大表数据复制
前提:
数据库仓库A(就拿oracle11g为例)中有两个用户user1和user2,现在有user1中有表ldm_table1,且表ldm_table1有数据5千万以上,ldm_table1中的数据是从其他库B(数据源)中抽取过来的,前期业务理解不够或者需求有变,数据有变动需要重新从B中抽取数据到A库表ldm_table1中。
- HTTP加速器varnish安装小记
ronin47
http varnish 加速
上午共享的那个varnish安装手册,个人看了下,有点不知所云,好吧~看来还是先安装玩玩!
苦逼公司服务器没法连外网,不能用什么wget或yum命令直接下载安装,每每看到别人博客贴出的在线安装代码时,总有一股羡慕嫉妒“恨”冒了出来。。。好吧,既然没法上外网,那只能麻烦点通过下载源码来编译安装了!
Varnish 3.0.4下载地址: http://repo.varnish-cache.org/
- java-73-输入一个字符串,输出该字符串中对称的子字符串的最大长度
bylijinnan
java
public class LongestSymmtricalLength {
/*
* Q75题目:输入一个字符串,输出该字符串中对称的子字符串的最大长度。
* 比如输入字符串“google”,由于该字符串里最长的对称子字符串是“goog”,因此输出4。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
- 学习编程的一点感想
Cb123456
编程感想Gis
写点感想,总结一些,也顺便激励一些自己.现在就是复习阶段,也做做项目.
本专业是GIS专业,当初觉得本专业太水,靠这个会活不下去的,所以就报了培训班。学习的时候,进入状态很慢,而且当初进去的时候,已经上到Java高级阶段了,所以.....,呵呵,之后有点感觉了,不过,还是不好好写代码,还眼高手低的,有
- [能源与安全]美国与中国
comsci
能源
现在有一个局面:地球上的石油只剩下N桶,这些油只够让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顺利过渡到宇宙时代,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为争夺这些石油而发生战争,其结果是两个国家都无法平稳过渡到宇宙时代。。。。而且在战争中,剩下的石油也会被快速消耗在战争中,结果是两败俱伤。。。
在这个大
- SEMI-JOIN执行计划突然变成HASH JOIN了 的原因分析
cwqcwqmax9
oracle
甲说:
A B两个表总数据量都很大,在百万以上。
idx1 idx2字段表示是索引字段
A B 两表上都有
col1字段表示普通字段
select xxx from A
where A.idx1 between mmm and nnn
and exists (select 1 from B where B.idx2 =
- SpringMVC-ajax返回值乱码解决方案
dashuaifu
AjaxspringMVCresponse中文乱码
SpringMVC-ajax返回值乱码解决方案
一:(自己总结,测试过可行)
ajax返回如果含有中文汉字,则使用:(如下例:)
@RequestMapping(value="/xxx.do") public @ResponseBody void getPunishReasonB
- Linux系统中查看日志的常用命令
dcj3sjt126com
OS
因为在日常的工作中,出问题的时候查看日志是每个管理员的习惯,作为初学者,为了以后的需要,我今天将下面这些查看命令共享给各位
cat
tail -f
日 志 文 件 说 明
/var/log/message 系统启动后的信息和错误日志,是Red Hat Linux中最常用的日志之一
/var/log/secure 与安全相关的日志信息
/var/log/maillog 与邮件相关的日志信
- [应用结构]应用
dcj3sjt126com
PHPyii2
应用主体
应用主体是管理 Yii 应用系统整体结构和生命周期的对象。 每个Yii应用系统只能包含一个应用主体,应用主体在 入口脚本中创建并能通过表达式 \Yii::$app 全局范围内访问。
补充: 当我们说"一个应用",它可能是一个应用主体对象,也可能是一个应用系统,是根据上下文来决定[译:中文为避免歧义,Application翻译为应
- assertThat用法
eksliang
JUnitassertThat
junit4.0 assertThat用法
一般匹配符1、assertThat( testedNumber, allOf( greaterThan(8), lessThan(16) ) );
注释: allOf匹配符表明如果接下来的所有条件必须都成立测试才通过,相当于“与”(&&)
2、assertThat( testedNumber, anyOf( g
- android点滴2
gundumw100
应用服务器android网络应用OSHTC
如何让Drawable绕着中心旋转?
Animation a = new RotateAnimation(0.0f, 360.0f,
Animation.RELATIVE_TO_SELF, 0.5f, Animation.RELATIVE_TO_SELF,0.5f);
a.setRepeatCount(-1);
a.setDuration(1000);
如何控制Andro
- 超简洁的CSS下拉菜单
ini
htmlWeb工作html5css
效果体验:http://hovertree.com/texiao/css/3.htmHTML文件:
<!DOCTYPE html>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title>简洁的HTML+CSS下拉菜单-HoverTree</title>
- kafka consumer防止数据丢失
kane_xie
kafkaoffset commit
kafka最初是被LinkedIn设计用来处理log的分布式消息系统,因此它的着眼点不在数据的安全性(log偶尔丢几条无所谓),换句话说kafka并不能完全保证数据不丢失。
尽管kafka官网声称能够保证at-least-once,但如果consumer进程数小于partition_num,这个结论不一定成立。
考虑这样一个case,partiton_num=2
- @Repository、@Service、@Controller 和 @Component
mhtbbx
DAOspringbeanprototype
@Repository、@Service、@Controller 和 @Component 将类标识为Bean
Spring 自 2.0 版本开始,陆续引入了一些注解用于简化 Spring 的开发。@Repository注解便属于最先引入的一批,它用于将数据访问层 (DAO 层 ) 的类标识为 Spring Bean。具体只需将该注解标注在 DAO类上即可。同时,为了让 Spring 能够扫描类
- java 多线程高并发读写控制 误区
qifeifei
java thread
先看一下下面的错误代码,对写加了synchronized控制,保证了写的安全,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public class testTh7 {
private String data;
public String read(){
System.out.println(Thread.currentThread().getName() + "read data "
- mongodb replica set(副本集)设置步骤
tcrct
javamongodb
网上已经有一大堆的设置步骤的了,根据我遇到的问题,整理一下,如下:
首先先去下载一个mongodb最新版,目前最新版应该是2.6
cd /usr/local/bin
wget http://fastdl.mongodb.org/linux/mongodb-linux-x86_64-2.6.0.tgz
tar -zxvf mongodb-linux-x86_64-2.6.0.t
- rust学习笔记
wudixiaotie
学习笔记
1.rust里绑定变量是let,默认绑定了的变量是不可更改的,所以如果想让变量可变就要加上mut。
let x = 1; let mut y = 2;
2.match 相当于erlang中的case,但是case的每一项后都是分号,但是rust的match却是逗号。
3.match 的每一项最后都要加逗号,但是最后一项不加也不会报错,所有结尾加逗号的用法都是类似。
4.每个语句结尾都要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