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忆十六位大先生|《山高水长集》
一日一书
读本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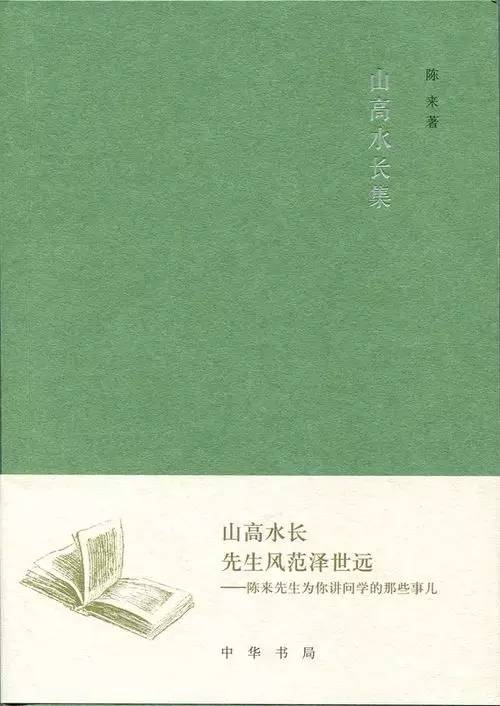
山高水长集
作者: 陈来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5-5
页数: 278
定价: 32.00元
《山高水长集》记述了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季羡林、朱伯崑、邓广铭、周一良、傅伟勋、何炳棣、陈荣捷等先生学问、人生的感人情事,以及作者向这些先生问学与交往的情形;此外,还记录了有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清华前辈的一些往事,以及作者代表清华大学国学院为上述前辈举办活动、出版有关书籍所写的一些文字。本书有两大特点,一是所记录的几乎都是哲学界顶级学者,其间的事情一般外界很难知悉,所以极为珍贵;二是目前作者在哲学领域所处的地位,也使本书眼界高远,视野开阔。本书文字流畅优美,具有哲学家的透彻和洗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记冯友兰先生
by陈来

一 特识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讲到王阳明晚年的学问境界,用了王龙溪的两句话:“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我觉得这两句话正可以用来表达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学问修养。
自1980年以后,冯先生的主要工作是撰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新编》体现了冯先生近年的思想。《新编》是对旧著而言,故要了解《新编》,不能不涉及到他的旧著《中国哲学史》。众所周知,冯先生有几种享誉学界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三十年代初写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他自己习称为“大哲学史”;此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小史》,和原在美国用英文出版、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中国哲学简史》。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仍是冯先生这一部“大哲学史”。晚近有学者批评冯先生此书不过是大量引经据典和被动式的注释,与西方学者哲学思辨的功夫相差太远,这种评论显然是不公允的。因为冯先生此书,正如书名所表示的,乃是一部哲学史著作,而不是哲学论著,读过“贞元六书”的人是不应该以“过重引述经典”来评判冯先生的哲学著作的。而且,与写西洋哲学史不同,有著作经验的人都会了解,用中文著写中国哲学史,必须引述经典的古汉语原文,尔后再加说明阐释,这已是一条不成文之通例,不足以成为此类著述之病。
《中国哲学史》出版时,陈寅恪先生曾作审查报告,有言:“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近几十年,学界每批评冯先生用新实在论讲程朱理学,其实,冯先生当初在美国学的若不是新实在论,而是实用主义或别的什么西方近代哲学,他是否能写出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史》来,是值得怀疑的。新实在论注重的共相殊相、一般特殊的问题,确实是古今中西哲学共有的基本问题,不管新实在论的解答正确或者不正确,冯先生由此入手,深造自得,才能使他“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哲学上实有所见而自成一家。而程朱理学,在哲学上也确有与新实在论相通之处,所以,冯先生从新实在论的立场所阐发的程朱理学的哲学见解,还是相当深刻的。
关于《中国哲学史》一书的“特识”,冯先生后来在《三松堂自序》中这样说:“就我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的内容来说,有两点我可以引以自豪,第一点是,向来的人都认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学,其主要的辩论就是‘合同异、离坚白’,认为这无非都是一些强辞夺理的诡辩。战国时论及辩者之学,皆总称其学为‘坚白同异’之辩,此乃笼统言之,我认为其实辩者之中分二派,一派主张合同异,一派主张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第二点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后来的研究者都以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统称为‘程门’,朱熹引用他们的话,往往都统称‘程子曰’,不分别哪个程子。我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不同的,故本书谓明道乃以后心学之先驱,而伊川乃以后理学之先驱也。这两点我以为都是发先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
冯先生此说是太过谦虚了。其实,从学术上看,在上述两点而外,不但《中国哲学史》的基本结构、人物、条理为此后写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所继承,书中的诸多观点和提法,如孔子的正名主义,墨子的功利主义,孟子的理想主义,老庄的楚人精神,法家的三种派别,王充的自然主义,《列子》的唯物主义,以及程朱异同、朱陆异同、朱王异同、佛教的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等,也都是“发先人之所未发,后来也不能改变的”,至今仍为学术界沿袭或吸取。其中大部分的分析和定位已成了本学科的“典范”,美国和日本的不少大学至今仍以此书为基本教本,这是与它的多方面的成就分不开的。
二 可怪之论
说到《新编》,可能会有人问,用冯先生以前常爱用的“瓶”“酒”的说法,到底是“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旧酒”,或是“新瓶装新酒”?就冯先生的主观想法来看,他是想尽量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考察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和发展,因而在形式方面大量采用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概念范畴,就这点来说,“新瓶”是可以肯定的,至于瓶中之酒,就不能简单地说是新是旧了。
在我看来,与旧著相比,从大的方面说,《新编》有两点突出的、与原来的“大哲学史”不同的特色。第一是对一般和特殊的问题理出了基本线索。冯先生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有一根本的线索贯穿其中,这就是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冯先生常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先秦儒家讲的正名,道家讲的有无,名家讲的名实,归根到底都是这个问题,玄学所讲的有无,道学所讲的理事,归根到底也都是这个问题。”旧著只是在“伊川”“朱子”两章中讲到这个问题,没有贯穿到整个中国哲学史,冯先生认为这次写《新编》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第二是把考察阐述中国哲学的精神境界作为一个基本着眼点。冯先生认为,哲学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中国哲学在这方面对人类文明有较大贡献,所以应当特别加以阐扬。举例来说,冯先生谈到玄学的“体无”时强调,这代表了一种混沌的精神境界。没有经过分别的、自然而有的混沌可称为“原始的混沌”;经过分别之后而达到无分别乃是高一级的混沌,可称为“后得的混沌”。诗人乐草木之无知,羡儿童之天真,其实草木并不知其无知,儿童也不知道他们是天真。“原始”与“后得”的区别,就在有自觉和无自觉,玄学代表的就是自觉的无区别、无计较的精神境界。这样的精神境界,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逍遥”“玄冥”。可是有这样境界的人,并不需要脱离人伦日用,对于外物也不是没有反应,所以从玄学一转,就是道学的“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物来而顺应,廓然而大公”。
“大哲学史”写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而“新理学”的体系形成之后,冯先生对共相殊相的问题在哲学及哲学史上的意义,更有自觉的重视,就这一点说,《新编》重视共相殊相,与冯先生四十年代的思想,是有一脉相承之联系。在《新原人》中也讨论过人的四种精神境界,不过,我自己的感觉是,《新原人》以“天地境界”为最高,虽然说来是如此,但似终有一间未达,并有说得过高处,未如《新编》论玄学和道学的境界透彻圆融。我以为这是由于四十年来,冯先生自己的精神境界与日俱进,屡经磨难而更臻于圆达,如元好问所谓“亲到长安”者,因为他对这些精神境界有真“受用”,所以说出便与人不同。有一次冯先生对我说:“参前倚衡,‘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是说的孔子的精神境界啊。”冯先生说的话和当时说话时的神情给我印象甚深,我认为他对这些精神境界,确实是有真体会。
所以,从这两个基本点来说,就难以用新酒旧酒截然分开来说了。如果说新,“新”与“旧”也有联系;说旧,“旧”的也有了“新”的发展。从前朱子和陆子寿诗有两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从这方面看冯先生,也可以说“旧学”益密,“新知”益深。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之序中,说自己“已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海外朋友常有冯先生晚年是否已经糊涂的疑问,其实不然。就以冯先生晚年的情况说,据医生讲,自1986年视力大减之后,脑力更见增益。我帮助冯先生作《新编》,对冯先生思维之敏捷,每感惊讶,现举几例来说明。
在写《新编》的过程中,冯先生每创新意,不落旧套。写魏晋玄学时他说:“我有一想法,王弼是贵无论,裴頠是崇有论,郭象是无无论;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郭象的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冯先生发明了“无无论”一词讲郭象,又提出郭象对贵无、崇有作了“扬弃”,破除了终极的无,但不否定境界的无,这样一来,就把玄学从纵到横重新贯穿起来了。冯先生很注意每一大的时期的哲学发展线索,写到宋明时他又提出:“道学可分为两期。从前期看,二程讲理是肯定,张载讲气是否定,朱子是否定之否定。到了道学的后一阶段,前一阶段的‘否定的否定’就成了后一阶段开始的肯定,因此阳明是朱子的否定,王船山是否定的否定。”照冯先生这个说法,王船山不但是朱子的否定之否定,即更高程度的肯定,而是整个宋明道学发展的集大成者,这与时论视船山为反道学唯心论的唯物主义大师的观点,相去大远;而他对“肯定”/“否定”发展关系的看法,也与一般的辩证法家大不相同。冯先生说,这在许多人看来,可能是可怪之论。
冯先生虽年过九旬,哲学思维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正如古人所谓“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始须臾忘也”。他常常语出惊人,提出与时论有所不同的种种“新意”,并且每戏称之为“非常可怪之论”。前边说的就是个例子。宋明的一册快要写完的时候,一日他又对我说:“我近来又有一个想法,也可以说是非常可怪之论,就是毛泽东的哲学实际上也是接着中国古典哲学讲的。”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他们理解的中国化,是指在实践上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照冯先生看,这个“化”不可能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没有关系。冯先生说:“从孔子到王船山,中国哲学有个基本问题,就是一般和特殊的问题。到了王船山,给了一个解决,解决的方法是‘理在事中’,毛的《矛盾论》《实践论》讲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其思想归结起来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这个寓字从前人不常用,而这个思想也就是‘理在事中’,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事上求理。”找出这个联系,冯先生颇满意,他说:“《西厢记》中红娘有一句唱调,说‘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么一来,毛的思想和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接上了。”
《新编》写到清近代的时候,冯先生又有了一个“非常可怪之论”。他说:“时人称许太平天国,贬骂曾国藩,可是从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来说,洪秀全要学习并搬到中国的,是以小农平均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中国当时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所以洪秀全的理想若真实现,中国就要倒退。这样一来,自然就把他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主观上是如何是一回事,但客观上看,他打败了太平天国是阻止了中国的一次倒退。不过曾推行一套以政代工的方针,违背了西方国家近代化以商代工的自然道路,又延迟了近代化。”冯先生对曾、洪的评价与几十年来近代史学界的流行观点完全相反,学术界对此自然有不同的反应。
1988年我从美国回来后,冯先生对我谈《新编》的进展情况,他说:“我又有了几个‘非常可怪之论’。照马克思本来的想法,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照这个道理说,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只有另一次在广度、深度上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类似的新产业革命出现之后才能出现,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另一点是,几十年来赞美农民政权等贵贱、均贫富,其实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农民起义成功,建立的还是旧的生产关系和等级制度,所以‘农民政权’是没有的。这是因为农民是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是这个生产关系的内在的一部分,他没有办法提出新的生产关系来。由此引出一点,现在计算机和超导材料的发展,也许会造成一个大的产业革命,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新的生产关系出现,以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以上所举数条,不过是借此使人一窥冯先生晚年思想之活跃,这些观点人们可以因为他受黑格尔、马克思影响太大而不同意,但由此可见冯先生的哲学思维确乎未尝一日而中断。他的思想,一方面总是充分利用既有的一切形式,扣紧时代的课题,另一方面也从内容上作各种积极的转化。
三 道学气象
我在198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以“道学气象”论冯先生。我还说,冯先生气象最近于程明道,不过什么是我所了解的明道气象,则语焉而未详。
冯先生一向最为推崇程明道《秋日》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平时闲居亦常讽咏。我想冯先生所以喜欢这首诗,从精神境界来说,是因为他对“从容”“自得”有真受用。他的宽裕温平、和易怡悦、从容自得的气象,充分体现了他的精神境界。他的晚年气象正如古人所说“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如时雨之润”。在我的了解中,明道与冯先生互相辉映,充养完粹,神定气和,动静端详,闲泰自然,未尝有忿厉之容,冯先生乐易和粹的气象,是我所了解的明道气象的具体表现。
近人论冯先生学问,皆知《新理学》是“接着”伊川讲的,殊少知其气象境界尤近于明道。人之学问与气象不可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陈白沙曾言“学者须理会气象”。所以我常想,儒学在中国不得复兴,只讲生命进动,缺乏涵养气象一节,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吧。
1986年,我赴哈佛访问研究,行前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冯先生,当时第五册只剩下王船山未写完。冯先生说,可惜《新编》的写作没法得到你的帮助了。1988年我回国后,见冯先生身体大体上与前两年相近,只是目力大退。我赴美前,冯先生偶尔还可以戴上眼镜把书拿到眼睛前边看,现在已不能看书。有客来访,可以看得一个轮廓,但不能分辨。不过倒也由此省去了摘戴眼镜的麻烦。
1985年,有一次杜维明教授携太太若山(Rossane)及不满两岁的儿子在冯先生家做客,冯先生竟问杜太太:“你是四川人吧。”这固然可以表现出黄发碧眼的杜太太的中国话已可以“以假乱真”,也说明冯先生“耳目失其聪明”的程度。人入老境,常有慈幼之心,从前冯先生几次对我提起:“杜维明的那个小孩很好玩。”1988年我从哈佛回来,他又说起:杜维明那个小孩很好玩。
冯先生说话从容平缓,但不乏风趣诙谐。198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朱荣贵博士忽到北大,我陪他去访冯先生,谈话间说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现在有多少院士,朱荣贵说:“台湾现在不会承认您是院士了。”冯先生笑道:“那是当然,开除院籍!”
冯先生常对我说,有那么一个客观的道理,古今中西的人都可能有所见,即使讲的相同,也不必是抄袭,因为本来就有那么一个客观的道理。我曾问他,写“贞元六书”时有没有继承儒学传统的意思,冯先生说:“当时是有这个意思,不过现在并没有这个意思了,因为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这个界限对我来说已经打通了。我现在觉得好东西都是通的,康德和禅宗也是通的。”冯先生还说:“我现在就像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去的草再吐出来细嚼慢咽,不仅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吧!”
我帮冯先生写《新编》曾有好几年,工作的性质我在另一篇文章已经谈过(见《当代》十九期《十年道问学》)。冯先生总是以为我很懂哲学,所以希望我常去谈谈。其实我根本是似懂非懂,冯先生每每给我许多特别的启发,使我得益极大。每当冯先生“津津有味”地谈说他的种种思考所得时,我便坐在对面默然而“观”。这种“观”并非现在人所说的看,而是从中体会,体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真正的“中国特色”的学者怎么思考,体会他对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所抱的态度。数年之中,所闻所观者,不为不详,然终觉未能得其达者大者。噫!语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先生其此人也欤!
(原载《读书》1990年第1期)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作多种,除《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卷(包括:《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朱子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版)、《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增订版)、《宋元明哲学史教程》《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增订版))外,还有《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等。

“2015凤凰网年度图书”发布|如果我们沉默,世界仿佛也无声
 主编:严彬(微信号:niaasai) 责编:Choq
主编:严彬(微信号:niaasai) 责编:Cho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