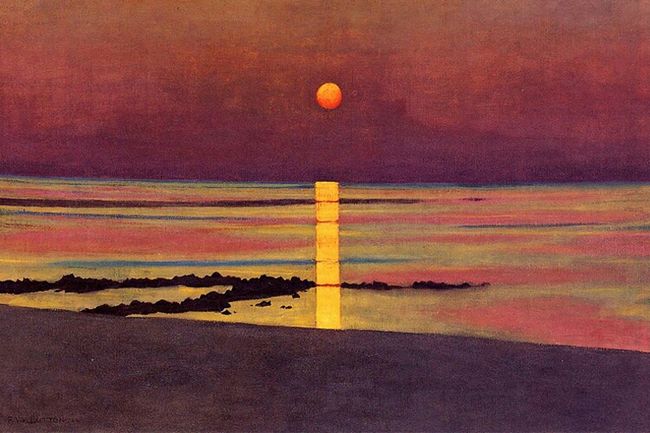早些年间,村里造就出第一位“作家”。年轻时,风流倜傥,小有闻名,不久,省里派车,把他接了去,名义为“保护千年难得一遇的盛世奇才。”
再见他,是2005年腊月初八,我记得那时候吧,四季分明。夏天,就像加了柴,添了火的大锅炉,到了冬天,则是另一番景象,那些没人住的房前,门前的雪阿,十丈,正好淹没大人的臀部之上,腰部之下,譬如,作家的房前,我母亲是坚决不让我涉进一步。
和往常一样,爱闹腾的孩童出来撒泼,玩耍到作家房屋前时。
“啊~有死人!有死人!”从孩童之中某个角落,爆发出尖叫声,惊醒了村中的父老乡亲。
随即,一个,两个,三个……从忙中偷闲赶来的男人;从某条不知名的田沟里爬出来的孩童;从半月未踏出家门,畏惧新鲜事物的少男少女们,闻讯而来,纷沓将至。
“这不是去省城的作家吗?”村民甲说道。
“是啊,是啊,可不正是他嘛。”村民乙回答道。
一些年长且带着疑问的老者,迅速围了过去,有的人,探了探他的鼻息,看是否有一息尚存;有的人,从家中拿了一条破旧的毛毯,预盖在他的身上;有的人,盛了半碗热汤,正在往返的路上……
“村长来了,村长来了。”眼尖的村民丙向忙里忙外的老者、村妇,小声汇报道。
村长离作家的院子还有五里,嘴里叼着他的大烟斗,吧嗒吧嗒的吮吸着,冒着缕缕浓烟,时隐时现的面孔,竟给村长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捉摸不透,也猜不准他的心思,戴着他的大雕帽,听说是前几年自个在村中某个不知名的山林里打的野味,剥的皮,制作而成。村里某些人虽眼红、羡慕、嫉妒的发狂,却也奈何不了。村长双手交叉,藏在厚实的衣袖中,一深一浅的走了过来。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的那些村民叔叔婶婶们,知晓村长伯伯正在赶来,反道是拘谨着,左右为难着。那个正在探鼻息的老者,忙缩回右手中指;那个拿了一条破旧毛毯的村妇,迅速将毛毯披回了自己身上;那个端着半碗热汤的青年,站在院子前,栅栏之外,一口干了半碗热汤,像是见了妖魔鬼怪,大难临头似的,仿佛在宣告:我没有出手相助,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不禁笑出了声,父亲荡了荡牵着我的右手,我朝上瞧了瞧,紧皱着眉头,两眼死盯着路面,不知向谁摇了摇头,亦或是叹息着,只不过条件不允许他出声。
村长步入栅栏前,努了努嘴,朝嘴角还有汤汁的有为青年斜了一眼,青年回应村长的,是一声低沉且响亮且充满挑衅的饱嗝。
村长步入院中……
“村长来了,”村民们问候着。
“嗯,”村长回答道。
“村长,那个……”村民甲伸出长年酸痛的右手臂,手心手背面向前,握拳,用那粗糙的右中指,指了指。
“死了没?”村长抽着大烟,蹲在作家“尸体”脚前面。
“没,暂时还没,不过,快了。”村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吱了声。
“来人,”村长把烟斗里的烟灰往雪地里倒了倒,站起来,掸了掸衣服上面的烟渣,往前挪了挪,“把他抬到王二狗家去,他家宽敞,通风,对了,还来一人,去镇医院请最好的大夫,他,我们不可怠慢,特别是他的脑袋,你们抬的时候小心点,别磕着脑袋。”
村民无一人行动。
“怎么,有异议?”村长展现着气势磅礴的村威。
“村长,要不抬到我家去?我们家有个不学无术,但偏偏爱自个琢磨医术的不孝子,说不定啊,能医好这位贵人。”村民丁顶着官威,怯声声的问道。
“是啊,是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要不试试?”村民乙附声和道。
“哟,你们家?你们家能供的起这尊大菩萨吗?”村长阴阳怪气的调侃,“万一出了什么事,你能负责?”
村民一时鸦雀无声,手足无措。
“抬到我家去,宋老大,把你家那位不孝子捆来给他好好瞧瞧,怎么说,也是村里的人,出事,我负责,王二狗家,不能去,不能去,我先行一步,村长大人。”那位吱声的老者再度吱了声,拄着田里的棉梗子,走出了院子。
“村长,那,我们也先行一步。”村民甲招呼着几人,欲抬着作家告辞。
“走,走,走,眼不见为净,我就瞅着这个老东西死后,谁还能给你们撑腰,一个个不把老子放在眼里,我还当个球的村长,啊,你们说,我还当这个村长干嘛,真特么窝囊,呸!”双面充血,眼球爆出,头发直竖的村长,在我往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梦魇,是恶魔缠着心智。
村长甲他们几个,往前迈了几小步,又往后退了几大不,手上抬着作家,放下也不是,不放下也不是,尴尬至极。
“抬走呀,我说你们几个,别在这给村长添堵了,难不成你们是想……”赵大爷棉衣棉裤搭配着,双脚着一红一白大棉鞋,双手插进口袋,眉头轻佻,嘴角下撇,学着村长的官腔,笑煞旁人,“难道你们还想村长请你们吃午饭,还是给你们颁一条好人好事的锦旗?哎哟喂,你们可别难为他了。”
“噗嗤~”我不是故意的。
赵大爷向我眨了眨眼,“孺子可教,孺子可教也。”顺便使了使眼色,让村民甲赶紧功成而退,去往村口那户人家。
村民甲,出。
“赵七成,你……你太放肆了。”村长轻轻一掰,烟斗变成了孤魂,我为此惋惜了几秒。
赵大爷依旧老模样,插着双手,哼着小曲,离开了,紧跟着,我们这些无良村名,也先后离去。院中,村长拿着“孤魂”,骂骂咧咧。
我看见栅栏外,有两条很新很深的轮胎印子,虽下着雪,可还不足以掩盖。
我听见王小丫说,她早晨出来尿尿时,看见一辆车驶进了村长院中。她的父母则满脸惊恐,连忙捂住丫丫的嘴,环顾四周,瞧见我和父亲,心急的解释道,“小孩子迷糊,不能信,不可信。”
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看见或是听见,一直走到家门前。
“以后,不准这样不分场合的笑。”父亲严肃的说。
我一脸无辜却惹急了父亲。
“你不懂,那赵大爷敢这样挑衅,完全是因为她妹妹是村长的老婆,知道了吗?你该钦佩的,是梁老太爷,但,也只能心里钦佩,知晓便可。”父亲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教育道。
“哦,”我勉勉强强的听懂了父亲的话里话外。
“还想当作家吗?”父亲询问。
“想,”我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想像作家一样苗条,这样才配穿母亲房间,左边衣柜里挂着那条白如雪的连衣裙。”
“好,我和你母亲给你三年时间,请给我们一本好书,父亲拭目以待。”
作家活了,我和父亲去拜访他时,比我在雪堆里见他胖了些许,老天待他不薄。
至于他为何突然出现在雪堆里,有的人说,是写了什么隐晦的东西,省级留不得他,念他还有些功劳,就遣返回村里了。
可不可信,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的是,春天的到临,希望,也来临了。
为什么是三年?
一年去观察,一年去经历,一年去写作。正如我看见的,全过程也算经历其中,呐,现在我将它创作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