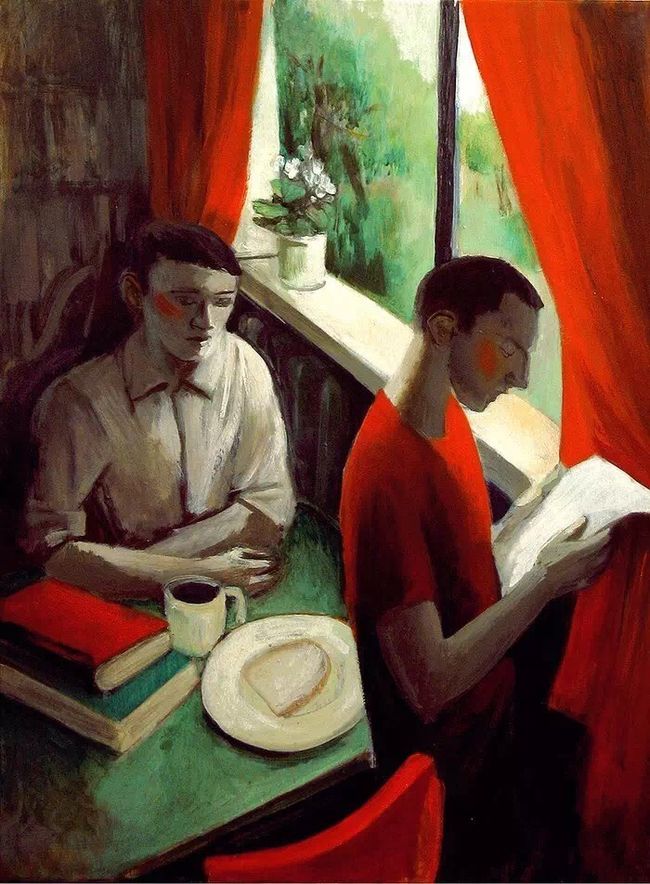文/Bluesea
人类性学研究生,关注性与爱
今天是517国际反歧视同性恋日,我们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同性恋这个话题。
在西心中,泰是他最在意的朋友。去年初冬,泰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萱乘坐了十一个小时的动车,来到西的城市看望西,这是泰新婚五日后做的第一件事。
当天,西特意去了火车站接这个一年才见得了一两次的朋友。
一只手拎着泰从老家带来的老字号小吃,另一只手查着百度地图,西带着泰和萱在这个依然令他觉得陌生的城市吃吃逛逛。
三个人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九点,泰要西和他去西的租房附近的手机店看看手机,萱因为天气太冷而选择先回酒店休息。
其实西知道,大多数手机店在晚上九点都已停止营业了,但他依然和泰在寒风中步行了二十分钟来到自己的租房附近。
当二人确认所有的店面都已经打烊后,他们掉头往回走。
这时,泰说:“我不熟悉路,你陪我走回酒店去吧。”
西接着说:“那我自己一个人再走回来?”
泰说:“难道不可以吗?”
听到这句温暖的话,西的脑海里回忆起了五年前的一天。
那时西和泰都上大二,西和泰在家乡的大街小巷闲逛,碰到了迎面而来的三五个同学,其中一个同学说到:“哟,你俩谈着的呀?”
泰答到:“那是的嘛,难道不可以嘛?”
对方继续开玩笑地问:“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啊?”
泰也笑呵呵地回答:“十来年吧”
时间再往前推一年,一天,伴随“嘀嘀嘀“的声音,西qq好友列表里那个熟悉的、停止了跳动两年多的海贼王qq头像又闪烁了起来。
西觉得开心,却又立马平静了下来,因为他担心这个闪烁的头像只是盗号者发来骚扰信息。
于是他期待而又紧张地点开消息,他看见对话框里出现这样一句话:“寒假帮我带一点周黑鸭回来行不行?”
西毫无准备,也不知道说什么,于是就点了一个疑问的表情发送给对方,接着,对黄框里出现那句熟悉的反问句:“难道不可以吗?”。
当时西的心像是被刀划了一下,这句原本轻松愉悦地反问句竟在那一刻诉说着乞求。
“难道不可以吗”,这句话对于对于泰和西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
上初三时,每当泰想抄西的作业,他会说“难道不可以吗?”
上高一时,每当泰想蹭西的单车,他也会说“难道不可以吗?”
上高二时,一天,泰对西说:“我觉得同性恋都该死,你不要告诉我你喜欢男的。”
西什么也没说,微笑着看了看泰。
泰接着说:“你笑什么,我警告你了,我可不想和同性恋一起玩儿。”
西面无表情地答到:“我就笑一下,难道不可以?”
泰又说:“就是不准笑,不可以?当心我帮(把)你这个异类的qq都删了”…….
这句反问的话成了二人的友情纽带,十二年来,每当他们试图获得对方同意、认可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会用到这句万能的反问句。
泰或许没有想过,常常爱将这句话挂在嘴边的自己自始至终其实都没能摆脱对一个同性的友情依赖,即便他曾经说自己不会和“同性恋”一起玩儿,他最终依然愿意不远千里地带着大包小包来看望这个住在他心里的朋友……
往泰的酒店方向走了会儿,西开玩笑地对泰说:“你居然沦落到了要一个“同性恋”送你回家的地步。”
这时,泰把自己的右手搭在西的右肩上,说:“哥啊,你应该知道我早就对同性恋没那些偏见了,以前,因为很多人觉得同性恋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什么都没想,也就自然而然地觉得我要远离同性恋,后来我思考过这个问题,想不通,但我可不想让这些偏见影响了我俩十几年的感情。”
“我不太懂你们同性恋的感受”,泰接着说,“反正现在这不会再影响我和同性恋的人做朋友了”。
西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看得开了啊?”
泰答:“你各方面都比我优秀,那我还有什么好看不起你的?而且你让我对同性恋有了更多正面的认识,你能勇敢地对我们坦白性倾向,我也是发自内心地佩服。我也专门去了解了你们这类人,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偏见了。虽然我现在还是不懂你们的感受,至少不会想当然地看不起同性恋了。”
是啊,在过去,有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左撇子不正常”,想当然地支持“妇女应该足不出户”,想当然地坚信“处女膜是女人贞操的象征”,这些想当然的偏见是如此腐朽,尽管曾经它们拥有无数的支持者,但它们终究还是没能在正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存活下来。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当一类人没有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甚至比自己为这个社会作出了更多的贡献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因为一些腐朽的偏见去歧视甚至敌视他们?
有人说“我讨厌同性恋,因为我听说就是他们在传播艾滋病病毒”。
而事实上,艾滋病病毒这种简单的生物根本不会识别谁是同性恋,谁是异性恋,科学调查的数据显示同性性接触导致的艾滋病病毒传播比异性性接触导致的传播要少得多。
有人说“我看不起同性恋,因为我听说他们非常的滥情”。
其实,当你认定滥情是不道德的,同时也认定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这样的两层有色眼镜会默契地配合,使你自然而然地过滤掉滥情的异性恋和不滥情的同性恋。
有人说“我憎恨同性恋,因为我听说他们在制造‘同妻’的悲剧”。
一些男同或者女同的确是制造“同妻”或“同夫”的执行者,而这些悲剧背后的指使者,其实正是不计其数的“恐同者”和我们社会根深蒂固的“恐同文化”啊。
有人说“我想救同性恋,因为我听说他们其实是得了一种病”。
同性恋的疾病之说其实源于克拉夫特-埃宾的《性精神病》一书,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分别在1992年、2001年就已经将同性恋从精神病中排出,确认这只是少数、自然的现象。
有人说“我排斥同性恋,因为我听说他们的行为跟罪恶别无两样”。
殊不知中国在1997年就已经将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实际上,同性性倾向并没有也不可能引导人们去实施犯罪行为。
我还听说过我的某位同事就是同性恋,另一位同事的表姐也是同性恋,一位同学的爸爸是双性恋,某个明星的儿子就是同性恋。听说一个个同性恋可能正好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听说过很多很多和同性恋有关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越是能去进行客观地了解,就越能正确地辨别真相和谣言。
而所有的谣言就如“鞋子没掉,还有救”这样的梗一样,只是旧时代的错误经验,也必然会成为新时代的用于搞笑的梗。
真相其实是世界本来就是由很多的不一样组成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先天或者后天都存在一些不及他人之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是有权利享受生命之美好的人。
在不同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不同情况的少数群体,正是一个个不同的少数群体共同组成了人类这个庞大的群体。
正如泰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对少数群体有偏见,是因为文化偏见导致我们建立起的关于这类人的错误认知,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认知就是真理,被文化深深束缚的我们不愿意去客观地了解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并优越地认为这些人就是异类。
只有我们突破这样的束缚,我们才能无需勇敢地去在意那个被你藏在心中两年多的“异类”,才能无拘无束地将你的右手搭载这个“异类”的右肩上陪他前行,才能毫无忌惮地在众人面前笑呵呵地坦白你和这个“异类”十多年的感情。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挣脱这样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异类”也会因此更加勇敢,不愿再藏在柜子里,走出来,去勇敢地直面人生,追求幸福。
而身为“异类”的你,同样需要有更强大的心去面对这些恶魔般的偏见,用更坚韧的力量去挣脱这些根深蒂固的束缚,你的退缩和沉默会使它们变得更加强大。
蜜蜂负责酿蜜,花朵负责芬芳,蚯蚓负责松土,大树负责阴凉,世界很大,有很多的“不一样”。
面对这些“不一样”,我们无须让每个人变得一样,只要一个微笑、一些合理的沟通、一些正确的认知,大家便可以其乐融融地共享生命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