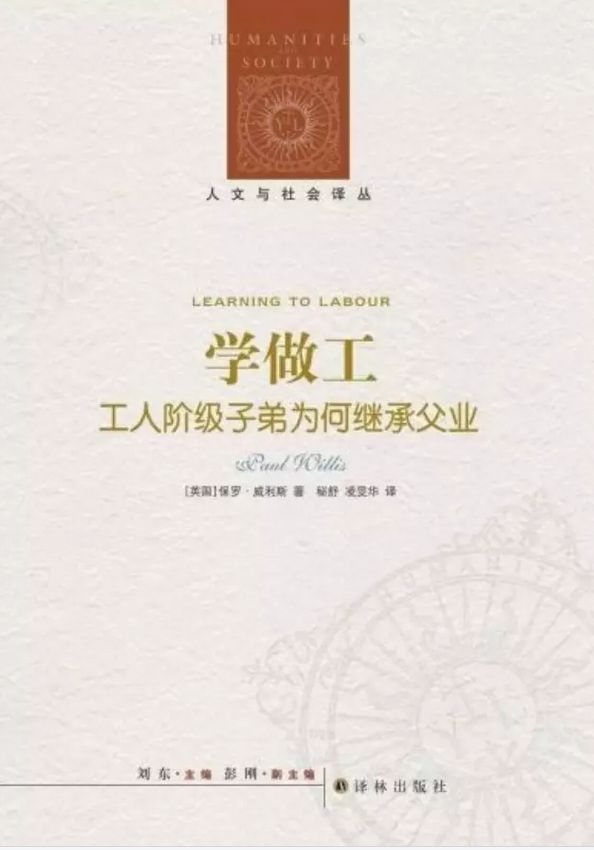将民族志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传统,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1977)并非首创。恩格斯早在1844-1845年所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便已运用这种方法来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政治意识。二十世纪英国文化研究承续了这种民族志传统,而其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文化。譬如威利斯深受影响的霍加特的著作《教养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1957),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不过,即便置身如此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志传统,威利斯的研究仍然显示出突破性的学术贡献。尤其是他对工人阶级文化内在的复杂性与悖谬性的探讨,更是创见迭出,启人深思。本文试图借助这些探讨,重省工人阶级文化的现实境遇与未来可能。
1. 反抗的文化形式与阶级身份的再生产
在《学做工》中,威利斯分析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形式"。要理解这个概念,就必须先了解他对文化概念的基本判断。在该著开头,威利斯这样写道:"文化不仅是一套被传递的内部结构(如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也不仅是主导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消极结果(比如在某些马克思主义制度下),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集体实践的产物。"(中译本,第5页;以下凡引该本处只标页码)显然,在这一判断中,"文化"包含了作为内部结构、意识形态和集体实践三个方面的意涵。更重要的是,他将集体实践的层面置于首位。这种处理,当然不是威利斯的个人创见,而是受到他身处其中的英国文化研究前辈的影响。
重新定义文化,是英国新左派学者开创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这种工作,最早由威廉斯开启。他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中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同年随后发表的《文化是日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一文,在强调文化的日常性质时,特别指出其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既是传统的又是创新的;既是日常的共同意义,又是卓越的个人意义。我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既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共同的意义,也是艺术和学问--发现和努力创造的特殊过程。"(Resource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R. Gabel eds., Verso, 1989, p.4)三年后,他在《漫长的革命》中由此引申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定义。如霍尔所言,这种定义突出了文化的人类学意义,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而威利斯将文化视为集体实践的产物,正是对威廉斯观点的直接继承。
除此之外,威利斯对文化含义第二个方面的界定,即将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手段,显然受到汤普森观点的影响。汤普森曾对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提出尖锐批评。在他看来,上述界定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忽视了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对立关系。他强调,这种对立的实质乃是意识形态冲突,充满阶级斗争和权力对抗。基于这种理解,他将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修正为"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显然,威利斯试图整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含义,将意识形态批判纳入人类学的文化理解。至于他提到的作为内在结构的文化,则是文化研究所借鉴的结构主义理论资源的直接体现。
经过上述辨析,威利斯整合前人思想的愿望显而易见。不过,《学做工》作为一部文化民族志,其立意不在理论的综合,而是现象的洞察。故而,他最初对整个工人阶级文化的兴趣,最终凝缩在工人阶级"文化形式"的层面,以此为概念中介,整合上述三种文化理论的视野。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形式被落实在一种特定形态--男性反学校文化。通过对汉默镇12名受中等教育的工人阶级子弟("家伙们")的跟踪调查,威利斯揭示出"特定的工人阶级主题和文化是如何获得世俗性的存在和节拍的"。(第256页)这里所谓的"世俗性的存在和节拍",即是反学校文化这种形式如何将工人阶级作为劳动力纳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
威利斯探究这一文化过程的贡献,并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民族志个案,而且包含着他在理论上回应已有再生产理论的巨大抱负。一方面,已有的再生产理论往往依据同样的逻辑和机制观察不同阶层的再生产过程,而并没有对此做出阶层间的区分。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布尔迪厄的《再生产》(与帕斯隆合著,1970)一书。而威利斯在该书一开始就强调这种区分的必要,他试图通过"工人阶级如何继承父业"来考察这一再生产过程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以往的再生产理论家(如阿尔都塞、鲍尔斯和金蒂斯等)将社会底层作为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只能以服从和认同的态度进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威利斯通过凸显文化的半自主性位置,强调文化形式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唯有通过文化,社会的真实结构关系才能被转换为概念化的关系,并再次折回原地。"(第225页)具体到汉默镇工人阶级子弟的个案。如果他们被动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往往能够摆脱工人阶级的命运,顺利上升为中产阶级;反而是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抗,构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悖谬性地将他们推向自我诅咒的道路,延续工人阶级的命运轨迹。进一步说,正是反抗本身赋予了这种工人阶级文化形式以独特的政治意味,使得"阶级身份在个体和群体中被传递,在个人和集体自主意识的情景中得以再现"(第3页),从而完成阶级身份的再生产。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子弟的意识形态反抗何以会落入此种自我诅咒的结局?
2. 理论与实践的分裂:男性气概与阶级意识的危机
在《学做工》的理论分析部分,威利斯将这种自我诅咒的结局,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以及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在他看来,文化因素的半自主性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相应的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塑了工人阶级对自身劳动力及劳动意义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决定了他们反抗行动的文化形式及其最终的悖谬结局。
威利斯借助"洞察"(penetration)和"局限"(limitation)两个概念来区别对待这种认识的正负两面。所谓"洞察"一面,即是工人阶级子弟对既定教学范式充满敌意,蔑视教师权威,对文凭价值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鄙视"书呆子"为此牺牲掉个人时间和人格独立。总之,他们不相信学校教育与未来工作之间存在必然的连续性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洞察并拒绝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构造,为自身解放准备了主观意识的可能。然而,这种"洞察"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转化为解放自身所需要的阶级意识,而是以极端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威利斯认为,工人阶级是以否定脑体劳动分工的方式,拒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他们固执地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才是对自身经验的独立确证。而脑力劳动(文凭和认证)在学校教育中总是以更高要求和更多强制侵占他们的私人空间,他们深信,这种劳动乃是通过教育交换和资本交换占有他们想要的自由的不平等形式。正是对脑体分工的这种否定,成为反学校文化的基本逻辑和动力,最终将工人阶级子弟推向车间,成为体力劳动者。这里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子弟何以如此迷恋体力劳动?是不是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生活的意义感?
威利斯的分析否定了这一点。按照他的民族志观察,工人阶级在体力劳动中并没有任何满足感。他们在进入车间的工作空间后,很快意识到现代劳动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并因此丧失对体力劳动的最初热情。对他们来说,具体的劳动种类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它们都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内在自我实现可言,那么工人阶级将如何在精神上克服工作的枯燥和无聊?威利斯认为,除了娱乐消遣,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体力劳动视为表现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方式。这里所说的"男性气概",无疑是该著理论分析的核心所在。作者认为,"男性气概的本质是超越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男性气概则具有一种独特风格和世俗的表达形式。"(第190页)即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出的特征:"'真正干事',身体活跃,以某种方式出卖劳动力"。(第135页)在反学校文化中,他们举止粗野,崇尚体力,暴力滋事,歧视女性和少数族裔。进入车间文化后,尽管他们学会了妥协,收心工作,吃苦耐劳,但基本态度并未改变。威利斯强调,正是这种男性气概,结构了他们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基本认识,限制了他们的文化洞见。更重要的是,男性气概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群体性态度,在战胜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之时便走向分化,转变为另一种个人主义表达,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在这种意义上,工人阶级并没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撇清干系,并因此失掉阶级独立性,以及自身解放的可能。
威利斯的洞察不止于此,他还明确意识到,在更大意义上,反学校文化的这种限度根植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基本认识:实践比理论更重要。他们相信,"实践能力才是首要的,是其他知识的基础。""理论是附属在特定生产实践之上的。理论如果不能维持其相关性,就会遭丢弃。"(第73页)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认识包含着工人阶级文化的洞见。然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认识往往被他们的经验性判断所扭曲。中产阶级文化作为这种判断的参照,往往将知识和文凭视为个人在实践中提升自我的必要途径。但在工人阶级眼中,这不过是对理论的过度依附,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践意涵。正是这一判断,让他们本能地反感并排斥理论,认为它"在社会伪装下空洞无物"。(第74页)与之相对,男性气概作为实践维度,代表着"运动、行动和断言"(第190页),成为他们选择体力劳动的观念依据。
显而易见,工人阶级文化的这种扭曲的认识,割断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理论被看成脑力劳动,遭到非理性的排斥,这使得工人阶级丧失了超越个体经验的阶级视野,无法摆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围困;另一方面,实践被简化为体力劳动,缺乏创造性内涵和道德根基,这导致他们陷入男性气概的迷思,无法识破这种劳动的剥削性质。在这种意义上,男性反学校文化作为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在实现阶级身份再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阶级意识的自觉,反而在男性气概的迷思中陷入危机。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摆脱这种男性气概的迷思,是否便可以再造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重绘工人阶级文化的未来?
3. 阶级主体的重建与工人阶级文化的未来
威利斯在《学做工》中谨守民族志的方法论,并未直接在理论层面回应这个问题。不过,他后来在该书中文版的前言中,引申出与此相关的政治问题:"在未来这些相互关联的关系循环中,这一平衡如何转变为被统治者的优势,在何种条件下对文化生产的洞察可能转化为政治意识和实践,并被动员起来中断社会再生产,而不是反过来强化它。"(第5页)
在我看来,要回应这些事关工人阶级文化之未来的问题,首先需要校准威利斯对男性气概的把握。他所理解的"男性气概"是masculinity,而非manliness。按照曼斯菲尔德在《男性气概》一书的研究,前者其实是1970年代女性主义兴盛之后开始流行的概念,往往并不包含赞赏之义。这个概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性别中立社会的诉求密切相关,是女性主义"解构"男性权力的概念表征。(参见《男性气概》,刘炜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因此,它并不是威利斯所谓的超越历史的范畴。事实上,真正具有超越历史意涵的是后者。这个词在古希腊即是勇敢(andreia),是与控制恐惧有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德性。它并不局限在身体和经验层面,而是指向更高的荣誉和尊严。(同上,第29页)由此来看,威利斯所概括的男性气概,只是人们攻击masculinity的流俗看法,并非manliness意义上的道德德性。不过,这种道德德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资产阶级追求自我保存,迷信理性控制,缺乏男性气概。
事实上,威利斯在《学做工》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注意到,"家伙们"攻击"书呆子"和"软耳朵"们顺从权威,"娘娘腔",死气沉沉。然而,在"茂宁赛德版"(1981)后记中,他明确指出,随着资本主义技术的进步,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工作将越来越少,工人阶级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内部竞争和失业恐惧。这无疑将进一步威胁和弱化工人阶级的男性气概。在后来出版的《民族志的想象力》(2000)中,他也专门论及工人阶级"男性气概的危机"(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技术性失业所带来的生活困难,使得体力劳动无法再为工人阶级提供男性气概的支撑。(参见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Polity, 2000, pp.91-97)不过,在我看来,摆脱男性气概的迷思,并不能挽救工人阶级文化的危机。从根本上说,这种危机的直接根源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腐蚀。而真正的男性气概(manliness)作为一种道德德性,正可以从观念上帮助工人阶级摆脱个人主义的狭小视界,在更高的荣誉和尊严上看待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并由此构造团结一致的阶级意识。
其次,威利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理解过分拘泥于"男性反学校文化"的思考范式。他将这种文化"视为更宽泛的工人阶级文化内部的一个变体,而工人阶级文化本身只不过是'文化形式'的一种宽松的构成方式[......]"。(第257页)由此,他将工人阶级子弟反抗的文化形式视为反省工人阶级文化的民族志视角。这样的选择样本并推演结论的方式,不难让人将反抗视为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威利斯的这种研究方式,曾被人攻击忽视了"书呆子"(循规者)以及女孩子们。对此,他在"茂宁赛德版"后记回应:对他而言,这是集中关注"家伙们"的研究需要,"书呆子"必然成为陪衬,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研究便因此不重要,只是"文化形式"有所不同。然而,马库斯(George Marcus)随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1986)一文中提出了作者无法回避的尖锐批评。马库斯并不反对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而是指责他并没有考察何以有的工人阶级子弟循规蹈矩,而另一些反叛对抗。(参见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0页)换言之,他忽视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内部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便无法简单地将反抗看作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而必须正视其现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另一方面,威利斯的这种研究方式,忽视了工人阶级文化在理论上所面临的挑战。要解释这一点,必须回到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最初定义。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威廉斯辨析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概念。一方面,他对"资产阶级文化"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充满怀疑,而倾向于认为存在"持同一种语言的人们所共享的智性和文学的传统遗产"。在这种意义上,"人为地制造一个'工人阶级文化'以对抗这种共同传统,纯属愚蠢之举。"(《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34页)这意味着,"工人阶级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必须处理与这种共同传统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他强调,如果说存在"资产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的差别,那只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必须意识到,"工人阶级文化,以其经历的阶段而言,基本上社会性的(因为它创造了机构),而非个体性的(特别是在智性或想象性作品上)。"(同上,第347,349页)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文化意味着一种新的集体性伦理生活方式的构建,其核心难题是如何处理与形态不同的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复杂的断裂和连续性关系。但在《学做工》中,威利斯通过反抗的文化形式,将工人阶级文化置于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面,并没有深思其更新和创造阶级主体的文化资源。即便这种文化可以通过反抗的形式在阶级社会中获取更新的动力,但一旦阶级对抗胜利,这种对立面便会消失,而其自身也将随之瓦解。
最后,深究起来,威利斯之所以并没有在理论上思考工人阶级文化与共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包含着社会主义理想的文化形态。在《学做工》中,他明确批评,所谓"工人阶级文化正在以某种方式实验未来"的观点,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这种观点认为,"当资本主义被推翻的时候,工人阶级文化将为人类生活提供具体的蓝图。"而在他看来,"此类设想根本不可能向人们做出承诺或兑现承诺。如果乐观地将工人阶级文化或意识视为实现理性和社会主义的先锋,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第157页)威利斯的这种悲观态度,自然与他对反学校文化悖谬后果的观察密切相关。但在更大意义上,这种态度也是社会主义实践在现实中遭遇挫折的历史效果。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名声,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暴力与混乱,令许多战后左翼知识分子倍感失望,不再对工人阶级文化寄予期待。在这种语境中,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往往陷入对悲观现实的无奈观察,而缺失了想象未来的维度。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想象未来的努力,那么所有的现实观察都可能失掉方向感,无法为工人阶级主体的重建指示未来实践的可能。
对当代中国而言,《学做工》并不仅仅是研究方式和学术观点的启示。更重要是,它作为一个观察工人阶级文化之现实的生动案例,指示并促动我们在日益固化的现实中重审这种文化的历史限度和未来可能。这种愿望,既非单纯热烈的怀旧式情绪投射,也不是无所依凭的意识形态教条,而是以工人阶级文化的变迁为线索,重构当代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想象未来中国文化图景的可能。
【书目推荐】保罗·威利斯著,秘舒等译,《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译林出版社,2013。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1期。作者简介:符鹏,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