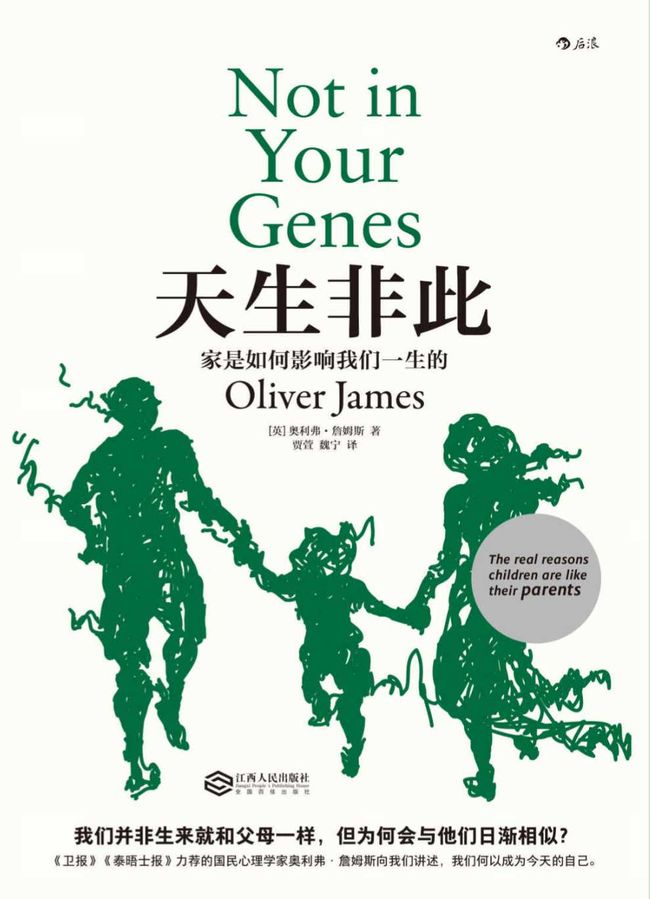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总和父母一样
相比其他物种,人类依靠父母生存的时间最长。尽管大多数哺乳动物都能在出生几周或几个月之后脱离父母独立生存,人类却需要至少5年。正因为如此,人类自出生起就一直努力迎合自己的养育者,期盼赢得他们的关爱并获得其他物质方面的满足。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可能面临死亡,不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孩子努力获取父母关注,并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无限维护。我将这种普遍趋势称为“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Offspring Stockholm Syndrome)。尽管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消极,但它不过是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一方面而已。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场银行抢劫案中,受劫持的人质对绑匪产生了同情,还认同了绑匪的许多观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由此出现并得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最理性的求生策略。绑匪一旦与人质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并将人质视作与他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类,他们撕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人质也更有可能活下来。
大多数父母为了能够让孩子得到最好的环境而竭尽所能,随时准备将自己放到次要的位置,或者至少感觉在自我需要和孩子需要之间苦苦挣扎。然而对于父母来说,年幼的孩子的确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在婴幼儿时期,孩子完全依赖他人照料,自己不会动,不会吃饭,也无法自我舒缓,这种过度的依赖也造成了他们内心的强烈不安以及对迎合父母的迫切需要。 因此,多数母亲(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有时难免会觉得这些折磨难以忍受。由于这样的压力,一半母亲在孩子一岁之前都真的幻想过自己在某些时候会杀掉孩子(事实上,可能几乎所有父母都有过类似想法,尽管只是一闪念)。
对于大多数母亲来说,一天24小时连轴转的强度实在太大,有时甚至会发展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必须有个了结”的情况。 照料过年幼儿童的人都会明白,这项工作不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让人筋疲力尽。你会睡眠不足、丧失自主,甚至会感觉自己逐渐过时,与文明社会脱节。由于当今社会过度分化,很多母亲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会感觉分裂孤立、与世隔绝,以及自己不是社会的一员。这样看来,她们普遍患上抑郁症或表现得怒气冲冲也就不足为奇了。绝望加上易怒造成的周期性情绪爆发,会让她们的情绪发展为极端痛苦或无节制的暴怒,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发展为精神崩溃。这样说来,诸如在短短一周内,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两个婴儿被照料者杀害之类的新闻,以及一岁之前的婴儿最容易被杀害这一事实就没有那么令人奇怪了。
子女变得与父母相像的主要原因就是年幼儿童对父母的全然依赖性。而这种情况对养育者精神造成的威胁,有时会导致他们伤害孩子。子女必须千方百计地赢得父母关注,同时获得生存资料以满足自身需要,否则就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对于子女来说,想要获取父母赞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完全复制他们的所作所为。
三种行为机制——言传、身教、身份认同
言传
实际上,父母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教育子女什么是“正确”的言行方式。最初,养育者掌控着婴幼儿的一切事宜。当儿童到了懂事的年龄,父母就会教导他们吃喝拉撒睡的正确方式和正确时间,同时教育他们应该如何回应成年人。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父母会对他们的某些言行大加鼓励,而对其他言行大加抵制。孩子们学会了如何取悦父母,如何避免令父母失望,并学会对父母的话全然照办。
最终结果就是,为了获得父母的赞许,他们会对这些品质十分重视(同时也满怀希望,因为他们能够乐在其中)。同样地,有时我和妻子都会表现得十分争强好胜,我们尽管没有特意教孩子这样做,却会在不经意间将这种习惯教给他们。孩子们性格的养成,不论积极还是消极的一面,都会受到父母教育的直接影响,包括良好的日常习惯、组织性思维方式、知足常乐的心态,以及那些不良的习惯和态度。
身教
不同于父母的主动教导,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认真学习父母的行为,并对其进行一丝不苟的模仿。他们也会模仿父母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行为模式,包括守时、好斗及消极情绪。
有时孩子们甚至会完全复制父母的某些行为,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基因造成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孩子们近距离观察父母的个人风格、性格特征及行为模式。
身体认同
如果说身教是一种模仿,那么身份认同就是孩子通过代入父母的角色来体验他们的某些方面。孩子将父母的言行代入自身,并将其当作自己本身的一面。 身份认同产生的根源是爱意或恐惧。如果出自对父母的爱意,孩子会通过模仿父母来取悦他们,或者避免不同给他们带来的不快,这种爱的传递会令我们陷入迷失自我的危险中。
而如果子女对父母的身份认同是为了逃避糟糕的情况,例如训斥、惩罚甚至是体罚,那么与施虐者的身份认同就是一种抚慰他们的方式。这相当于告诉他们,“不要再伤害我了,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啊。”在这种情况下,施虐者伤害他们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虐待是父母子女拥有相似之处的一大成因
除了这三种学习机制(言传、身教、身份认同),虐待是子女同父母相似的最大成因。这是因为,虐待会开启绝望而强制的机制,进而造成人们重蹈覆辙。 我们长大后,很快就会察觉出父母的言传身教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因此自主选择是否停止。想要摆脱与父母的身份认同当然要难一些,因为这早已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然而,最困难的却是克服幼年时遭受虐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简言之,父母的消极情绪会通过虐待传递给子女。如果我本人悲观抑郁,那我就可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孩子。如果你的父母通过某种特别方式让你感到难过,那么这种情绪可能仅仅是对他们的悲观情绪的一种复制。
而让他们感到悲观失望原因很可能是一致的。如果父母因为自己肥胖或智力不足而沮丧,他们就会通过一种高压教学的形式,将这种观念植根于子女的脑海中——“你很胖,你很笨”。他们也可能通过某种行为将这种思想灌输给孩子,比如在众人面前对孩子进行羞辱。“我很好,”这些父母们事后感叹道,“而你不是。”
虐待的形式包括精神虐待(例如受到不当处罚、被粗暴对待、看到其他兄弟姐妹更受父母喜爱)、对精神或身体忽视,以及身体虐待、体罚或性虐待等。如果我们曾遭受虐待,就会产生严重的悲观情绪,而这会决定我们感受整个世界的方式。它们会顽固地留在我们身体内部,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因为孩子们对抗这种悲观情绪的方式就是将这种情绪在与其他人的相处中进行重演,包括幼年时与兄弟姐妹和其他同龄人相处,以及长大后与恋人、同事或是朋友相处。 举例来说,一个女孩会从父母双方接收大量负面情绪。父亲在饭桌上反复申述自己在她这个年纪比她聪明太多,而母亲则会不断挑剔说她实在太胖了。
实际上,这反而会让她吃得更多,变得更重。这也导致女孩对自己抱有极度消极的看法,认为其他人也不喜欢自己,觉得自己又胖又蠢。不论是年幼时还是长大后,她都会选择与那些骂她胖、不把她当回事的人交朋友,并以此来继续这种虐待。尽管这样的情况会让她难过,但这是她最熟悉的方式,反倒比那些和善的对待更让她感到舒服自在。尽管如此,她也保留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这次,这个新的朋友会让事情变得不同。 研究表明,这种情感虐待是最具毁灭性的虐待。如果我坚持告诉我的孩子他们很蠢、很丑或是很糟糕,他们的内心就会觉得不满和受到伤害。如果我对一个孩子更偏心,对其他孩子来说,伤害也是很深、很难被治愈的。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事实上,所有父母都会在无意中对子女进行或多或少的虐待,而大多数人或许完全不曾意识到自己有过这种行为。实际上,所有人际关系中都能发现虐待的影子,包括同事和朋友之间。然而,如果这种反复极端的虐待来自父母,那么它造成的伤害就会尤为强烈,这是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和双方力量悬殊造成的。 对于这种将自己厌恶的消极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的现象,我把它称为“我很好,而你不是”机制。如果我感到愤怒或悲伤,那么通过激发他人情绪,我可能使自己得以解脱。我们每天都会将彼此当作自我厌恶情绪的垃圾桶。 如果这种事件不常发生或者是十分微小、转瞬即逝的,那么它就不会造成任何长久伤害。因此,你在工作情绪不佳时,就可能会发邮件给同事,催他们交齐早该上交的文件。你自认为这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然而在潜意识中,你选择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向他们施压,内心深处也明白自己是在找麻烦。因为这会加大他们的压力,你通过将这种负面情绪发泄到他们身上来减少自己的负面情绪。在潜意识中,你明白当他们看到邮件时,一定会诅咒一句,会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额外压力而感到焦虑。你明白他们打开文件后,会心跳加快、血压上升、眉头紧皱,而这会让你在按下发送键的那刻觉得有一些舒缓。你的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一丝放松,还能够使自己在消极的情绪中得到一丝小小的暂时解脱。
这种“我很好,而你不是”的情绪之所以能够完美隐藏,是因为它早已成为我们内部情绪的固有组成部分。我们对它太过熟悉,就像我们熟悉厨房里的水池一样,因此难以注意到它的存在。与之相反的是,一些更为明显的虐待却会让人更容易牢牢记住并识别出来,例如身体虐待和性虐待。
虐待就如同房间里的光或是空气,我们对它们的存在太过习惯,认为它们太过理所当然,因此很难发现。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我要不断地帮助患者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实:他们确实受过父母的虐待,那些经历真的就是那么痛苦,几乎每个患者都是如此。他们就像那些惊弓之鸟,极不情愿面对父母曾经无情甚至残忍地对待过自己这一事实。在同心理医生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的温暖和支持给了他们一种不同体验,让他们在疗程结束后,能够同家人、朋友和同事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 长大后,受虐儿童通常会变得酷似自己的施虐者。这一点在遭受生理虐待或性虐待的极端事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大部分施虐者都曾遭受过相同的虐待。由于受到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影响,我们所有人都会为父母辩护,极不情愿批判他们的所作所为。曾经那个脆弱的孩子还住在我们内心深处,害怕自己的反抗会招致恶果。受虐儿童在为父母辩护时不遗余力,这一事实简直让人震惊。
精神疾病的最新观点认为,上述现象的主要成因在于虐待而非基因。由临床心理学家约翰·里德建立的创伤后遗症模型(Traumagenic Model)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种模型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疾病,不如说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者说就是这种症状。人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做出了严格界定:脱离人类控制,大脑突然迸发入侵式的想法或记忆,有时甚至包括幻觉;对亲密关系和困难问题进行逃避;无缘无故的消极情绪和想法;突发或轻易被激怒、反应过激及过度敏感等。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通常都试图通过毒品和酒精来控制这种不快的状态。在许多精神“疾病”中都能够发现这一系列发病症状。
最新研究表明,并非某种特定形式的虐待会导致某种特别的精神疾病。事实上,所有受虐待的儿童都会同时遭受多种精神疾病的折磨:焦虑症、抑郁症、情绪失调及妄想症。长大成人后,他们比那些在童年时期更少遭受虐待的同龄人更容易产生情绪悲观。
那些认为某些精神疾病是孤立存在的,与其他疾病没有任何重合的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种全新的模式被称为“创伤后遗症”(Traumagenic),这是由于几乎所有成年人消极情绪的爆发都是过去的创伤造成的。父母的影响导致这些受害者随时准备好了遭受这种威胁。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都可能激发他们不正常的过激反应。
极端的情况包括:强奸受害者如果突然回想起遭受袭击的细节,会觉得自己突然又回到了当时的卧室或是后巷,而强奸犯正在侵犯他们。一些微小的细节,例如一个名字或是一种声音都会触发他们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突然闪现的回忆就如同现实一般,当创伤的“视频片段”开始播放,事情就如同在真正重演一样。就像我们会感觉梦境同现实一样真实,那些受害者重历创伤的感觉也是一样。
这种“经验性视频”同幻听和幻视不同。很显然,很多精神病人的幻觉都不过是回忆的不同版本——例如听到童年时听到过的告诉受害者他们是坏人的声音,或是看到当时真正的施虐者出现在屋子另一边。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可能会重新解读这些经历,最终使其变得完全不同。 因此,当在某些经历中我们显得十分弱势时,我们会将自己幻想为一个力量强大无比的人,一个更安全的人,比如上帝。这就是妄想症的真正成因:妄想症并非物理性的故障,也不是基因缺陷造成的大脑缺陷。但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神病学专家一直坚持相信这种错误理论。
如果孩子受到父母的诱骗,并将这种经历视作正常,那么当他们长大后,意识到这实际上不正常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抑制这些回忆。因此,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时会乐在其中,甚至还能体验到一些性兴奋。这种虐待可能是他们能够体会父母关爱的唯一途径。关于这种禁忌的秘密,他们拥有矛盾的感情,这也使他们在长大后回想起这些记忆时感到更加痛苦。这种记忆与秘密会以幻觉和妄想的形式迸发出来,而幻觉的内容基于原始创伤。因循守旧的医生或是基因学家对患者的想法不屑一顾,认为那纯属大脑功能失调的产物。事实上,这些妄想和幻觉包含的内容意义十分重大。
多数情况下,这些经历都是痛苦的。不论是极端的情况——例如强暴,还是不那么极端的——例如呵斥和挨揍,都会演变为一种模式,并在现在不时迸发。所有精神疾病的核心都是过去的事件在现今重演,不论是表现为患者误认为过去真实的痛苦经历发生在现在,还是扭曲记忆中的某个方面。
这些当然只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然而在某些时刻、方面,我们所有人都曾是受害者,无人能幸免。最关键的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兄弟姐妹和我们受到的虐待和关爱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导致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怪癖。
到底该如何做?三条建议
一、你和父母到底有多相像?原因是什么?
找出与父母相似之处
二、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找一位心理医生,请他帮助你深入分析自己的童年,让你获得全然不同的体验
受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影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想要相信“如同父母爱我们一样,他们也会虐待我们”这一事实其实艰难无比。几乎所有人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通常只需要简单的治疗就完全足够。许多其他的短期心理治疗也能够挖掘过去经历对你的影响,而且通过与心理医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你产生全新的体验。心理治疗同时会提供实用技巧或教学手段来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瑜伽和冥想能够帮助你在平日里保持心情平静。还有一些疗法是我本身就十分了解而且认为十分有效的,包括交互分析疗法(Transactional Analysis)、超个体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以及霍夫曼疗法(Hoffman Process,对抑郁症非常有效)。当然,还有很多疗法的变体,我不会不懂装懂地告诉你我全都了解。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与心理医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做好准备揭开问题产生的童年根源。
其中最本质的问题是,与心理医生建立的关系与童年痛苦的遭遇完全不同,它能为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体验。父母在你心里留下的恶劣印象会被现实中心理医生建立的良好形象所取代。运用图表或构想自己不同行为的技巧,能够通过思维来改变感觉,从而在解决问题中发挥辅助作用。
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认为思维能够控制感情,转变思想就能转变感情。这种疗法宣称,在短短6~16个疗程中,就能够将抑郁症或焦虑症彻底治愈。医生会告诉你停止说自己很胖、很丑或很笨,即使事实如此。如果你一直无缘无故感到焦虑,担心厄运的降临或害怕自己出丑,认知行为疗法会教你反向思考。
接受认知行为治疗并明显“康复”的抑郁症患者中,有2/3会在两年内复发或寻求进一步帮助。治疗结束后,一般的患者仍受抑郁症困扰(大约30%的患者根本没有完成整个疗程)。事实上,如果不接受治疗,大多数抑郁症或焦虑症患者的病情也是时好时坏。两年过去后,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患者的精神健康状态并不比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更好。
精神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虐待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有十分有力的证据。这样说来,认知行为疗法明确要求医生将患者从自身童年经历中剥离开的做法就显得十分诡异。这一疗法忽视病因,却强调集中关注思想如何对症状产生作用。
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有效疗法或是比其他疗法更加科学,反倒是心理动力学疗法被证明拥有长期疗效。
焦虑症的某些症状,例如恐慌或疑似强迫症,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得到长期改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光芒褪去,消极情绪又会卷土重来。然而,因为克拉克和莱亚德的 “功劳”,无论是在公共医疗体系或是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认知行为疗法都是现今最为常见或者说唯一的疗法。
然而认知行为疗法确实有其优势所在,同时对一些其他疗法也起到了启发作用。它鼓励采用实际手段,而这些手段也确实能够提高人类健康,例如体育锻炼、冥想以及瑜伽。 克拉克教授本身就是一个医术高超的临床心理医生,我也知道一些人声称认知行为治疗确实减缓了他们的抑郁症。但事实上,他们所有人都接受了多年的治疗,实际起作用的是他们同心理医生的关系,而非思维模式的转换。这一点也早已被研究证明:目前为止,只有在医生和病人建立了良好关系的情况下,认知行为疗法才真正有效。然而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认知行为疗法很不完善,也不鼓励医患之间建立情感联系。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可负担的疗法。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急需适合所有人的可行疗法,而非仅仅是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其他选择的人——也就是那些通过与医生建立良好关系,并深入探索童年经历来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以及其他所有精神疾病)的疗法。
三、将“我很好,而你不是”的心理转换为“我很好,你也很好”的心理
在与家人、朋友及同事交往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有运用“我很好,而你不是”的心理来摆脱坏情绪的时候。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同样对待。
如果没有好友、亲人或心理医生的帮助,我们通常很难发现自己犯了这种错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替朋友或家人做决定或是处理棘手问题时,人们往往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观点。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当时的行为,深入分析事情是如何发展的。
如果你将这些问题与你童年的经历进行对比并思考,可能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十分惊人。或许对在餐桌上吃饭这件事,你的父母表现得十分严苛或十分宽松,而伴侣态度冷淡和同事奸诈狡猾的问题也是如此。当然了,可能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确是错的,而你是正确的。然而,问题通常不会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