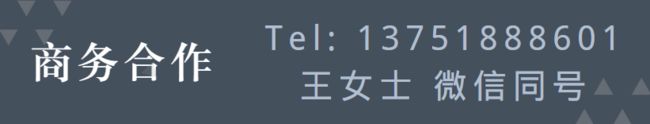00后艺考少女:为梦想耗尽父母钱包,妹妹以为我当明星
 图:视觉中国
图:视觉中国
“ 眼前就两条路,艺术的道路是彩色的, 特别好看,然后医科是黑白的”。
文 |未金梦王超 编辑 | 盛倩玉
17岁的麦合丽娅想象不到自己不学表演的生活,对她来说,不搞艺术的生活是黑白的。而大她两岁的一航,中专毕业后,复读也要参加艺考。
据统计,2020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115万,他们都是其中一员。校园难觅他们的身影,高中生活一半时间都奔波在外。
2019年,高考人数突破千万,艺考人数也水涨船高,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计划573人,总报名67946人,一百余人中,只有一个能够圆梦中戏。
“艺术道路是彩色的,特别好看,医科是黑白的”
21世纪初,印度电影在新疆风靡一时,影星沙鲁克·汗成为不少人的“男神”,维族少女麦合丽娅也不例外。
小学时,麦合丽娅在姥姥家和表哥表姐们一起看印度电影,之后回家对着镜子偷偷模仿演员的表情动作。年幼的麦合丽娅并不知道电影工业的真实图景,以为那就是现实的人生,“感觉他们好幸福,这样真好”。
知道有表演专业后,麦合丽娅也想“尝试不同的人生”。中考填报志愿前,麦合丽娅和父母商量自己的未来,提出想去一所高中的艺术班,但身边家人朋友都反对。
仔细思考大家的反对理由,麦合丽娅觉得有道理,演员生活不稳定,有时候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麦合丽娅舍不得家里人,最后乖乖上了普通高中。
关于未来,父母对她的规划是希望她读医科,但麦合丽娅对此并不期待,“我当时眼前就两条路,一个是艺术,一个是医科,艺术的道路是一个彩色的,特别好看,然后医科是黑白的”。
麦合丽娅的演员梦其实并没有真正熄灭过。她与在艺术班上课的旧友一直保持联系,也时常能在朋友圈刷到艺考生朋友发的视频,画面里她们排小品、练歌、练台词,麦合丽娅十分憧憬。
艺术生排练小品(受访者供图)
麦合丽娅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就是每天都搞艺术。”
在外界看来,学艺术可能是“成绩不好”的学生选择的“退路”,或者“有钱有颜”的学生选择的“捷径”。但真正走上这条路的男孩女孩们才知道,对于他们而言,学艺术是“唯一彩色的路。”
19岁的一航来自福建泉州的一个离异家庭。几年前,一航还是初中生,当时他在B站上看到了《芝加哥》和《魔法坏女巫》的音乐剧。那时候,他还不懂音乐剧要表达的内涵,甚至觉得演员“穿得暴露”,但是“真的太帅了”。
高中时,一航考上一所中专,学的是电商专业,但他对此不感兴趣,反而对音乐比较上心,经常跟着隔壁幼教的老师学习唱歌跳舞。
一年前,一航中专毕业,他决定复读,并开始正式的艺术学习。对于一航来说,学音乐“意味着我可以与我喜欢的捆绑”,让音乐剧融入他的生活,是一件想想就开心的事。
为5万元学费,停了11岁妹妹唯一的补习班
艺术学习的费用往往比普通学习高出不少。 不同艺术专业花费不同,一年的花费普遍在五万到二十万不等,包括培训机构的学费、在外生活费、器材费和文化课补习费。
一航为了学艺术,已经不清楚自己花了多少钱,“以十万为单位,几十万就不知道了”。
在声乐课上学习(受访者供图)
麦合丽娅曾偷偷联系过培训机构的老师,想先问清楚学费。五万元的费用,是她们家近半年的收入。
麦合丽娅的父母都是克拉玛依的石油工人,两人工资加起来一万块左右,要供养姐妹三个,上次超过五万的花费还是家里装修房子。
一边是梦想,一边是家人,麦合丽娅陷入为难。麦合丽娅决定先征求母亲的意见。
听到女儿大学想学表演,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干啥?学艺术能干啥?”母亲其实也知道女儿喜欢表演,这一次聊天结束后,母亲虽然比较犹豫,但还是同意了麦合丽娅的请求。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母亲突然“变卦”了,她和麦合丽娅说学艺术可能还是“不太好”,这让女孩的心提了起来。
“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自己想支持我,还是不支持我”,麦合丽娅无奈地说。
最后还是培训机构老师起了作用,老师向母亲表达了麦合丽娅的渴望,母亲想到,自己年轻时因家庭条件有限而未能实现的教师梦,跟女儿说:“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环境,你还是去做你喜欢的吧,没事。”
后来母女二人结成同盟,一齐“攻克”父亲。晚上父亲看电视的时候,母亲提了一嘴麦合丽娅想学表演的事,观察父亲的反应,没想到父亲毫无反应,仿佛没有听到,专心致志看着电视屏幕。再提时,父亲表示了坚决反对。
后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住在隔壁卧室的麦合丽娅,会听到母亲的劝说声和父亲犹豫的话语。
磨了近20天,父亲终于点头了。从克拉玛依开五个小时车,父母送麦合丽娅到乌鲁木齐的培训机构,签合同、交学费。付学费时,麦合丽娅感觉心疼,甚至“不敢在场”,她借口要和老师去参观学校宿舍躲开了。
多了这么一大笔花费,家里只能节俭再节俭,还停掉了11岁妹妹唯一的补习班。
幸而妹妹成绩好,对此也不甚在意,反而和更小的妹妹一起自豪:“我姐要当明星了!”她还把姐姐演出的视频发到朋友圈。每到这时候,课间都有同学问:“你姐姐是演员吗?”“你姐姐是明星吗?”
中午回来,妹妹会跟麦合丽娅骄傲地说:刚刚谁谁谁找我,跟我要姐姐签名!
麦合丽娅无奈地解释道:“我现在还是个新生。”
但小孩子并不明白其中的区别,只觉得姐姐是个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这个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
很多维吾尔族人说话不分前后鼻音,所以如何将普通话说标准是麦合丽娅面临的一大难题。 麦合丽娅 开始每天读稿件、读新闻学习普通话,看电视的时候,演员说一句,她跟着学一句。
有时和别人聊着天,麦合丽娅也会突然停下来问人家,“这个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
不过对麦合丽娅来说,最难忘的还是“撕腿”。每个上过形体课的艺术生都躲不开一个叫“撕腿”的项目:被“撕腿”的同学躺在形体教室的地上,几个老师同学围着,三位同学制住她的腿和双臂,老师将她的一条腿无限压向头顶。
在形体课上“撕腿” (受访者供图)
麦合丽娅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感觉比生孩子还疼。”
即使之后站起来,“撕腿”的痛感还萦绕在大腿肌肉上。上完课,麦合丽娅看着同学们,觉得他们走路都有些不正常。
撕腿那天,麦合丽娅痛到无法走路,去厕所都需要同学帮忙,进了厕所也不敢蹲。这天,她给父母打了第一通诉苦电话。此前,她打给父母的电话,除了讲讲日常生活就是传达老师对她的夸奖,她不想让父母担心。但这次,麦合丽娅在电话里止不住哭泣。
一直哭到晚上回宿舍,形体衣和鞋子都没换,麦合丽娅直接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出早功,麦合丽娅依旧痛到无法换运动服。她想打电话请假,谁料隔壁编导班的女老师直接“杀”到寝室,递给她一个正在通话的手机。
电话那头,是她的辅导老师丁老师的声音:“要么你立刻下来,要么你转到编导班去。”最后,麦合丽娅还是边哭边换好衣服,拖着疼痛的双腿,一步步下楼。
出晨功(受访者供图)
艺考这场战役,只有足够优秀才能在成千上万人中脱颖而出。
一航主修的是音乐剧,表演专业的考试他也会报名。所以他的主要训练项目就是唱和跳。舞蹈课上,老师会给学生安排学习内容,要求学生私下学会,然后在课堂上进一步“抠动作”。
同学们在老师面前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老师像考官一样坐在他们前面,大多只需口头指点。但到了一航,老师得站起来亲自给他示范。
老师一点点教他,有时一航做到一半就僵在那里,一脸疑惑地看着老师。
回到宿舍,冲个热水澡是让他感到最轻松的事儿。站在莲蓬头下,闭着眼睛接受热水的冲刷,一航会幻想自己站在瀑布之下。
离家的孩子,19岁做得一桌“硬菜”
每次谈到家人、家庭,麦合丽娅都会变得感性。 她经常想念一家人在黄昏的阳光里看电视的场景。
有时爸爸不在,家里的四个女性会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综艺,一天吃甜的,一天吃辣的。每次假期结束回到培训机构,麦合心里都是不舍,想玩手机转移注意力,却又刷到家人的照片。她更想家了。
每到这时候,麦合丽娅都想抓住一缕客厅里落日的光线,但却抓不住。她无法留住时间,只能自己慢慢克服。
以前她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在爸妈身边,直到考上大学,“没想到选择了这个专业,高二就出去了,离开了爸妈,就感觉剪短了这段时间。”
她用了“剪”这个动词,感慨在家的时间“就这样戛然而止。”
图:视觉中国
一航父母离异,初中时,他和父亲吵架,就出来独自生活。六七年前,外卖软件并不像现在这样盛行,十三四岁的一航自己住在母亲为他租的小公寓里,自己做饭自己吃,练就了不少独立生活的“技能”。
今年一月中旬,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校考,考试后一航回到北京继续上课,随后疫情爆发,一航没有回家,索性留在宿舍继续学习。
除夕夜,一航和一个一起留在北京学习的武汉同学约好,他们在生鲜超市买了菜,一航做好一桌年夜饭,都是硬菜,可乐鸡翅、红烧肉、炒青菜、清蒸鱼,还有一道闽南的特色焖黑鸡。
室友洗了碗之后,两人看了会儿电视剧,还没撑到十二点,一航就睡着了。
迎来大考,甜甜苦苦的日子都会过去 今年四月,各大艺术院校下达通知,很多学校都把校考改为线上,麦合丽娅和一航报考的学校也在其中。 今年,大多学校使用小艺帮APP进行线上考试,三个小时以内需要完成所有考试科目并上传视频。
图:视觉中国
年前两人已参加过几个学校的校考,乍一听说考试形式变了,都有些惊讶。不过经过几天的缓冲期,两人都开始积极准备线上考试。
考试当天,一航找来一个学摄影的女生朋友帮忙,带着提前买的打光灯和服装去到本市的一个形体教室录制视频。教室是借来的,环境不错,有钢琴,也算有了可供开声的场地和设备。
到了教室,朋友帮他画了个简单的淡妆,他对着风口吹脸,为了让妆面更自然些。之后便是撕胯拉伸和弹钢琴开嗓等一系列热身。这一套准备工作,大约要花两个小时。而朋友就在旁边静静玩手机,等拍摄时再来帮忙。
一航要先进行几次模拟考试,然后再正式开始,三次正式录制后,他会选取状态最好的一次进行提交。他觉得,拍视频的方式“会比校考来的要紧张”,有时候还会“说秃噜嘴”。那天,一航在形体教室从下午三点多一直考到晚上十点。
和一航一样,麦合丽娅也在借来的形体教室考试,和同市的一位同机构考生搭档,互相录视频、找角度和光线,期间还差点因唱歌声音太大被别人驱赶。
三个小时的考试里,她们唱歌时就跑到一楼的教室,考其他科目时再爬上四楼。麦合丽娅说,“线上考试比现场校考还累。”因为她去一趟形体教室就要考三四所学校,考到最后都不记得考的哪所学校了。
而且不去现场,她看不到考官的反应,也无法估计自己的成绩水平,心里更没底。
不过,这些甜甜苦苦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麦合丽娅和一航都在补习文化课,等待艺考成绩的陆续公布。
(受访者均为化名)
来源|南都周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