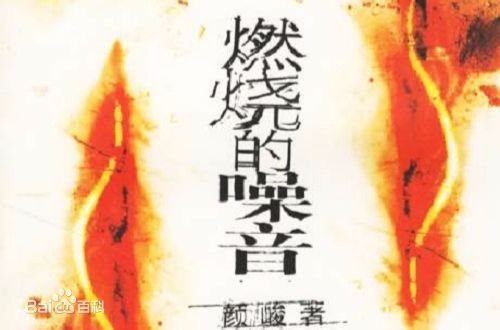1
先说一下我吧。
在颜峻的乐评集《燃烧的噪音》的第211页,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蹲在空空的小村巷子边的方脑壳,那个方脑壳就是我,一个暂住在北京西北角一个名叫“树村”的小村子的摇滚青年。
故事的開始發生在2000年前後的首都,中國新搖滾的“地下時代”,,,
還處在地下時代的樂隊們有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名字,“地獄香皂”,“痛苦的信仰”,“夜叉”,“木馬”,“藥用植物研究所”,“廢墟”,“木推瓜”,“舌頭”,“暗夜公爵”,“聲音碎片”等等等等…… ……
這些當時只在北京地下搖滾圈知名的樂隊,如今或者正在火遍全國各地的音樂節上大出風頭,或者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
不好意思,我做的樂隊雖然在上面那堆名字裏面先後占了兩大兩個席位,卻都屬於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的後者。
這兩個樂隊名字是“藥用植物研究所”和“暗夜公爵”,我在這兩個樂隊裏面的職務分別是“主唱”和“人聲”,我知道你能明白這中間的區別。。。
2
我的那兩個樂隊現在只有不多的N個人知道或者記得的原因是:
老子突然得了肺穿孔氣胸病,只好,留在蜀都養病而不是像我真心誠意希望也像顔峻希望的那樣,繼續去燕京的西北角的那個名字叫做樹村的有嘿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搖滾青年的小村子
混。
當然,在我生病的時候,這個叫做樹村的小村子已經被拆掉了,被同時拆掉的還有我和我那個把樹村變成一個莫高窟以便讓政府和開發商捨不得下手的幼稚夢想以及我在這個幼稚夢想推動下
畫的那一副在我自己看起來好看得不得下臺的壁畫。
看過周雲蓬的那本名字叫做《春天責備》的詩文集的朋友現在可以開始微笑了,老周在書裡提到的那個在麗江束河因為稱自己是將軍而被一個因為他家老漢兒是個所謂將軍而拽得不得下臺的家伙限時離開束河的那個不知道名字的老周的朋友,就是區區在下鄙人我:曹草,又叫曹無聲,網名和QQ名“查無此狼”。
我之所以要稱自己是將軍,是因為我那次去束河耍的時候,除了和老周朝夕相處,還在向不多的幾個朋友們散發我在家裡用我的上一個號稱“堅如盤石”的華碩筆記本電腦做的歌曲小樣DEMO,在小樣的封面上,我把我的音樂風格稱之為“黑色殺人民謠”。那时候很流行玩“杀人游戏”,而在所有那些殺人的人裏面,“恐怖分子”,“殺手”,“土匪”“士兵”,“警察(又被稱為“條子”)等等身份都不太合我的胃口,
我喜歡“將軍”這個稱號是因為我曾經很有好喜歡下象棋,喜歡享受由自己喊出“將軍”的那一刻:)
3
现在的我已经很久不下棋了。只是有时候会在我自己码的小说里头下一两把。无他,弈,小术耳。
在替天码道的事业面前,花一抹多功夫去弈道高手面前找虐,不是一件合算的生意。
就像现在已经没得啥子人还耍老古董的“杀人游戏”了,大家都在手机上玩时髦的“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4
我在樹村混的時候,嘿有好佩服冉土匪云飞老師,那是因為在我所創作演唱過的N多首歌曲裏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是根據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名詩《不但嘿有好沉重而且飛雞巴嚴重的時刻
(看情況簡稱《沉重的時刻》或者《嚴重的時刻》)》的歌曲,而我們的土匪老師冉雲飛先生正好就出版得有一本叫做《尖銳的秋天》的書,書裡頭說的就是這個寫了一首名字叫做
《不但嘿有好沉重而且飛雞巴嚴重的時刻(看情況簡稱《沉重的時刻》或者《嚴重的時刻》)》的歌詞的的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故事。
我對冉老師的這本書喜歡到了興致勃勃看完一遍就趕緊找個角落藏起來生害怕放在書架上哪個朋友來耍看到了要借去看的地步。
是的朋友,我和你一樣,自己屋裡頭多多少少有幾架書,但貌似我們的書都比不上冉老師的多。
在冉老師的另一本關於詩歌的著作《像唐詩一樣生活》初版上架的那段日子里,我終於決定只是來回來去在很多書店路過《像唐詩一樣生活》都只瞟它一眼而絕不拿來翻看,你知道是因爲啥子嗎?
我暫時先不解釋,因為我接下來要講的是我第一次在書店外面看見冉老師的這本書的情況:
那是在一個成都常見的看不見太陽的大白天的中午前後一點點的時間,
我從雙流跑成都市裡頭切耍,
在新南門車站外面那條河的北岸,沿著河邊有一抹多茶館。不過我並沒有急著去喝茶,而是背著書包先切那附近的一個賣D版書的書店,花僅僅10圓錢就買了一本正版定價要2大27.00塊錢的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
然後又到那附近的一個工藝品店,花僅僅5員錢就買了一串後來我去香山周雲蓬家裡頭切耍的時候發現他手上也帶著一串一模一樣的卻買成好幾十塊錢的綠檀木佛珠。
我買鄉音買到的這串寶貝佛珠後來遭我一次去陶然亭公園裏面那面湖邊邊上的“山鷹”組合開的錄音棚去耍當然既然到了這裡就必須再走一摩多路到石評梅女士和高君宇先生的墓前去獻點點子花花草草啥的然後坐下來和他們兩口子擺一會兒鬼龍門陣然後再走一抹多路到一個我現在搞忘了叫啥子名字的小廟子門口那顆大槐樹下舒活一下筋骨,我在舒活筋骨的時候不小心嗖的一聲我的這串我去香山周雲蓬家裡頭切耍的時候發現他手上也帶著一串一模一樣的寶貝綠檀木佛珠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鈴兒響叮噹當然不可不戒戒律森嚴言而有信之勢以略低於小李探花的飛刀刀速的速度離開了我的手腕不曉得跑到哪個地方切和我耍捉迷藏遊戲去了它藏得可真好,直到親愛的讀者您也就是此時正在電腦屏幕前讀這些我要拿來吸引你娛樂你并順便掙一點點花差花差的文字的時候,我都還沒有找到它而此時也就是我正在我的寶貝名字叫小黑的筆記本電腦前碼這些我要拿來吸引你娛樂你并順便掙一點點花差花差的文字的時候原來,嗨!抱歉,我已經跑得離題太遠了:)
回過頭來講故事:
在那個成都常見的看不見太陽的大白天的中午前後一點點的時間,我從雙流跑成都市裡頭切耍,在新南門車站外面那條河的北岸,沿著河邊有一抹多茶館。不過我並沒有急著去喝茶,而是背著書包先切那附近的一個賣D版書的書店,花僅僅10圓錢就買了一本正版定價要二大二十七塊錢的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然後又到那附近的一個工藝品店,花僅僅5塊錢就買了一串寶貝綠檀木佛珠,然後沿河邊的一抹多茶館慢慢走,然後就看見有個人手裡拿著一本冉土匪雲飛先生的新作《像唐詩一樣生活》坐在那裡入神的閱讀,我就在附近坐了下來要了一杯茶想要看一看冉土匪雲飛先生的這本到底能有多吸引人,還有,我也想看看這麼入神地閱讀著冉土匪雲飛先生的新作《像唐詩一樣生活》的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
現在可以交代一哈我在剛才留下的那個懸念了,我爲啥子不敢買這本書呢?
我就是怕老子也會像這個傢伙一樣也這麼喜歡得一塌糊塗,卻破壞了我藏在我屋裡角落里的那本《尖銳的秋天》和我之間的心電感應——我不買新的,它在角落里就不會抱怨我,罵我是一個TMD喜新厭舊之徒——因為它是一本我爲了把《不但嘿有好沉重而且飛雞巴嚴重的時刻(看情況簡稱《沉重的時刻》或者《嚴重的時刻》)》這首歌唱得更好而專門從孔夫子舊書網網購的寶貝二手書。
而且老子還確實是心裡頭有那麼一點點討厭唐詩,就算它們是詩仙詩聖之流寫的都有那麼一點點抵觸情緒,因為我小時候我老漢兒老是估到起我和我兄弟坐牢一樣無比鬱悶一樣的關在屋裡頭背唐詩,而不是像周圍團轉的老彝胞娃娃些一樣歡天喜地地和夥伴們一起做遊戲。
我家老漢兒是現在叫彭州當時還叫彭縣的那個我其實沒得啥子印象的地方的蒙陽鎮三邑鄉南培村人,我對彭縣的印象僅限於蒙陽鎮的極少數極少數幾個地方和南培村的我爸爸的家的周圍幾戶鄰居。爸爸據他自己說是1936年出生的,從7歲開始就給人家吆牛車。我媽媽對爸爸的這個出生年份表示了嘿深嘿深的懷疑,因為解放了讀翻身書的時候,大家伙兒怕讀不到書,都使勁把自己家娃娃的年齡報得比實際更小。
我媽媽則是榮縣五保區和龍潭區交界線上牛尾鄉中心村zou家灣人。聽我講故事的你要問了,這個zou到底是周還是鄒呢?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是寫法是撮箕匟土口的“墏墏周”,而不是另外一個寫法的“包耳鄒”。
我父母家鄉相隔那麼遠卻終於走到一起的原因,聰明的讀者您已經猜到了,那就是:他們都是到我剛才說過的那個周圍團轉都是老彝胞的山村支邊的支援涼山建設的共和國第一代新青年。
我父母當時的職業是劉慈欣已經被購買了電影拍攝權的那篇優秀得不得下臺的短篇科幻小說的名字:《山村教師》。
非常巧合的是,我母親和這篇已經被購買了電影拍攝權的優秀得不得下臺的短篇科幻小說的作者是家門,也就是說,我母親也姓劉!
子曾經曰過: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5
現在我這個“當如孫仲謀”就坐在新南門車站外面那條河的北岸,沿著河邊的一抹多茶館中的一個的座位上,要了一杯茶,中遠距離觀察我發現的那位正聚精會神閱讀冉土匪雲飛先生的新出版作品《像唐詩一樣生活》的人,想要知曉他到底是哪位朋友。
那位正聚精會神閱讀冉土匪雲飛先生的新出版作品《像唐詩一樣生活》的朋友一動不動,所以我只能動動了,
我端起我的茶杯,走到這位朋友對面的空位上坐下來。
這位朋友放下了書,嗨,我道是誰,原來是范美忠范老師。
我認識范老師,范老師卻還不認識我,自然我就自我介紹一個先,然後開始擺龍門陣。
范老師曉得我是搞音樂的之後,首先問我對羅大佑的看法,我說羅是用音樂來作為表達手段的文人而不只是音樂家,因為在樹村混過的我,對音樂家的理解就是不停的排練和不停的演出,而貌似羅大佑的現場演出實在是太少太少而關在屋裡頭做專輯的時候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這在以現場為樂卻沒有出過專輯的我看來,多少有點點那個。
然後范老師提起了李皖的樂評,我認為李皖是作為一個业余聽者而不是專業人士在寫樂評,并向他介紹了我當時特別喜歡的做著足夠霸道的音樂同時也寫寫樂評的姚大均。
接下來我們交流了對王朔,韓寒等等作家的意見,最後基本上一致認定史鐵生是其中最對得起讀者的一個。
然後就聊起了范老師最關心的教育問題,我們差不多不用討論就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意見:貌似在教育部的管轄範圍內基本上沒戲,希望只能寄託在體制外學校身上!
這次非常愉快的會面的最後是這樣結束的:我因為當時沒買手機而給了范老師我的QQ號,范老師給了我他的手機號,然後范老師買了我那杯茶的單而我將我的老兄,也寫小說的馬吹牛馬老師給我的一張由他撰寫文案的,兩個搞音樂的彝族兄弟的一張作品DEMO贈送給了范老師。
在這張DEMO的封面上,這兩位彝族兄弟一位身著黑衣,一位身著白衣,長得非常非常之帥氣。
最後補充一句,對我剛才提到的馬吹牛馬老師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在網上搜索一下他的小說《混亂不堪》來看哈。
6
聽完了上面這個故事的你現在向我發問了:
“你說的這個故事,是好久的事情喃?”
我和范老師的這場對話雖然很愉快卻還沒有經典到可以牛叉轟轟地說一聲“一時”的地步,只好說,這個,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嗯,應該就是在第一次見到冉土匪雲飛先生的面之後不久吧。
我第一次見到冉土匪雲飛先生本人,是在我們蜀都的草堂讀書會搞的一次活動上。
這次活動的主題是
關於
那場惹得連海峽對岸的龍應台龍女士都忍不住要站出來請海峽這邊的胡總書記錦濤先生用文明來說服她的風波的詳細情況的。
我記不得當時都說了些啥子情況了,但我記得主講王怡王老師說話時那張充滿委屈的年轻激动的脸,和默默坐在他身邊的冉土匪雲飛先生不動聲色穩如泰山的面容。
情況都說了過後,王怡老師的總結發言是非常經典的經典到了我不能夠在這裡重複其具體內容以便維護版權的《保持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
您要是有興趣,請向王老師請教。
您要是已經知道內容,就請你再多微笑一次。
王老師講完之後,就該聽眾們發言了,大家都有話要說,但在說之前,有一個非常必要的環節:你要說的話願不願意留下录音檔案記錄,說之前要考慮清楚,然後選擇是或者否。
聽眾們按座位順序依次發言,,,,
輪到我的時候,我先掏出了一張我特意帶來的,由當時還存在但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的,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名字叫做“木馬”的樂隊的BASS手,也就是曹操來擔綱製作的,由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出版的名字叫做《彝族民歌的電子生活》的CD【注:這張CD是由身在燕京的眾電子樂手和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人民政府合作錄製的。】。
然後我選擇了可以留下檔案記錄,然後對王怡老師說:
當時具體是咋個說的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意思是這樣的:先自己介紹了一下自己,然後說,和政府合作,我可以保證你的言論自由至少是百分之五十五。
我当时之所以選擇五十五這個數字而不是六十甚至七十的原因,是正好那段時間我正在以“五十五公里”,“伍拾伍公里”,“55公里”這一系列馬甲在彝族人網(網址是www.yizuren.com)的論壇耍,和這個論壇的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們甚至還有一個網名叫李土不的彝族老爺爺一起耍簡直好耍到了讓我廢寢忘食地沉迷在電腦面前半夜三更餓了去廚房煮一碗面或者燙飯然後端著碗回來一邊吃一邊耍的地步,在所有這些兄弟姐妹叔叔阿姨裏面我尤其要介紹一位名叫羅木果的兄弟,他擺的鬼龍門陣實在是擺得太好聽了,如果你對這些好聽得不得了的彝族鬼龍門陣感興趣的話,你可以到我和羅木果在天涯開的博客“後青銅時代”上去翻看。同時你還能看到我用“查無此狼”這個馬甲寫的長篇小說處女作《琵琶行》,這個小說也正在以“後現代試驗搞笑穿越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的頭銜而在中國武俠小說發展史上留下嘿JB搞笑的一筆。
這一節龍門陣就擺到這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