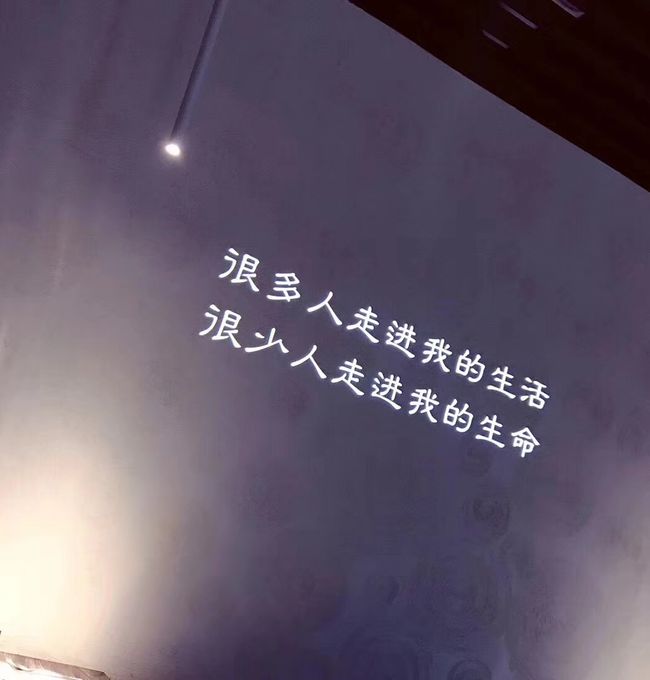盛夏来临,湾谷科技园里的姑娘穿的越来越不成体统了。
下楼去买杯咖啡, 氧气、欢鱼和小红书上的传说的鱼网黑丝袜、半边露肩衫、齐B短裙和克罗星皮裤都已一个个的映入现实,在温暖的阳光下,晃的我眼睛也睁不开。
咖啡厅里结账的长队排的让人难受,举目望去,YSL的24色口红可以在这里集齐。
排在我前面的姑娘低头发着微信,估计微信另外一端的男人在积极向她忽悠自己有条祖传染色体,要送给她,于是不好意思的笑容不知不觉的爬上她高原红的脸颊。
以至于星巴克店员问了她要不要奶,她才恍然大悟的随口回答:不要,我有。
说出口之后才发现似乎有所不妥,拿着咖啡匆匆坐到了吧台上,硕大的巨乳搁在吧台桌上,一副神游的表情望着窗外的绿地,似乎在 YY《霸道总裁爱上你》这样的桥段,“我忐忑不安的走在宾馆长廊上,敲开总裁的房门,哎呀,真是羞死人了”
正在神游期间,突然有个孩子跑进来问我:哥哥,你是来相亲的吗?
我说不是,然后他对着外面的一个美女说,姐姐进来吧,放心吧,不是他。
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你妈逼”是骂人,“你爸屌”却是称赞。 一把钥匙可以开很多锁,就是钥匙牛逼; 一把锁可以被很多钥匙开,就是锁有问题。
凭什么要一个男人在才华横溢的同时,还要做到貌似潘安,并且拥有 8 块腹肌和硕大的阳具?
而女人的美貌似乎就是永恒的“杠杆”——可以无限放大;可以让男人的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的奔溃危机。
女人靠一条丝袜摆平一个男人;男人却靠一条丝袜,要去摆平一个银行。
话说奶茶妹妹,估计正好喝奶茶,就被拍照了,就叫奶茶妹妹了。
如果他正在喝麻辣烫,拍下来,就是麻辣烫妹妹;
如果吃木须肉被拍到了,就叫黑木耳妹妹了吧。
但无论叫什么,人家长的漂亮是事实,叫什么都好听,不是么?
大学毕业的时候,每天出入陆家嘴汇丰大厦,看着楼下昂贵的星巴克排着长队。
而那时我每天像个毛驴一样,一边舔着酸奶盖子,一边重复着自己的工作。
那个时候纠结我的最大的困惑,就是中午吃炒饭省钱,还是吃炒面省钱。
想不到一下就过了本命年,碎了一地烟火。既要守得住忠烈,还得做的好婊子。
和时间死磕,败的只有传奇;与其逆流而上,不如随波逐流。
朋友总劝我,生活要知道满足,下雨有伞,炙热有阴凉,有二两小烧,一碟花生, 接受寡妇暗送的秋波,跟一群闲人打五毛钱的麻将,就是一种满足了。
别整天琢磨着怎么和王石去爬山,和潘石屹喝茶,喝着上年份的红酒看摇杯挂壁, 琢磨着收藏 12 个流失的兽头,人生的境界,不是天天幸福,而是天天不烦。
本命年已过,才知道一起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表象。
潦草的岁月不仅消融掉我浓密的长发和胸毛,也弄丢了我蓬勃的激情和梦想。
有时候早晨一觉醒来,居然忘记了下体的早勃,于是每天只能把演讲和码字当做自己性生活。
走进大堂,前面 4 个女人刚用完午餐,结伴扭着屁股往回走。
Christian Louboutin 的红底鞋和地板敲打出噔噔的声响; 另外一个女人的 Victoria secret 的 Bra 粉色肩带已经露出来了,她不知觉的往上提了提。
仔细凝听,女人谈话内容似乎关乎那个永恒的话题:男人和婚姻。
似乎在女人看来,婚姻都有 7 年之痒,所以她们都在讨论“头七”过了会怎样。
另外一个女人似乎说了一个关于他男伴的黄段子,引来了另外 3 个女人的花痴乱颤,颤的我都有些担心那条紧身皮裤会从她扁平的屁股上脱落下来。
吴磊总是说,真正纯洁的女人是不会紧紧捂住自己的裆部跟人谈情说爱的,只有那些逼上起了老茧的女人才夹紧双腿伪装纯洁。
这话也就是他这种色胆包天的人说的出口。他还对着一群女人说他上一次进入女人的身体是参观自由女神像。
而我更愿理解为:公主的纯情写在脸上,巫婆的深情种在心里。
眼看他们进入电梯,我疾步赶上,但很不凑巧,电梯门已经关上。
透过即将关上的缝隙,我看到一个女子,挥舞着身体,从电梯桥厢一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手伸向另外一头,附身尝试开“open”按钮。
在她附身按钮的瞬间,电梯门的缝隙透露出她橙色的胸罩,盖在略显扁平的胸部脂肪上,两坨白脂中间的沟渠中赫然挂着凡客雅宝的黑色十字扣。
门开了,一桥厢的女人,我很尴尬的不得不走进去。
我端着咖啡,更端着自己的身体,轻声的说了一声谢谢,顿时四个女人没忍住, 几乎同时噗嗤的笑出声来。 那一刻,我回忆起了小学语文课本陈然的《自白书》: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