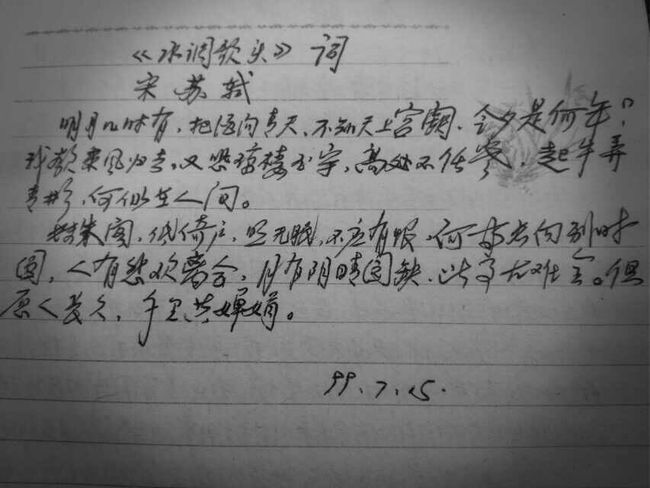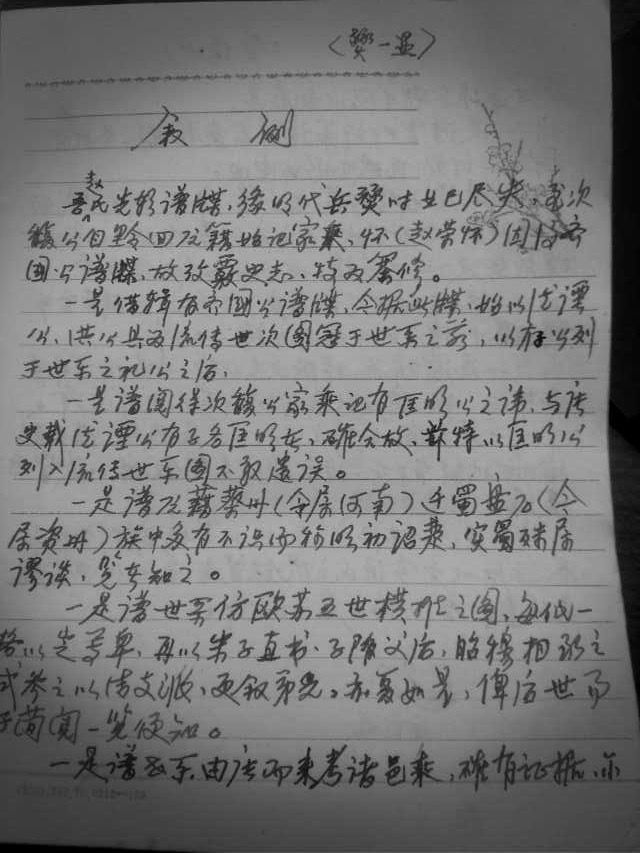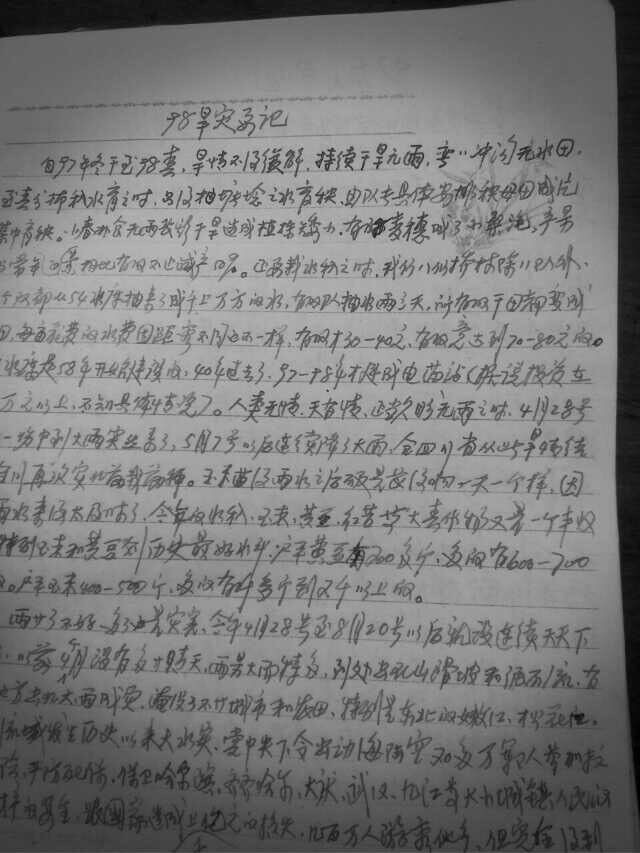- 放下是一段成长的修行
小莳玥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生和死。一件事已经做完了,另一件你还急什么呢?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是心,都有喜怒哀乐,这些再正常不过了。别总抱怨自己活得累,过得辛苦。永远记住:舒坦是留给死人的。苦,才是生活;累,才是工作;变,才是命运;忍,才是历练;容,才是智慧;静,才是修养;舍,才会得到;做,才会拥有。人生,活得太清楚,才是最大的不明白。有些事,看得很清,却说不清;有些人,了解很深,却猜不透;有些
- 将cmd中命令输出保存为txt文本文件
落难Coder
Windowscmdwindow
最近深度学习本地的训练中我们常常要在命令行中运行自己的代码,无可厚非,我们有必要保存我们的炼丹结果,但是复制命令行输出到txt是非常麻烦的,其实Windows下的命令行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操作。其基本的调用格式就是:运行指令>输出到的文件名称或者具体保存路径测试下,我打开cmd并且ping一下百度:pingwww.baidu.com>./data.txt看下相同目录下data.txt的输出:如果你再
- 高端密码学院笔记285
柚子_b4b4
高端幸福密码学院(高级班)幸福使者:李华第(598)期《幸福》之回归内在深层生命原动力基础篇——揭秘“激励”成长的喜悦心理案例分析主讲:刘莉一,知识扩充:成功=艰苦劳动+正确方法+少说空话。贪图省力的船夫,目标永远下游。智者的梦再美,也不如愚人实干的脚印。幸福早课堂2020.10.16星期五一笔记:1,重视和珍惜的前提是知道它的价值非常重要,当你珍惜了,你就真正定下来,真正的学到身上。2,大家需要
- Day1笔记-Python简介&标识符和关键字&输入输出
~在杰难逃~
Pythonpython开发语言大数据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杰哥开展一个新的专栏,当然,数据分析部分也会不定时更新的,这个新的专栏主要是讲解一些Python的基础语法和知识,帮助0基础的小伙伴入门和学习Python,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开始认真学习啦!一、Python简介【了解】1.计算机工作原理编程语言就是用来定义计算机程序的形式语言。我们通过编程语言来编写程序代码,再通过语言处理程序执行向计算机发送指令,让计算机完成对应的工作,编程
- 赠晶晶
在平凡中重新出发
逐伊衫望伊泪伊人雨中别离去莫再想莫再追莫要寸断再回味十六年六十年弹指挥间青鬓颜且浅行且珍惜待到山花烂漫时图片发自App
- 想家,想念家乡的四季
三妹杨敏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回自己出生地—老家,反倒有了一种出差走亲戚的感觉。人啊,出来得久了,就生分了。就不再那么心贴着心脸对着脸了。需要时间,需要机缘,需要我们再重新把自己的思维重置一遍,你才能够转得回这个弯儿的。最好的转弯儿,不是说教,也不是余旧,都有些治标不治本。真正管用的东西,只有一样。也简单。一个字:吃。吃一顿家乡的饭,喝一口家乡的水,听一听那浓重得有些陌生的乡音,心就回来了。心回来,人才算
- 学霸父母学渣娃,这孩子真是亲生的?太扎心了!
东北SK皇家成长中心
现在的社会,每个家庭基本都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哪怕父母平时上班再苦再累也不敢在孩子的教育上有丝毫的马虎,平时对孩子的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每天早起送孩子上学,晚上回家辅导孩子写作业,有的父母的文化程度非常高,但是每每到了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时候,父母们内心都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个孩子真的是我亲生的吗?真想一巴掌拍死他,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生出这么一个智障的孩子,家里每每就要上演全武行,看看这些孩子到
- 诡谲的一夜
乔三鳞
门缝里有一些眼睛,我再熟悉不过了,眼睛总和门有关。上次开门的时候,母亲的义眼骨碌碌地滚到我的脚边,顺着滚动的轨迹看过去,原来是父亲又打了母亲。父亲常这样殴打母亲,抓着她的头,往墙上,重重地砸。母亲的眼睛会掉下来,地上有灰,所以总要洗洗才能装回眼窝里。我想,装回去的时候会疼的——很疼,因为母亲总是流出血泪。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门和眼睛的关系是紧密的,现在也一样,门缝里那些如葡萄般一串串的眼睛,摘一个
- 不要偷走他人的声音
天天_27d6
朱会利焦点讲师班五期洛阳坚持分享第634天《来访者才是主角》2018.08.02今天的中级班课堂上,老师再一次给我们强调了咨询目标的建立过程中,作为咨询师一定要明白,我们只是在协助来访者解决他自身的问题,所以一切以来访者为主,他想解决的问题才是咨询的目标。所以如果在谈话的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感觉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的时候,我们不是再极力去引导来访者按照我们的思路走,而是觉察自己的预设并且进行调整,谨言
- 晨语问安2022年7月6日
求索大伟
『晨语问安7.6』不追悔昨日,不将就今天,不妄想未来。只要踏踏实实老老实实把今天做到、做实、做好,即使没有显著成绩,也要无怨无悔走实当下。昨日工作生活对也好错也好,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作用就是汲取营养,让自我更好地行走当下;未来即使再美好,也是空中楼阁,起到的是启明引领的作用,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当下的行动;今天不仅是空间上的承前启后,更重大的作用让梦想成真同时,也让自己行动更有针对性、思维更加犀利,
- 童年那些故事教给我们的
山川大地日月星辰
同事的女儿二次考研失败,但是仍不气馁还想接着再学再考,得为孩子点个赞,可是同事很矛盾,以她的意见,当初女儿大学毕业就该直接考编,回到家过安稳日子,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小马过河》的故事?她说跟小马有啥关系?幼儿园就给孩子讲《小马过河》,当然孩子们除了喜欢故事里的“人物”小松鼠、老牛、小马跟老马,对小马爱劳动喜欢帮助妈妈干活也是有基本认知的,孩子们对为什么老牛说水浅、而松鼠说水深也有一定的常识,到了成人
- 为什么瘦子很难增胖?
我的狗毛毛
我是个标准的瘦子,168,100斤。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我连马甲线都瘦出来了(体脂含量比较低)。但是我反而很羡慕那些比较丰满的女人,我的理想是再增重十五斤,练成前凸后翘的魔鬼身材。为此我开始纠正自己不规律的作息,吃高热量的食物,减少运动量,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但是结果却没有丝毫变化。我一直很苦恼,直到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英国的某个研究机构做了一个实验,想要知道瘦子能否在高热量的食物
- 越努力,越幸运!
Trulyjane
只有坚持,才可以做到~~记得以前在一本书上看过这句话:再深厚的夫妻感情,如果一方前进,而另一方保持色初心,止步不前,怎么也经不起岁月的考验,将会渐行渐远!当前是个务实的社会,很多的浪漫,没有面包的爱情经不起考验,所有的风花雪月都需要看似很俗却又不得不需要的东西~金钱。所以,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多去想想怎么赚钱,让自己无论说话还是做事可以随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拥有话语权。越努力,越幸运!!
- 二婚到底是领证好还是不领证好?
孟妃青
伟人讲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离婚了,再找对象,感情到了一定程度,领证结婚是水到渠成的事,再说我中华泱泱大国,有礼仪之邦的称谓,领证更是体现了尊重男女双方的行为。如果认为二婚就没必要领证了,只能说明,男女之间都暗藏心思,心不往一处走,日子过不好的。即便他们感情再深,都不是合法夫妻,只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假如不要二人共同的孩子还好,就怕有了孩子,没领证,到时给孩子上户口都成问题
- 疯丫头(四岁)
明媚如月
妞妞在姥姥家呆了十多天,姥爷问她,想不想爸爸,妞妞说想,姥爷说,我把你送回去吧,妞妞说,不行,我要等爸爸来接我。让妞妞吃东西,她不吃,说再吃会吃成大胖子。妞妞不喜欢上幼儿园,马上要开学了,我引导她,说一些幼儿园的趣事儿,她打断我,说,别说啦!好吧,我闭嘴。还总说,妈妈不上班,陪她玩儿。我总说她长了张女孩儿脸,内心住着个女孩子,甚至是个猴子,淘的不要不要的。大中午的,晒着毒辣的大太阳在院子里玩儿水,
- 祭坛随笔
阿门不热
街角右拐,便是北宋的祠堂。平日里冉冉的佛香被雨水打湿了,一地枯黄的银杏显得平静哀伤,如同一地被踩碎的阳光。我喜欢在这样的阴暗里吞噬古代的讯息,那遥远的来自过去的历史风潮。谢却茶扉,轻轻地抚上墙壁,寒风不御,无数深浅的纹路交织在心底,如同一把古琴不堪重负的尾音。寂寞锁朱门,香客们已是三三两两,巨大的雨帘让天空失掉了颜色,灰蒙蒙掉在阁楼一角,沉稳不惊地暗下去,再暗下去......古树上红色的挂牌像一块
- “日舍一物”之42——活在当下,并向前看
記二十一
这件衣服已经有十五、六年了(突然发现我可真是能囤东西啊)。这原本是一件我非常喜欢的衣服,无论是样子,还是质地。照片拍的比较渣,但其实,白色棉质衣料中,尚织有银色的丝线,在阳光或灯光下,会闪亮,不晃眼,但很漂亮。或许正是因为太喜欢了,所以一直保留着,尽管很多年都没有再穿过了。因为不合适了。首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尽管体重总量没有太多变化(哦,其实还是涨了)。但是体型还是和十几年前不一样了,最明显的就是
- 无题
琴韵无声
问了几家门诊部都没有科兴疫苗,突然自我感觉这种品牌的疫苗是不是少一些,于是又无端滋生焦虑感,可别一拖再拖影响孩子上学,学校要求下学期开学得接种完新冠疫苗。我在这种自制的焦虑的驱使下,立马上网查询看哪里能打到北京科兴的疫苗,终于找到了,大喜。与珊宝一起打车过去(路比较远,早想借此机会让她徒步拉练一下的计划泡汤了)。到达目的地,一看到医院大门前一条长龙似的队伍就知道那里应该是打疫苗的地方。迅速过去排队
- “愿你,戒酒也戒她。”
钟斯
你以荨麻疹为幌子,向全世界宣布,从今以后你不能再喝酒了,你要戒酒。你的朋友们,觉得你的健康最重要,所以大力支持,商量着以后谁都不能再劝你酒。可是,你转身就在夜深人静时独自痛饮,然后在意识涣散中发了疯地想她。你知道这样不对,但你难以自制。我一直觉得,你是那种“衣履风流,潇洒潇洒去了”的人,所以,当你跟我说你难受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诧异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如此洒脱的你难受。当我问及的时候,你
- 准备
胡珊珊乐平九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乐平九小的胡珊珊。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给大家做“智慧作业”应用培训。说到“智慧作业”我感触颇多,我是在智慧作业中成长起来的,我也时常以自己是一名“智慧作业人”自居。早在2020年疫情期间,学校电教处周光杰主任在学校群里发出智慧作业抢题通知,我看了有些心动,一节微课相当于一次省级公开课,这对于我们普通老师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但想归想,我也不会用软件啊,再
- 山海师秘录(草稿小段)
白淼清流
“阿弱,山北头还有两树好梨!我们给你留着呢,你快去采了吧,我们玩会儿就回家了。”几个伙伴都望着宁虚,其中一个胖胖喊道。宁虚望过去:“知道啦!你们趁着路好走,赶紧回家吧,这天一会儿怕是要下雨!”说罢,宁虚紧了紧后背的竹筐,迈步向山上走去。今天是村里采梨的最后一天,最多倒晚饭时,剩下的梨子便不许村民再采摘,熟透了便掉到地上,当做下次结果的肥料。宁虚顺着工匠铺出的简陋石道,却没有去同伴所说的山北头,而是
- 淘陶居老袁藏品
东海堂
【造像艺术】文化遗产•汉地木造像的区域特征、古代精品造像欣赏。。。。。。(来源:蠢牛/颜旭茂)原创2016-06-12作者:作者:蠢牛(颜旭茂)木造像的地位一直挺尴尬的。国外大型博物馆的木造像基本都是宋元以前的,明代只藏极品。国内也就故宫、国博和上博有能力弄几尊宋木,山西省博貌似只有一尊顶级的明代菩萨能拿得出手,其他木雕大省的博物馆再怎么也应当展示些明清木雕吧,总比同时代那什么坛坛罐罐更有艺术性。
- 2021-01-09 哥伦比亚 《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罗秀 译
juneyale
《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罗秀译序《总统先生,一路走好!》“再给我一杯咖啡。”他用纯正的法语说。随即补充道:“要意式咖啡,能让人起死回生的那种。”并没有意识到话里的双关含义。当火车开始加速,荷马突然发现总统的手杖还在自己手中,于是跑到站台尽头,把手杖用力扔过去,希望总统能在半空中接住。但是手杖掉在了铁轨上,随即被碾得粉碎。那真是恐怖的一瞬。拉萨拉看到的最后一幕是那
- 一个纯真姑娘被现实社会磨灭了热情
幽律
每个初入社会的人,都是满怀憧憬,热情对待这个社会,可往往都是被回馈以欺骗,恐吓,磨灭了热情。我的一个朋友,小吴,来自安徽的姑娘,初出校门,来到这座南方经济发达的城市,善良单纯,待人对事充满了朝气与热情。当时小吴所在的房产中介公司有一位女客户,是退休教师,谈吐方面能感觉得到很有素质,和她先生想要买房,小吴接待的。了解情况后,客户感觉经济方面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委托小吴先帮她卖自己的旧房,周转开来再买
- Table列表复现框实现【勾选-搜索-再勾选】
~四时春~
java开发语言elementuivue
Table列表复现框实现【勾选-搜索-再勾选】概要整体架构流程代码实现技术细节注意参考文献概要最近在开发时遇到一个问题,在进行表单渲染时,正常选中没有问题,单如果需要搜索选中时,一个是已选中的不会回填,二是在搜索的结果中进行选中,没有实现,经过排查,查找资料后实现。例如:整体架构流程具体的实现效果如下:代码实现{{scope.row.userName}}已选区{{userItem.userName
- 组诗·三国群英颂(周瑜、马超、贾诩、赵云)
颍川荀清
念奴娇·怀周郎矶头万仞、若关情,仍叹当年英物!一揽长江,龙流怒,化作孙吴阵壁。浪里船城,铁锁平川,袖挽千堆雪。烈胆豪情,斗牛惊认奇杰!但看戎马余生,纵横万里,正英姿勃发。宏图霸业弹指间,惟见涛生云灭。苍天轻狂,妒意猖作,帅将难华发。难忆郎顾,青史相伴别月。古体·西凉天将军大漠狂烟起,孑然佩青锋。神威震羌月,锦袍曜汉空。终囚蜀山险,瘴疠掩长虹。天地一孤啸,匹马又西风。水调歌头·文和乱武山水应将残,清
- Python 课程10-单元测试
可愛小吉
Python教學python单元测试开发语言TDDunittest
前言在现代软件开发中,单元测试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实践。通过测试,我们可以确保每个功能模块在开发和修改过程中按预期工作,从而减少软件缺陷,提高代码质量。而测试驱动开发(TDD)则进一步将测试作为开发的核心部分,先编写测试,再编写代码,以测试为指导开发出更稳定、更可靠的代码。Python提供了强大的unittest模块,它是Python标准库的一部分,专门用于编写和执行单元测试。与其他测试框架相比,
- 这样旅行的人,值得拥有丰富而饱满的体验
究竟
01“一张车票就实现了来拉萨的梦想。原以为很遥远,现也觉得旅途值得。也不过山河故人而已。”打开朋友圈,看到了强子新发的动态,配了两张图,一张图里是拉萨火车站,另一张图里是二十来张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火车票,终点站都是拉萨。又想起几天前,姑娘秀了一波在青海湖的美照,照片里的她,身穿鲜艳的红色长裙,坐在牦牛背上,阳光打下来,她笑靥如花。橙色的旗子风中飘扬,那蓝绿色的青海湖和天空再美,也都成了陪衬。再看看自
- python爬取微信小程序数据,python爬取小程序数据
2301_81900439
前端
大家好,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问题,python爬取微信小程序数据,python爬取小程序数据,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Python爬虫系列之微信小程序实战基于Scrapy爬虫框架实现对微信小程序数据的爬取首先,你得需要安装抓包工具,这里推荐使用Charles,至于怎么使用后期有时间我会出一个事例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就是分析接口,理清楚每一个接口功能,然后连接起来形成接口串思路,再通过Spider的回调
- 思考成长
丁昆朋
这篇文章是加紧赶出来“应付”日更,一方面不想要再晚睡了;另一方面不想失去日更达人的称号,只能坐下来匆忙写下一点文字。既然标题是成长,先来总结一下这段时间的收获:1、整理箱子站着可以看电脑,坐着反而是一种享受,减少了坐着腰酸背痛的现象;2、使用讯飞输入法大大增加自己的输出量;3、Anaconda+“pythontutor.com"+Google算是简单入门python;4、英语的阅读文章能力、听力提
- 遍历dom 并且存储(将每一层的DOM元素存在数组中)
换个号韩国红果果
JavaScripthtml
数组从0开始!!
var a=[],i=0;
for(var j=0;j<30;j++){
a[j]=[];//数组里套数组,且第i层存储在第a[i]中
}
function walkDOM(n){
do{
if(n.nodeType!==3)//筛选去除#text类型
a[i].push(n);
//con
- Android+Jquery Mobile学习系列(9)-总结和代码分享
白糖_
JQuery Mobile
目录导航
经过一个多月的边学习边练手,学会了Android基于Web开发的毛皮,其实开发过程中用Android原生API不是很多,更多的是HTML/Javascript/Css。
个人觉得基于WebView的Jquery Mobile开发有以下优点:
1、对于刚从Java Web转型过来的同学非常适合,只要懂得HTML开发就可以上手做事。
2、jquerym
- impala参考资料
dayutianfei
impala
记录一些有用的Impala资料
1. 入门资料
>>官网翻译:
http://my.oschina.net/weiqingbin/blog?catalog=423691
2. 实用进阶
>>代码&架构分析:
Impala/Hive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http
- JAVA 静态变量与非静态变量初始化顺序之新解
周凡杨
java静态非静态顺序
今天和同事争论一问题,关于静态变量与非静态变量的初始化顺序,谁先谁后,最终想整理出来!测试代码:
import java.util.Map;
public class T {
public static T t = new T();
private Map map = new HashMap();
public T(){
System.out.println(&quo
- 跳出iframe返回外层页面
g21121
iframe
在web开发过程中难免要用到iframe,但当连接超时或跳转到公共页面时就会出现超时页面显示在iframe中,这时我们就需要跳出这个iframe到达一个公共页面去。
首先跳转到一个中间页,这个页面用于判断是否在iframe中,在页面加载的过程中调用如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function
- JAVA多线程监听JMS、MQ队列
510888780
java多线程
背景:消息队列中有非常多的消息需要处理,并且监听器onMessage()方法中的业务逻辑也相对比较复杂,为了加快队列消息的读取、处理速度。可以通过加快读取速度和加快处理速度来考虑。因此从这两个方面都使用多线程来处理。对于消息处理的业务处理逻辑用线程池来做。对于加快消息监听读取速度可以使用1.使用多个监听器监听一个队列;2.使用一个监听器开启多线程监听。
对于上面提到的方法2使用一个监听器开启多线
- 第一个SpringMvc例子
布衣凌宇
spring mvc
第一步:导入需要的包;
第二步:配置web.xml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web-app version="2.5"
xmlns="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
xmlns:xsi=
- 我的spring学习笔记15-容器扩展点之PropertyOverrideConfigurer
aijuans
Spring3
PropertyOverrideConfigurer类似于PropertyPlaceholderConfigurer,但是与后者相比,前者对于bean属性可以有缺省值或者根本没有值。也就是说如果properties文件中没有某个bean属性的内容,那么将使用上下文(配置的xml文件)中相应定义的值。如果properties文件中有bean属性的内容,那么就用properties文件中的值来代替上下
- 通过XSD验证XML
antlove
xmlschemaxsdvalidationSchemaFactory
1. XmlValidation.java
package xml.valida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x.xml.XMLConstants;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stream.StreamSource;
import javax.xml.validation.Schem
- 文本流与字符集
百合不是茶
PrintWrite()的使用字符集名字 别名获取
文本数据的输入输出;
输入;数据流,缓冲流
输出;介绍向文本打印格式化的输出PrintWrite();
package 文本流;
import java.io.FileNotFound
- ibatis模糊查询sqlmap-mapping-**.xml配置
bijian1013
ibatis
正常我们写ibatis的sqlmap-mapping-*.xml文件时,传入的参数都用##标识,如下所示:
<resultMap id="personInfo" class="com.bijian.study.dto.PersonDTO">
<res
- java jvm常用命令工具——jdb命令(The Java Debugger)
bijian1013
javajvmjdb
用来对core文件和正在运行的Java进程进行实时地调试,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命令帮助您进行调试,它的功能和Sun studio里面所带的dbx非常相似,但 jdb是专门用来针对Java应用程序的。
现在应该说日常的开发中很少用到JDB了,因为现在的IDE已经帮我们封装好了,如使用ECLI
- 【Spring框架二】Spring常用注解之Component、Repository、Service和Controller注解
bit1129
controller
在Spring常用注解第一步部分【Spring框架一】Spring常用注解之Autowired和Resource注解(http://bit1129.iteye.com/blog/2114084)中介绍了Autowired和Resource两个注解的功能,它们用于将依赖根据名称或者类型进行自动的注入,这简化了在XML中,依赖注入部分的XML的编写,但是UserDao和UserService两个bea
- cxf wsdl2java生成代码super出错,构造函数不匹配
bitray
super
由于过去对于soap协议的cxf接触的不是很多,所以遇到了也是迷糊了一会.后来经过查找资料才得以解决. 初始原因一般是由于jaxws2.2规范和jdk6及以上不兼容导致的.所以要强制降为jaxws2.1进行编译生成.我们需要少量的修改:
我们原来的代码
wsdl2java com.test.xxx -client http://.....
修改后的代
- 动态页面正文部分中文乱码排障一例
ronin47
公司网站一部分动态页面,早先使用apache+resin的架构运行,考虑到高并发访问下的响应性能问题,在前不久逐步开始用nginx替换掉了apache。 不过随后发现了一个问题,随意进入某一有分页的网页,第一页是正常的(因为静态化过了);点“下一页”,出来的页面两边正常,中间部分的标题、关键字等也正常,唯独每个标题下的正文无法正常显示。 因为有做过系统调整,所以第一反应就是新上
- java-54- 调整数组顺序使奇数位于偶数前面
bylijinnan
java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Random;
import ljn.help.Helper;
public class OddBeforeEven {
/**
* Q 54 调整数组顺序使奇数位于偶数前面
* 输入一个整数数组,调整数组中数字的顺序,使得所有奇数位于数组的前半部分,所有偶数位于数组的后半
- 从100PV到1亿级PV网站架构演变
cfyme
网站架构
一个网站就像一个人,存在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养一个网站和养一个人一样,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法下有共同的原则。本文结合我自已14年网站人的经历记录一些架构演变中的体会。 1: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架构师不是一天练成的。
1999年,我作了一个个人主页,在学校内的虚拟空间,参加了一次主页大赛,几个DREAMWEAVER的页面,几个TABLE作布局,一个DB连接,几行PHP的代码嵌入在HTM
- [宇宙时代]宇宙时代的GIS是什么?
comsci
Gis
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在行星内部的时候,因为地理信息的坐标都是相对固定的,所以我们获取一组GIS数据之后,就可以存储到硬盘中,长久使用。。。但是,请注意,这种经验在宇宙时代是不能够被继续使用的
宇宙是一个高维时空
- 详解create database命令
czmmiao
database
完整命令
CREATE DATABASE mynewdb USER SYS IDENTIFIED BY sys_password USER SYSTEM IDENTIFIED BY system_password LOGFILE GROUP 1 ('/u01/logs/my/redo01a.log','/u02/logs/m
- 几句不中听却不得不认可的话
datageek
1、人丑就该多读书。
2、你不快乐是因为:你可以像猪一样懒,却无法像只猪一样懒得心安理得。
3、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那么你的生活将变成一件裤衩,别人放什么屁,你都得接着。
4、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买书太多,读书太少又特爱思考,还他妈话痨。
5、与禽兽搏斗的三种结局:(1)、赢了,比禽兽还禽兽。(2)、输了,禽兽不如。(3)、平了,跟禽兽没两样。结论:选择正确的对手很重要。
6
- 1 14:00 PHP中的“syntax error, unexpected T_PAAMAYIM_NEKUDOTAYIM”错误
dcj3sjt126com
PHP
原文地址:http://www.kafka0102.com/2010/08/281.html
因为需要,今天晚些在本机使用PHP做些测试,PHP脚本依赖了一堆我也不清楚做什么用的库。结果一跑起来,就报出类似下面的错误:“Parse error: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T_PAAMAYIM_NEKUDOTAYIM in /home/kafka/test/
- xcode6 Auto layout and size classes
dcj3sjt126com
ios
官方GUI
https://developer.apple.com/library/ios/documentation/UserExperience/Conceptual/AutolayoutPG/Introduction/Introduction.html
iOS中使用自动布局(一)
http://www.cocoachina.com/ind
- 通过PreparedStatement批量执行sql语句【sql语句相同,值不同】
梦见x光
sql事务批量执行
比如说:我有一个List需要添加到数据库中,那么我该如何通过PreparedStatement来操作呢?
public void addCustomerByCommit(Connection conn , List<Customer> customerList)
{
String sql = "inseret into customer(id
- 程序员必知必会----linux常用命令之十【系统相关】
hanqunfeng
Linux常用命令
一.linux快捷键
Ctrl+C : 终止当前命令
Ctrl+S : 暂停屏幕输出
Ctrl+Q : 恢复屏幕输出
Ctrl+U : 删除当前行光标前的所有字符
Ctrl+Z : 挂起当前正在执行的进程
Ctrl+L : 清除终端屏幕,相当于clear
二.终端命令
clear : 清除终端屏幕
reset : 重置视窗,当屏幕编码混乱时使用
time com
- NGINX
IXHONG
nginx
pcre 编译安装 nginx
conf/vhost/test.conf
upstream admin {
server 127.0.0.1:8080;
}
server {
listen 80;
&
- 设计模式--工厂模式
kerryg
设计模式
工厂方式模式分为三种:
1、普通工厂模式:建立一个工厂类,对实现了同一个接口的一些类进行实例的创建。
2、多个工厂方法的模式:就是对普通工厂方法模式的改进,在普通工厂方法模式中,如果传递的字符串出错,则不能正确创建对象,而多个工厂方法模式就是提供多个工厂方法,分别创建对象。
3、静态工厂方法模式:就是将上面的多个工厂方法模式里的方法置为静态,
- Spring InitializingBean/init-method和DisposableBean/destroy-method
mx_xiehd
javaspringbeanxml
1.initializingBean/init-method
实现org.springframework.beans.factory.InitializingBean接口允许一个bean在它的所有必须属性被BeanFactory设置后,来执行初始化的工作,InitialzingBean仅仅指定了一个方法。
通常InitializingBean接口的使用是能够被避免的,(不鼓励使用,因为没有必要
- 解决Centos下vim粘贴内容格式混乱问题
qindongliang1922
centosvim
有时候,我们在向vim打开的一个xml,或者任意文件中,拷贝粘贴的代码时,格式莫名其毛的就混乱了,然后自己一个个再重新,把格式排列好,非常耗时,而且很不爽,那么有没有办法避免呢? 答案是肯定的,设置下缩进格式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在用户的根目录下 直接vi ~/.vimrc文件 然后将set pastetoggle=<F9> 写入这个文件中,保存退出,重新登录,
- netty大并发请求问题
tianzhihehe
netty
多线程并发使用同一个channel
java.nio.BufferOverflowException: null
at java.nio.HeapByteBuffer.put(HeapByteBuffer.java:183) ~[na:1.7.0_60-ea]
at java.nio.ByteBuffer.put(ByteBuffer.java:832) ~[na:1.7.0_60-ea]
- Hadoop NameNode单点问题解决方案之一 AvatarNode
wyz2009107220
NameNode
我们遇到的情况
Hadoop NameNode存在单点问题。这个问题会影响分布式平台24*7运行。先说说我们的情况吧。
我们的团队负责管理一个1200节点的集群(总大小12PB),目前是运行版本为Hadoop 0.20,transaction logs写入一个共享的NFS filer(注:NetApp NFS Filer)。
经常遇到需要中断服务的问题是给hadoop打补丁。 DataN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