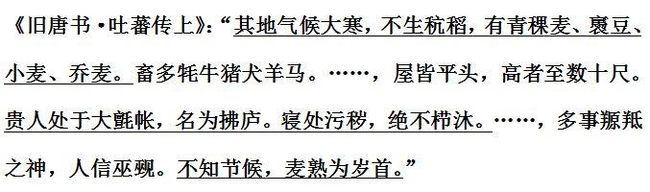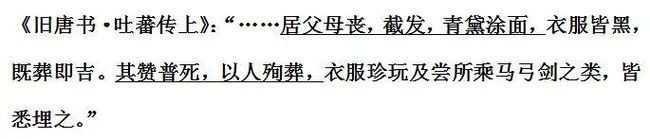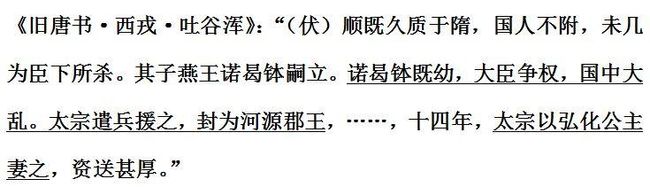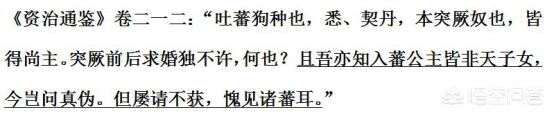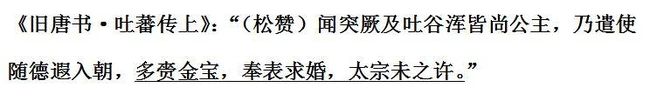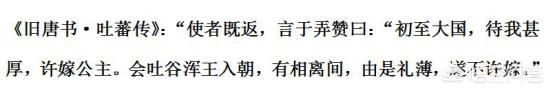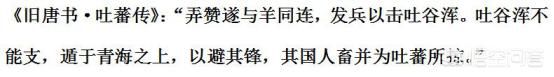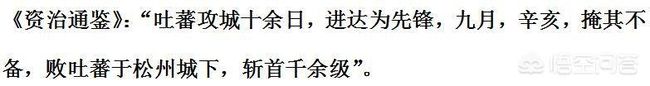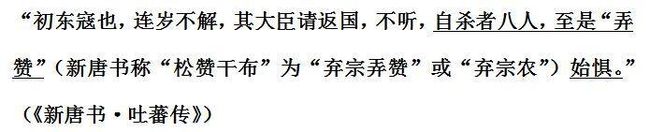本文五千字,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解读,这场充满“面子”意味的松州之战
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八月,勃勃而兴的吐蕃王朝与正处在“贞观之治”中的唐帝国,在川西北群山之间的松州(今四川松潘)迎头相撞。
这是两个大帝国第一次正面交锋,也就此开启了绵延二百年的唐蕃国战。
从松州之战的战役规模来说颇不值得一提,双方各损兵千数人便草草收兵,比之后期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的大兵团会战,松州城下的战事充其量算一次小边境摩擦。
但它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唐蕃两国均通过这场战争,改变了对对手的看法和策略,并成为之后二百余年间互相博弈的基础。
松州之战是时任霸主(唐朝)和新兴挑战者(吐蕃)间的遭遇战。
唐朝要维护其辛苦构建起来的东亚“天下秩序”,而吐蕃则谋取获得霸主的认可,博得挑战者应受的尊重。
因此,松州之战是一场充满了“面子”意味的战争。
今天,我们就从战争前后,两国关系变化的视角,来解析松州之战的影响。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李世民击倒了当时北方草原的霸主东突厥。此战震惊整个亚洲游牧世界,曾经臣服于东突厥颉利可汗足下的各游牧部落,纷纷倒向了唐朝,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
自此,唐朝成了东亚地区的盟主,随后唐朝以“羁縻州府制度”、“质子及宿卫制度”、“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及“公主和亲制度”四大制度相配合,构建了上承隋朝,具有唐朝特色的“天下秩序”。
之后的唐朝凭借“质子入朝”和“公主和亲”等手段,表明对周边诸政权的支持与否,先后瓦解、扶持了薛延陀、西突厥和吐谷浑,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至唐玄宗时至,围绕着唐王朝的政权,突厥、回纥、吐谷浑、契丹、奚、宁远国(拔汗那)、于阗、突骑施、南诏都成了唐朝“天下”体系的成员,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吐蕃。
吐蕃从达日宁塞(松赞干布祖父)起,国力呈现急速上扬之势,但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蕃悉卜野王族致力于高原上的争霸绞杀,无暇顾及周边地区事务,未向更远处伸出触角,从未与中原王权发生接触(“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旧唐书·吐蕃传》)。
但当松赞干布即位后,相继降服了苏毗和象雄,吐蕃王朝终于成为高原之上唯一的霸主。
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帝国,吐蕃王朝开始谋划走下高原向北方拓展,这便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到唐帝国的“天下秩序”。
因此,唐蕃两国是不可调和结构性矛盾,争斗的根本诉求是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这种不可调和矛盾的第一个引爆点,便是发生在贞观十二年(638年)松州之战。
其实,两国在松州动武之前,曾以遣使问候的方式互相试探,但很显然双方试探的效果都很差,也很草率,这导致两国领袖的决断都出现了偏差。
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长安朝见。(“其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始遣使朝贡”)
作为礼尚往来,唐太宗派遣冯德遐随使回访吐蕃,作为第一位正式访问吐蕃的唐使,冯德遐的观感是唐朝制定对蕃政策的基石。
虽然,冯德遐访蕃的报告现已不存,但从《旧唐书·吐蕃传》里对吐蕃的描述可大致推测出他的观感。
冯德遐对松赞干布个人的评价颇高,也认可吐蕃在高原的强势地位(“弄赞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但除这一句以外,其他的都是负面清单。
冯德遐吐蕃访问报告,涉及了吐蕃王朝政治、官僚、法律、农业、墓葬、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可见其考察颇为用心,其中有三点很值得玩味:
首先、贞观八年冯德遐访蕃时,吐蕃还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
我们都知道,藏文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创立并完善的,但显然至少在贞观八年,冯德遐访蕃时尚未形成。
其次、青稞的种植古已有之(“有青稞麦、褭豆、小麦、乔麦”),不知为何依旧有人坚信,青稞的种子是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
吐蕃人赭面(“青黛涂面”)的习俗,是文成公主入藏后在她的提议下,被松赞干布下令禁止的(“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
最后、当时吐蕃尚未形成规范的官僚体制和司法条文。(“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但随喜怒而无常科。”)
吐蕃王朝的官僚体系、行政管理制度和法令律条,大部分制定于松赞干布时期。但冯德遐笔触下的吐蕃,尚处在草莽初创、未臻文明的状态。
这一方面说明,松赞干布初期确实是白手起家,逐渐将吐蕃王朝打造成了官阶森严、律条明确的大帝国。
另一方面也说明,《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述,大多源于冯德遐的对吐蕃王朝早期的观感。
当这份报告送到李世民面前时,吐蕃的草莽模样,实在引不起他的兴趣,加之西南地区从来也不是唐朝的战略发展方向。
因此,吐蕃在李世民心里除了差评以外,还给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定位,既不值得武力侵夺,也不值得和亲笼络。
要知道,就在唐蕃两国互遣使节拜访期间,唐朝可是连续两次对吐谷浑用兵。
唐军在李靖、侯君集、李道宗、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名将的带领下,大败吐谷浑军,逼吐谷浑王伏允自缢,其子伏顺率全国归附于唐。
之后伏顺控制不住朝政,被其国人所杀,诺曷钵继位,唐朝不但出兵援救,还以弘化公主下嫁的方式,表达对其政权的认可。
从吐谷浑的案例可知,唐朝对于周边政权有明确的取舍标准。凡是值得下手的,不论是军事威逼,还是和亲拉拢,都毫不犹疑的实施。
而相比于吐谷浑很倒霉的,处于中原连接西域的咽喉位置,山高水远的吐蕃自然让李世民提不起兴趣。
正因于此,当吐蕃得知周边政权以“尚公主”为荣,为获得时任霸主的认可,松赞干布于贞观十年左右,再次遣使入朝,这次使臣只有一个目的——求婚。
我说当时周边政权借以“尚公主”为荣,绝不是给唐朝脸上贴金。和亲作为一个政治手段,在唐朝带有明显的政治选择性,并不是谁来求亲唐朝都许婚,有时即便许了婚,之后也称多次悔婚不嫁。
突厥毗伽可汗在开元十二年(724年)求婚被拒后,便曾恼羞成怒直接开骂。
但就像前文所述,李世民对吐蕃的观感实在太差,不想就此拉低了公主和亲的门槛,断然拒绝了吐蕃的求婚请求。
吐蕃使臣没有完成任务,为了能够像松赞干布交差,把锅扣在了吐谷浑头上,说本来唐皇对吐蕃很重视,对我们很好,但吐谷浑从中搅合,导致唐皇的态度急转直下,不答应求亲了。
吐蕃谋求获得霸主认可的举动受挫,那剩下唯一能够博取尊重的方式,就剩下上台比划比划了。
贞观十一年(637年)秋,松赞干布便以“吐谷浑坏了好事为由”兵发吐谷浑。
其实,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治理下,社会已经基本稳定,作为一个有扩张野心的大帝国,对那个方向用兵一定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松赞干布断不会因为影响了娶媳妇“怒而兴兵”,从地理关系的角度上看,吐蕃对外扩张的战略方向不外乎以下三条:
向东越横断山脉,出剑南杀奔四川;
向西跨昆仑山,攻于阗博取西域;
向北翻巴颜喀拉山,攻吐谷浑染指河陇。
在这三个战略方向上,草原连绵的北向,显然对吐蕃战争后勤的压力最小。所以,不管吐谷浑是否介入了求婚一事,松赞干布立威的第一刀都会砍向吐谷浑。
吐蕃用兵的时间窗口极佳,恰逢此前一年(贞观十年)李世民刚把吐谷浑打残了。实力未曾恢复的吐谷浑根本不是吐蕃军队的对手,稍稍抵抗便便败下阵来,吐谷浑王也逃入唐境寻求庇护。
打跑了吐谷浑王,松赞干布还顺手将青海湖东部的党项、白兰羌部也收拾了一番。但他发现唐朝居然对吐蕃的战果无动于衷,既然揍了小弟依旧没有引起老大的注意,那就得捋捋老大的虎须了。
那唐朝为什么会对吐谷浑的战事置之不理呢?
这就还要回到,李世民对吐谷浑和吐蕃的战略认识上了。
唐朝对于西南方向的国家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虽然唐朝多次出兵吐谷浑,但却对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依旧满足于将吐谷浑定位为“朝贡体系国家”,其国家领土则被唐朝定位为河西走廊的缓冲区。
因此,对吐谷浑的政策执行到“扶持亲唐政权,保持称臣纳贡”便心满意足了。
李世民对吐蕃的观感之前已经说过,两国间的“小打小闹”,并没有诱发唐朝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为获得唐朝的“尊重”,松赞干布顿兵二十万寇关松州,同时遣使入长安来迎公主(“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并对左右喊出了“公主不至,我且深入”的口号(《新唐书·吐蕃传》),松州之战正式爆发。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两国战前交往的事件排序:
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长安朝见。
贞观八年(634年)年底,唐使冯德遐随吐蕃使臣回访。
贞观九年(635年)上半年,冯德遐到达吐蕃,下半年出发返回长安。
贞观十年(636年)上半年,吐蕃使臣随同冯德遐抵达长安,第一次提出求亲申请,被李世民拒绝。
贞观十年(636年)十二月,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亲自来唐求婚,李世民许嫁弘化公主。
贞观十一年(637年)秋,使臣汇报唐朝拒婚后,松赞干布兵发吐谷浑。
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松赞干布在打了吐谷浑、党项、白兰羌后,发现唐朝无动于衷,寇关松州,同时遣使入长安第一次“迎公主”。
在松州之战前,两国进行了四次互访,吐蕃3次、唐1次。但这四次访问,并没有让两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唐朝没有给予吐蕃足够的重视,而吐蕃则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既然外交活动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战场上见吧!
文章最开始我曾说过,松州之战的战役规模很小,唐蕃两国不过是各有一个攻守来回而已。
松赞干布兴兵而来,松州都督韩威贸然出城与之野战,被蕃军击败(“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
而后,唐军转为守势,吐蕃攻城十余日不得寸进。八月二十七日,太宗以侯君集、执思司力、牛进达分三路救援(“督步骑五万击之”)。
九月初六,牛进达率前锋抵达,夜袭吐蕃营帐,斩杀千余人,松赞干布领军徐徐退去(“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松州之战结束。
这就是两国百年国战的开篇之作,双方不过各自损兵千数人便草草收场。
之所以双方都无意继续缠斗下去,原因在于两国均志不在此。换句话说,双方都没有死缠烂打的决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在朝堂上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在战场上。
因此,两边各自亮相,便很有默契的收手。
随后,便又是朝堂上的试探和斡旋,松赞再次遣使入长安,对军事行动道歉并第二次求婚,这次李世民答应了。(“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
李世民态度的转变是松州之战最直接的结果,这意味着吐蕃通过唐朝许婚,获得了足够的尊重,可以不用向突厥毗伽可汗一般“愧见诸蕃”了。
另外,吐蕃作为挑战者还收获了诸羌的敬慕。不但之后吐谷浑、党项、白兰羌均长期跟随身后,原本附属唐朝的川西羌酋也拜服在吐蕃脚下。(“羌酋阎州(一说阔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资治通鉴》)
那唐朝又得到了什么呢?
首先,唐朝没有在战场上失利,成功守住了自己的疆域,至少保全了亚洲霸主的面子。
其次,通过和亲缓解了西南方向的压力,之后十几年两国确实休干止戈保持了和平。
再次,在唐朝的要求下,吐蕃军队撤出了吐谷浑。唐朝的小弟吐谷浑得以复国,再次稳定了“天下秩序”。
最后,唐朝也寄希望于以和亲的政治手段,将这个实力颇强国家纳入自己“天下秩序”的构架之中(成不成功另说,至少唐朝是这么考虑的)。
所以,唐朝实际上是通过松州之战认识到了吐蕃的实力,并希望用一种低成本的解决手段(公主和亲),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松州之战的意义,战场行动完全是为了朝堂博弈服务,最后双方各取所需,以平局结束。
最逗的是,随后两国各自书写历史,都将自己打扮成了“获胜者”,而将对方描写成“失败者”。
唐史这边写的是,牛进达夜袭蕃营后,“弄赞(松赞干布)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旧唐书·吐蕃传》),以及“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至是弄赞始惧”(《新唐书·吐蕃传》)。
而藏文史料《敦煌本古藏文文献》大事记年里,则记载战后“李唐与吐谷浑二者皆进贡”。
完全向左的两国史料放在一起看,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写史之人都是有倾向性的,读历之人也一样有倾向性,至于孰真孰假,各人自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