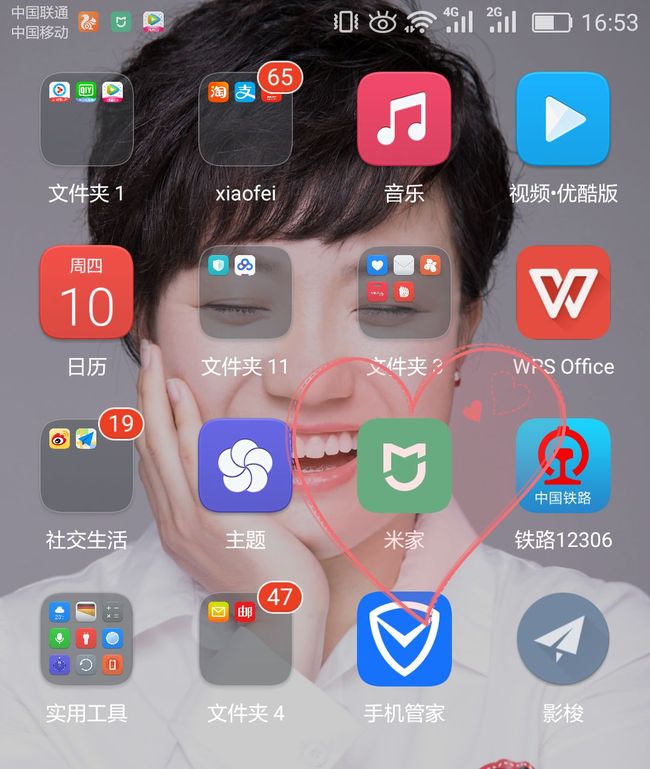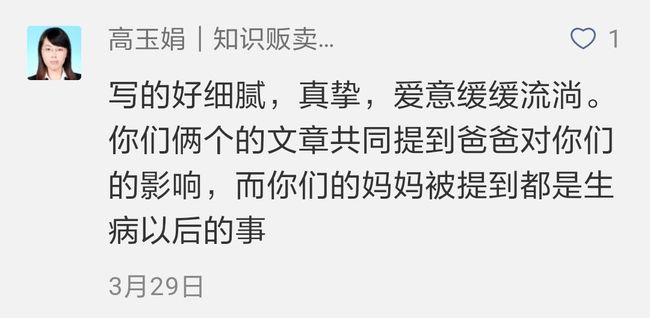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话:
去年母亲节,妈妈趟在床上,我在妈妈的床边写下了你这一生。
一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明天是妈妈的二七。这一年是我们最最难熬的一年,也是成长最多的一年,在母亲节,记录下我的心灵探索,祭奠在天堂的爸爸妈妈。
(一)不愿卸载的米家APP
虽然知道小米摄像头的另一端已无人走动(每次摄像头监控区域有移动,就会自动通知用户),但每次米家APP通知栏的新消息推送,都会让我“心有所动”。
摄像头是在妈妈第三次生病出院之后安装的,那是2016年年初。我与摄像头相伴的日子已两年多。
妈妈2011年农历六月十四日第一次脑卒中发病,之后时好时坏,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又发病三次,经历了四次脑卒中。
明天妈妈过二七。
从2011年第一次生病之后,刚刚研究生毕业,在外边工作边考试的我回到老家,与爸爸一起照顾妈妈。直到去年7月份,爸爸在照顾妈妈6年之后,心力交瘁,倒地未起。妈妈在爸爸二七的前一天第四次生病,在重症监护室门口焦急期盼了二十天之后,妈妈又一次挺了过来。妈妈坚韧的生命力,已然成为了医学奇迹,在不大的小县城口口相传。第四次出院之后的妈妈,已同刚出生的婴儿般,浑身上下只有眼珠和头可以活动。
料理完爸爸的后事,弟弟的婚事,把出院的妈妈接回老家的房子,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弟弟牵着妻子的手,回到省会城市工作生活。老家空荡荡的二层小院,只留下我和如婴儿般的妈妈。
我要工作,有孩子,有家,有自己想追求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还有躺在床上的妈妈。
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
老公陪我到家政公司找来了保姆。安排妥当,生活继续。不能陪妈妈的日子,是监控摄像头给我以安慰。而今,妈妈已不在,我却迟迟不愿意断网卸掉摄像头。我的摄像头情结何时才能了去?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 ——周国平
妈妈和爸爸是我们生命的共同源头,同样的存在,同等的重要,在5.13母亲节,纪念妈妈的日子里,如何能不想起爸爸?
当初安装监控是为了随时了解妈妈的情况,可是去年在摄像头里确认爸爸趴在地上的那一刹那,让我对摄像头有了深深的恐惧,可是找了保姆之后,摄像头依旧不得不用。每次打开摄像头的时候,都有一念闪过:
我何时才能不需要再用到监控?
如今,我确确实实不再需要打开这个让我深深恐惧的软件,而我却不愿意卸掉它?我在期盼着什么?躺在床上无聊刷屏的间隙,还是会下意识地去点开米家APP,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期盼着奇迹出现,期盼着无线电波那一端传来的仍是爸爸妈妈的讯息。
(二)这真的是孝顺吗?
妈妈的葬礼上,亲朋好友们拉着我的手,开着玩笑:“采访一下刑满释放人员,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笑来老师讲:七年就是一辈子。我一被困就是一辈子,现在刑满释放,感觉怎样呢?
我问自己:你真的有被释放的自由感吗?
“……”一旦犹豫,必有隐情。
被困的这几年,
我抱怨,婚后一年360天我还是在娘家,我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
我抱怨,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而我却被迫“坐进观天”;
我抱怨,罗胖的跨年演讲夜我还在给妈妈换纸尿裤;
我抱怨,本来陪孩子的时间,我在喂不愿意张嘴吃饭的妈妈;
我抱怨,单位的任何活动我都没有时间参与;
我抱怨,007线下活动这份饕餮大餐我却只能望而却步;
我抱怨, 妈妈是我一个人的妈妈们,爸爸为何不主动提出让弟弟承担一部分责任?
我抱怨,……
这都是真的吗?真的是妈妈的病,把我硬生生从大帝都拉回来的吗?每次别人在夸我“孝顺”的时候,对妈妈的愧疚感会油然而生。
我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与爸爸平等对话,来谈更合理的妈妈的照顾问题,比如可以找保姆,这样我们都有更自由的空间。
这七年,我外在看似无怨无悔地照顾妈妈,内里却积攒了太多对爸爸的抱怨”,对自己的“恨”。
我一直在探索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听话地被“拴”在家里做着全职保姆的工作。
对,听话。我一直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为什么我要做个乖孩子?听话可以获得爸爸的肯定,刷存在感。
因为从小到大我都不能令爸爸满意。我不是男孩,没能为三代单传的爸爸完成传宗接代家族使命。我知道这种性别偏见不是爸爸的错,但是生长在传统家族制的环境里,爸爸不能幸免,我和爸爸都是受害者。性别偏见的按钮一旦启动,我这个女孩,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在家里没有任何存在感,我学习没有弟弟好,我数理化学的一塌糊涂,我理科考不上大学,我长得不漂亮,我个子不高,我没有听爸爸的话读师范上中专,我没有……
总之,发生在身上的一切都是不好的,我的一切都是错的,我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我在家里没有任何存在感。没有存在感,倔强的我要刷呀。
妈妈生病后,我毫不犹疑,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照顾妈妈的责任,潜意识里,我用看似心甘情愿地照顾妈妈,来博得爸爸的喜欢,我用行动告诉爸爸,我是有用的,有价值的,是有存在感的。真想抱抱当初那个“摇尾乞怜”的自己。
妈妈,对不起,我不是真孝顺,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感而照顾你这么多年;
妈妈,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三)那根牵我的线还在那里
初中地理课上,我望着窗外的吕梁山,在日记本上写下:
我一定要走出大山。
而真正走出大山的我,为何会被所谓孝道、所谓自我存在感、所谓价值感的线轻而易举地拉了回来?
去年,爸爸的离去,所有的人都觉得是意外,是突然发
生的。而我在监控摄像头里,确认爸爸趴在地上的那一刹那,第一反应是:
尘埃落定!我这么多年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我安心了,不用再提心吊胆。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知到:
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希望他“死”的冲动。所以我们会说——爱死了。爱的另一个极端是死亡,当你不能确保所爱的人健康快乐的时候,你真的希望他“离开”,这样你就永远地拥有了他。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真切的画面感,从小到大,我无数次地在头脑中看到爸爸趴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这种恐惧感折磨了我二十多年。
这么多年,爸爸每一次出门,不论远近,无论干什么,我的心都是提在嗓子眼的,我怕爸爸出门再也回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死亡焦虑,死亡恐惧?
同时,在妈妈生病最初的那段时间,我甚至发狠到希望爸爸妈妈一起离去,我就可以自由自在过我的生活。因为这个大逆不道的闪念,那种愧疚感一刻不曾停歇。
在看似心甘情愿地照顾妈妈的这些年里,我时时笼罩在死亡的恐惧和愧疚感中不能自拔。于是我到健身房锻炼、学习冥想、练瑜伽、学习心理学,来释放我的恐惧与焦虑。
直到最近在武志红老师的专栏中读到:
共生关系是共享一个自我。所以不管谁离开谁,共生关系的破裂都意味着这个共享自我的死亡。这个时候,活在共生关系中的人会产生死亡焦虑,而婴儿因为会觉得,我如果想离开你,你就会死,因此你会恨我,想杀了我;同样的,如果我想离开你,我也得杀了你,不然你不会让我离开你。——武志红
活在共生关系中的人会产生死亡焦虑。也许,我的死亡焦虑,只是因为“共生”。武志红老师在他的书中多次提到,大多数的中国家庭一直处于共生的状态。之前,我从没有把自己的这些焦虑与恐惧与“共生关系”联系到一起。
走出大山的我,也许是被“共生”的线硬生生拉回来的,也许没有妈妈生病这回事,我也会找其他理由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妈妈的病,只是我的一个台阶。
那些看似大逆不道的闪念,也许只是作为孩子想成长,想独立,希望自由的基本的人性需求而已。
妈妈,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而今,与我产生共生关系的父母都已离去,共生的明线已断,而我依旧可以感觉到还一根若隐若现的“线”在牵着我。为什么?这里还有什么在羁绊着我?
(四)继续在找妈妈的爱
我多次在文中提到自己内心的不温暖,我尝试寻找,我说温暖的生命底色,才会流淌出温暖的文字
去年的母亲节,我写了关于妈妈的文章你这一生,爸爸看后委婉地向我表达了对文章题目的异议,表明妈妈明明还在,我为什么要用这样有明显盖棺定论味道的题目。
我也不知道。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妈妈不在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找不到妈妈,感觉不到妈妈的存在。我和弟弟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妈妈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照顾的非常好,但是,我们就是感觉不到妈妈的“温度”。
妈妈总是少言寡语,眉头紧锁,机械地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工作上班,鲜有与我们的情感互动。交流最多的时候,还是在妈妈生病的最初几年,还与我们有很多情感互动。
好友玉娟在看完我和弟弟的文章后留言:
孩子会将母亲感知为自己的内部空间,而父亲不同,父亲是自己世界之外的第一个“他人”,所以父亲象征着外部世界,因此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孩子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雏形。 ——武志红
所以,我在下意识里把自己的不温暖与妈妈联系起来。
爱的源泉不在表面,它在内心最深处,与我们的痛苦一样深。神圣的母爱隐身于黑暗的地窖里,我们必须走入地窖才能找到她,而且必须穿越我们的恐惧、愤怒和愧疚,才能感受到她无条件的爱。 ——保罗·费里尼《宽恕就是爱》
扫一扫,开启奇妙的自我探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