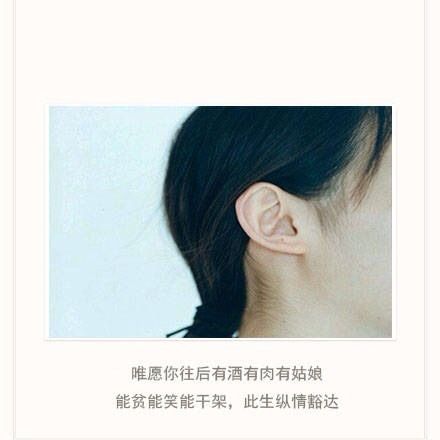很久以前看到过兰波的字母诗,在雪莱的西风颂和惠特曼的草叶集中突然出现这么一首想象力爆棚的诗,让人眼前一亮。在他看来每个字母都有自己的个性和色彩,诗句的后面是一个飞扬跳脱打破世俗枷锁的少年诗人。
后来看到李奥纳多演的兰波。就面相而言,本阿弗莱克更贴近兰波本人,可是幸好有了leo的演绎,此兰波也许并非彼兰波,但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可磨灭。
这孩子太野了。毫无顾忌地爱,毫无顾忌地狠。我不喜欢看到魏伦和他在一起,然而我很理解魏伦对这孩子的迷恋。
他无视诗社的任何人,甚至跳上桌子大闹一场——魏伦作为一个成熟的有地位的诗人不但不制止,反而疯狂地大笑,让兰波不要伤到自己。
就像王尔德对待波西:宠溺。把这两个孩子彻底宠坏了。为什么宠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抛弃妻子锒铛入狱?在那样一个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他们怎么敢?
无论是魏伦,还是王尔德,他们都已经得到了声誉、地位、金钱和妻儿,也开始感受到自己被社会同化,被家庭和社会责任压得喘不过气。兰波和波西,都有飞扬跋扈的青春和藐视一切的无知,让他们觉得第二春降临,再燃爱情… 这方面王尔德比魏伦理智许多,相比较魏伦的摇摆不定,王尔德可以说一直很理智地爱着波西,同时在孩子面前扮演好父亲的角色(他的丈夫角色是无论如何不能及格鸟),这也是波西比兰波幸福的地方:即使波西任性地说“你不爱我”,但是内心从不会怀疑王尔德永远在身后支持和保护自己;兰波问魏伦“你爱我吗”,魏伦醉醺醺的点头,却三不五时逃开兰波跑回家,把这个任性地惹怒他的少年孤零零留在异乡——兰波的恨和爱一样充满一种恶狠狠的味道。“爱”,魏伦想都没想就这么说。兰波冷峻地笑了:“那么,把手放在桌上,手心朝上。”
魏伦沉浸在和少年调情的旖旎氛围中的脸,和被兰波用刀扎穿掌心的惊恐表情——对比起来及其有趣。
兰波有时候会狠狠亲他,有时候满眼憎恶地看着他。这个男人,什么都做不到位,惊世骇俗做不到位,爱又爱不到位,就这么窝窝囊囊地被世人骂着又缩头缩脑向世俗屈服。兰波鄙视地对他说:“做错就做错了,事后别再道歉,用道歉来侮辱被你伤害的人。”魏伦这辈子都做不到。他丢开了兰波,不考虑少年今后会怎样,正如他当时为了兰波抛弃妻子,也没考虑家人今后如何面对世人的嘲讽。他没有耐心,甚至用枪打通了兰波的手。(世人的通病?兰波要是看过富江,就不会对魏伦竟然想杀他的事实震惊了。)
王尔德被波西的父亲送入监狱,傻兮兮的波西吓哭了,王尔德淡定地告诉他“没关系的,波西。无论发生什么,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曾经波西太骄纵,王尔德不止一次说要和波西分道扬镳,结果一看到波西哥哥的死讯就本能地要去找波西——“可怜的波西,一定难过极了。”如果兰波能看到这一场,必定得把魏伦的手掌扎烂了吧~
兰波和波西,一个是野草一个是娇花,身份地位天差地别——兰波在自家牛圈旁的泥地上奋笔疾书,波西却衣着考究地和一群美貌少年寻欢作乐,一个美得肆无忌惮,一个美得艳惊四座。唯一相通的是他们的浪漫理想,还有:父爱的缺失。兰波从出场就没有爸爸,波西的父亲暴虐专横至极。魏伦真心欣赏兰波的才华,带他来大都市生活;王尔德怜惜波西的美貌,竭力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两个少年迷恋的其实是来自父辈的爱和认同。对于兰波可能还多一点,他想要成名的机会,魏伦无疑能帮助他。
能说他们的感情深刻、让人感动么?显然不能。我看到的是功利、欲望、肤浅和懦弱,而不是爱。我想兰波自始至终都清楚这一点,是以他只肯说“i'm very fond of you”而不肯言爱,波西也只是想要有人宠自己罢了。
韶华很容易就逝去了,只有塑料花草才永不凋谢。短暂以为美,从古至今皆如是。全蚀狂爱,让太阳盲目也只是一下子而已,狂是爆发,不是永恒。
但这种美才够刺激感官,也让人有资本在失去它之后体验淡淡的哀痛。
兰波头也不回地走了,去蛮荒之地,得病断腿,在妹妹的怀中死去—— 魏伦只在他死后才知道这些事,因为兰波不玩了,我的事与你无关。为何而恨?绝不是不在乎,兰波在乎过魏伦所以才恨得如此决绝。可惜不是爱情,他的生命太短暂,还没明白什么是爱情。
垂垂老矣的魏伦独自坐在酒馆,像往常一样点了两杯苦艾酒。
少年兰波似乎就在他跟前,端起苦艾酒抿了一口。
“你爱我吗?”魏伦问。“你知道我喜欢你。”兰波回答,“那么你爱我吗?”
这一回魏伦没有喝醉,他清醒地认真地说“爱”。
兰波让他把手放在桌上,掌心向上。
这次魏伦没有被刀刺痛。少年拿起他的手,在掌心印下一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