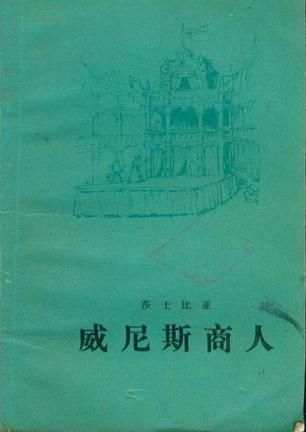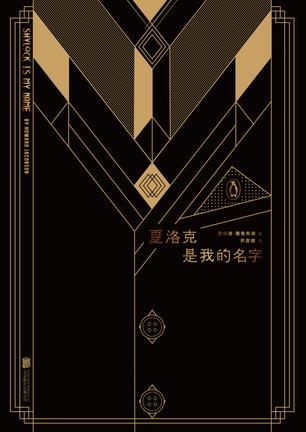英国作家、《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作者霍华德·雅克布森(Howard Jacobson)
2015年,企鹅兰登旗下的英国霍加斯出版社向全球八位小说家发出邀请,希望由他们来改写莎士比亚作品,以此来向这位英语世界的伟大作家和戏剧之王致敬,并纪念次年的莎士比亚去世400周年。
英国小说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接到邀请时,刚好完成了他的上一部作品,出于对莎士比亚的热爱,他欣然接受挑战。他让代理人告诉出版社“我想改写《哈姆雷特》”,代理人交涉后得到的反馈是:“嗯……这个确实很不错,但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告诉出版社我想改写《麦克白》。”但霍华德的第二次尝试依然未果。在来来回回交涉的过程中,霍华德几乎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又过了一遍——每一部悲剧,每一部喜剧,每一部社会问题剧,唯独忘了《威尼斯商人》。(注:莎翁社会问题剧指创作于1590年代晚期-1600年代早期的三部戏剧,《终成眷属》(All's Well That Ends Well)、《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和《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威尼斯商人》
[英]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
霍华德的选择性遗忘有其原因。14岁时,他在学校第一次接触到《威尼斯商人》。老师让同学们坐在课桌前,每个人认领一个角色,大声朗读剧本。老师对霍华德说:“你可以扮演夏洛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他是个犹太人。霍华德当时并没有觉得不舒服,他也不认为这是关于犹太人的一个糟糕剧本。等他成为了一名在大学教授莎士比亚戏剧的老师,他仍然对《威尼斯商人》提不起兴趣。
在漫长的沟通交涉之后,霍华德和他的代理人终于意识到,出版社希望霍华德改写《威尼斯商人》,原因和14岁时老师希望他扮演夏洛克一样显而易见:他是犹太人。但如今还应该补充一条:在英国,并没有很多用英语写作的白人男性犹太裔作家。作为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霍华德·雅各布森,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改编这个剧本的不二人选。“之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一段时间,我应该改写这部剧吗?作为一个犹太人,这是不是太过明显了?最后我说,我要重读一下这个剧本。”在重读过程中,霍华德渐渐意识到,自己14岁时对于《威尼斯商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剧本,尤其是放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来看,显得更加有趣。最终,霍华德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议,于是便有了《夏洛克是我的名字》。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
[英]霍华德·雅各布森 著 齐彦婧 译
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6月
《威尼斯商人》约写于1596年前后,全剧有两条交叉的情节线。其一是众所周知的“借债割肉”,威尼斯商人安东尼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一位如今落魄的贵族青年巴珊尼追求大家闺秀波希霞,向犹太富商夏洛克借了三千个杜卡(相当于七百英镑);他立下字据为证,若到期无法偿还,夏洛克将在安东尼身上割下一磅肉。第二条情节线是“挑匣求婚”。在贝尔蒙庄园,按照父亲生前的遗命,美丽而富有的少女波希霞的终身大事必须由父亲生前设置的三个彩匣决定。追求者慕名而来,但纷纷因选中了错误的彩匣而悻悻离去。最终波希霞芳心暗许的巴珊尼选择了正确的铅匣,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莎翁巧妙的安排下,两条线索在“法庭诉讼”一场中汇合。假装成法学博士的波希霞出现在威尼斯法庭,要求夏洛克可以割肉,但不能见血,以此阻止了夏洛克的割肉行为,挽救了安东尼的性命。
2004年由迈克尔·莱德福指导的电影《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庭诉讼场景
霍华德擅长将英国的日常生活转化为探讨犹太人在英国处境的幽默小说,在他笔下,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转移到了英国的曼切斯特,而波希霞所在的幽雅的贝尔蒙成为了柴郡——曼彻斯特的富人聚居区,同时也是犹太人聚居区。故事由此展开。夏洛克摇身一变,成为西蒙·斯特鲁洛维奇,一位犹太裔艺术品经销商。而与夏洛克关系紧张的安东尼奥,在这里叫做德·安东。至于那位富有的波希霞,在书中成为了一位住在古旧大宅中的、父亲爱抽大麻的普鲁拉贝尔。在继承了身为传媒学教授的父亲的遗产后,她整容,参加各种聚会,创办了一家名为“乌托邦”的餐厅,制作美食节目,开发互动视频网站,混迹于当地的富人圈子。
在这些完全改头换面的人物中,有一位并未改变,那就是夏洛克。在小说的第一章,当斯特鲁洛维奇在墓地中吊唁自己的母亲时,夏洛克就出现了。霍华德没给出什么理由,也没有多余的解释,他就在那里,他确实是那个从莎翁剧本中走出来的夏洛克。“墓地中的第二个人来得比斯特鲁洛维奇早得多……他就是夏洛克,一位易怒又暴躁的犹太人……”从此之后,夏洛克持续在场,与斯特鲁洛维奇交谈,与自己的亡妻交谈,也与自己的内心交谈。在这些不计其数的交谈或内心独白中,霍华德像我们展示了一个别样的夏洛克——或者说,一个数百年来被人以定式思维解读的夏洛克的另一种面貌。这是霍华德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惊喜。
第二个惊喜是对于一磅肉的解读。霍华德创造性地将“割肉”理解为斯特鲁洛维奇要为德·安东施行割礼。整个小说的高潮出现在接近尾声时的声势浩大的割礼仪式上,以德·安东主刀大夫的一封来信告终,在信中,他说:“经仔细检查验,此手术方法及其他任何手术方法,均属冗余,因该病人的包皮此前已被切除。”通过将一磅肉解读为割礼,霍华德对于犹太人身份以及信仰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一方面延续了莎士比亚原剧中关于犹太人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霍华德自己对于四百多年来人们对于这个剧本中反犹主义问题的批评和看法。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日前电话采访了霍华德。访谈从割礼聊起,谈到了原剧和小说中对于犹太人的解读,以及小说反映的当下英国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作家也谈了对于夏洛克这个人物的看法,以及古代夏洛克和现代夏洛克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何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莎士比亚。
关于割礼:
对于犹太人的古老恐惧仍在欧洲游荡
界面文化:在你的改写中,对于原剧中的一磅肉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解读,你是如何想到把这一磅肉和割礼联系起来的?
霍华德·雅各布森:我读完剧本开始写这部小说,突然就产生了这个想法。我还记得当时跑出书房,兴奋地对我爱人说:“我想我读懂这个剧本了,我突然明白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了。”你想想,一磅肉,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太奇怪了。在一些舞台剧版本中,我曾看过夏洛克以一种非常私人的语气对安东尼奥说出这句台词。在有的版本中,他甚至以一种十分私人的方式看着安东尼奥,他说“万一你失了约,就得随我的心意,从你身上的任何一部分割下整整的一磅肉。”这是十分私密的,甚至带着点儿调情的意味。我尝试思考这些细节的意义,直到那天我突然意识到,啊,这和一个古老的习俗有关。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从事莎士比亚时期犹太人研究的历史学家,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理论,一磅肉在某种程度上和割礼有关。你可能觉得我这么想一定是疯了。”他说:“不,我不认为这个想法很疯狂,你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我正在写相关的著作。”
界面文化:那在你看来,莎士比亚在写作这个剧本时,是否认为那一磅肉就是割礼?
霍华德·雅各布森:首先要明确,《威尼斯商人》这个故事并不是莎士比亚凭空发明的,这其实是一个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流传已久的古老故事。
我曾经在威尼斯的一个图书馆里看到过可能是最古老的版本的《威尼斯商人》,我不确定莎士比亚看没看过这个版本,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流传的过程非常有趣。早于莎士比亚几百年前,也有一个更早版本的剧本,我们仍旧无法确定莎士比亚是否读过。早期版本的作者十分明确地表示,夏洛克就是希望在安东尼奥身上施行割礼,这是他的复仇。如果这么想,整个事情似乎更说得通了。夏洛克在这个较早版本中说:“为了回应你对我是一个犹太人这一事实的羞辱,我要将你变为犹太人。”如果将割礼理解为一种惩罚,那么在隐喻层面上,他将安东尼奥变成了一个犹太人。
莎士比亚自己是否在一磅肉上做文章,我不确定。但我感觉这个剧本的氛围确实和割礼有联系。莎士比亚也许并不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但埋藏在他潜意识中的材料就是割礼,割礼是一种让异教徒变成犹太人的方式,而改宗是让犹太人变成异教徒的方式之一。想清楚这一点之后,我有了一个当代故事的灵感,毕竟很难为割一磅肉找到一个当代版本。
剧场版《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正准备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
界面文化:在后续的讨论中,很多人都提到《威尼斯商人》和反犹主义(anti-semiticism)的关系,这和割礼有关吗?
霍华德·雅各布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割礼背后还有个古老的故事。犹太人恐惧是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主题。在中世纪欧洲,人们十分惧怕犹太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人们不明白什么是割礼,也不明白犹太人为何对自己做这种事。当然了,不仅仅是犹太人施行割礼,穆斯林也施行割礼。但在英语世界,在欧洲,在非犹太的异教世界,他们听说的都是犹太人在遵从这种习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将割礼等同于自我阉割,认为犹太男性是在将自己变为女性。
曾经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迷信说法,犹太男性通过割礼实际上将自己变成了某种女性,因此他们和正常男性不一样。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迷信说法:男性在割礼中会流血,就像女性在月经期间会流血一样。建立在该想法之上的是另一个说法是,犹太男性需要换血,其中的方法之一是杀死异教儿童,取用他们的血液,这被称为“血祭诽谤”(blood libel)。欧洲人憎恨犹太人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可以一直回溯到《圣经》,而上面这些是迷信说法中的两个,这种迷信至今仍在欧洲游荡徘徊。
十五世纪的版画,描绘的是犹太人正在试图谋杀来自特伦特的赛门(Simon of Trent)
界面文化:所以,在莎士比亚创作《威尼斯商人》的时候,这些说法就已经存在了?
霍华德·雅各布森:很有可能。试想一下,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反犹主义其实很奇怪,因为当时英国并没有多少犹太人。在早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两三百年,犹太人已经被驱逐了。虽然一定会有一些漏网之鱼躲在伦敦,但总体而言,当时英国没有犹太人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和犹太人有关的焦虑。有关反犹主义很有趣的一点在于,即便在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反犹主义还是能够发展壮大,这种憎恨还是能够滋长。因此我认为这种迷信在每一个和犹太人或者犹太角色相关的剧本里都会阴魂不散。我并不是说这整个剧本是反犹的,而是说剧中总会有反犹的角色,而这种反犹的气氛来源于一种古老的恐惧。
关于反犹主义:
做一个反犹主义者,需要有狭窄的心胸和匮乏的想象力
界面文化:对于《威尼斯商人》是否是一个反犹太剧本曾有过很多讨论,你如何看待这些讨论?
霍华德·雅各布森:每次人们谈论起《威尼斯商人》,焦点都在于这个剧本究竟是不是反对犹太人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在讨论莎士比亚时不值一提的问题。我自己经常谈论这个问题,也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和作品,但我不希望莎士比亚被这样的对话毁掉。围绕莎士比亚有很多其他的话题。不管怎么说,对我而言,要让我相信一个如莎士比亚这般有着驰骋想象力的人可能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是很困难的。
做一个反犹主义者,或是任何一种种族主义者中的一员,你需要有狭窄的心胸和匮乏的想象力。只有无法想象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是什么样,人才能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在所有的作家中,莎士比亚是那个从来不需要为这个问题而感到愧疚的人。毫无疑问,在《威尼斯商人》中,他出色地想象了成为一个名叫夏洛克的男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剧本是在为犹太人辩护,也不意味着这个剧本是通过研究犹太人,让观众对犹太人产生谅解和同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剧本发生在一个充满反犹主义者的世界,当时大部分威尼斯人是反犹主义者。莎士比亚所做的就是他一贯会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将夏洛克人性化了:这就是此人,这就是此人之所是,这就是莎士比亚如何感知夏洛克其人之所是。而一旦他明白了个体之所是,他便无法以一种种族主义的眼光和方式去憎恨某个个体。一旦他明白了夏洛克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一个个体,他就会知道,因种族而憎恨一个人是多么狭隘。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作为一个个体的夏洛克,而非作为犹太人的夏洛克,了解到作为个体的夏洛克碰巧是个犹太人,我们就更能意识到当时威尼斯的人们对于夏洛克的想法是多么糟糕。我们对于夏洛克的同情越多,我们就越能感受到剧本中其他人物的那种狭隘的憎恨。
因此我从来不希望卷入这个剧本究竟是否反犹的讨论,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伟大的作家不会是反犹的。我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作家都不反犹,也有一些是的。但是真正伟大的作家,比如莎士比亚,他通过《威尼斯商人》将读者带入一个犹太人脑海中,通过《奥赛罗》将读者带入一个黑人脑海中,通过《麦克白》将读者带入一个谋杀者脑海中——莎士比亚对于这种一般人不喜欢的角色、对于从声名狼藉中拯救一个人有着浓厚的兴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人都厌恶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都憎恨奥赛罗或者麦克白?这些人的人性和困境又是什么?这正是莎士比亚要去捕捉的东西。
1922年电影《奥赛罗》海报
界面文化:作为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威尼斯商人》经常被改编,被搬上舞台。相比这些改编,你认为自己的改写有何不同之处?
霍华德·雅各布森:我见过作为英国首席拉比的夏洛克,也见过夏洛克变成了埃尔雷丝·普雷斯利,我也见过戏剧的地点从威尼斯移到了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场里,剧场喜欢更新剧本。并且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剧本中的反犹太元素,有很多改编都将夏洛克刻画成了一个现代或当代的犹太人,其中有些将时间设置在大屠杀之前,有些在大屠杀之后。
但我的作品有一些不同,我的小说不仅是这个剧本的产物,也是对于这个剧本的评论。由于我的双重身份——作家和批评家——我希望在小说中给予评论一些空间。我希望我的小说一方面是对于《威尼斯商人》的重新讲述,另一方面则是一篇关于这个故事的论文——当然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论文。与此同时,我也在小说中添加了一些与剧本解读相关的批判性思考。正如我刚刚说过的,将这个剧本解读为一个反犹剧本是百分百错误的,但这就是那些希望成为反犹主义者的人们几百年来的解读方式。因此夏洛克是那种最最荒诞可笑的、可怕的、充满复仇心与恶意的犹太人,是一个非常丑陋的老人。但实际上,以上任何一条都不能成立。在剧本中,夏洛克是机智的,并且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他是个老人;如果他很老了,为什么他会有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他可以是个很好的伴侣,也很风趣幽默。
界面文化:你之前的很多作品都探讨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在今天的英国,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本《夏洛克是我的名字》是否也可以归类到这个主题中?
霍华德·雅各布森: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随着我个人以及整个大环境不断变化,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一直在变,时好时坏。所以有时候我感觉更加愤怒,有时候我能用一种喜剧和幽默的方式看待,有时候我觉得情况还可以,大部分时候我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我感到事情倒退回了六七十年前。虽然这还没真实发生,但是有可能发生。
《芬克勒问题》
[英]霍华德·雅各布森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1月
界面文化:你是不是指在当下的英国,仍然存在着对于犹太人的厌恶?
霍华德·雅各布森:是的。我必须说,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英国很安全,我本人也没有过太多这样的遭遇。但对于犹太人的憎恨通常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国家,这种伪装后的变形是对于以色列的憎恨。在国内有很多相关争论:是否能在憎恨以色列人的同时不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可以对以色列抱有批评态度,但不憎恨犹太人。但还有一种反锡安主义(anti-Zionism,也叫犹太复国主义,指的是犹太民族主义者拟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主张),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首先反对的是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即犹太人在被流放后的两千年中一直想着回去。当你反对这个观点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反对一种犹太人的雄心和梦想,一种对于犹太人寻求安全感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这个国家目前正针对“反锡安主义是否等同于反犹主义”展开激烈辩论。有的人认为是,有的人认为不是,这其中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太能看到极端的反犹主义者,比如取笑犹太人的外貌,或者认为犹太人唯利是图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想法就完全消失了。
关于夏洛克:
对于富有想象力的犹太人来说,夏洛克一直存在在他们心里
界面文化:在小说《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西蒙·斯特鲁洛维奇对应着原剧本中的夏洛克,但从小说的一开始,作为读者我们也被告知,夏洛克本人一直在那里。为什么夏洛克一定要在场?夏洛克和西蒙·斯特鲁洛维奇的关系又是什么?
霍华德·雅各布森: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将剧本现代化的挑战时,通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对应的人物。因此我找到了西蒙·斯特鲁洛维奇,他将会成为我小说中现代版的夏洛克,二者的相似性显而易见:有钱,和不喜欢犹太人的人私交颇差;和女儿的关系恶化,他女儿正在准备离家出走;他有一个妻子,但病得非常严重,所以相当于没有妻子。夏洛克当然没有妻子,他是鳏夫这点在原剧中很重要。这点我们稍后再谈。
有了这个现代版的对应人物之后,我就开始动笔了。写了没几章就意识到,这样不行,因为斯特鲁洛维奇这个角色不够“大”,他无法承受夏洛克的重量。唯一的方法就是保留夏洛克。我一定要有这种勇气告诉读者,这就是夏洛克。
对此我有两点恐惧:第一是因为我确实是在直接沿用莎士比亚,这又包含两部分,一部分要写对于莎士比亚的阐释,另一部分是接着莎士比亚写下去。我认为莎士比亚是目前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作家,因此我感到恐惧。接着我就在想,如果要把夏洛克放在故事中,我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呢?最后我决定要无为而为,我不去解释了,就把夏洛克放在那里。现代读者对于现实主义十分熟悉,对现实主义而言,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要写的不是什么迷信的、超自然的或是有魔法的现象,夏洛克就在那里。事实上,没有人对此产生抱怨,读过这本书的人不会问为什么夏洛克出现在这里了,他们都接受了这个事实,不管是作为隐喻还是作为现实的夏洛克。
电影《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
之后的挑战是,如果夏洛克一直存在在故事里,我需要让读者感受到他的存在。我需要找到能够谈论他的语言,这种语言不能完全是莎士比亚的语言,但也不能离莎翁的语言太远。他需要有莎士比亚笔下夏洛克的那种庄严宏伟。
但与此同时,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摆脱了斯特鲁洛维奇。本来斯特鲁洛维奇是夏洛克,但如今有了夏洛克,我不再需要斯特鲁洛维奇。又仔细一想,为什么要摆脱斯特鲁洛维奇?完全可以有一个彼时的夏洛克和一个此时的夏洛克,他们可以谈论与犹太人相关的情形是如何变化的,作为不同类型的男性就这个话题展开十分有趣的对话。比如在四百年间,人发生了什么改变,犹太人发生了什么改变。我越是这么想,就越觉得我应该这么写。斯特鲁洛维奇于是变成了一个能够和夏洛克说话的人,我也因此自由了,不需要把我这个故事里的夏洛克放回到那个有着反犹太背景的剧本中。我可以让他开口,让他谈论犹太人,让他自己说世界现在大不同了。夏洛克不是现代人,他是一个古人,但同时我也需要赋予他一种既古老宏伟又非常新潮的语言,这是我所面对的挑战。
同时,斯特鲁洛维奇也接受了夏洛克的存在,我喜欢这个想法。这说明对于富有想象力的犹太人来说,夏洛克一直存在在犹太人心里。在小说中,他不是在斯特鲁洛维奇的脑子里,他是确确实实存在着。当我意识到这两个角色可以并存的时候,我很开心。
我最乐在其中的是两个男性对话的部分。不仅仅是有关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的讨论,还有更加悲剧的事情:他们都丧偶,都试图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对于男性来说,抚养一个青春期女儿实属不易。通常我们会同情女儿,因为我们知道父亲是多么糟糕,但我在书中希望传达的是,我们同时也同情父亲。同时,让两个男人谈论成为鳏夫、思念你曾经深爱的女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十分有趣。另外我希望说明白的一点是,在杰西卡偷走了那枚戒指之后,夏洛克独自神伤。虽然这只是莎士比亚的轻轻一笔,但增加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我希望这种悲剧色彩在我的故事中有所体现,并通过两次描写——一次是古代,一次是现代,使这一点更加强烈、更加深刻。
界面文化:所以是否可以说,夏洛克是斯特鲁洛维奇的二重身(doubleganger),或者后者是前者的二重身?
霍华德·雅各布森: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非常文学性的表述方式。但当他们开始交谈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这样的词汇,他们就在那里。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想到“二重身”,我想的是人,夏洛克是一个人,斯特鲁洛维奇也是一个人。我想的是现实主义,这也许是奇幻的,也许是隐喻性的,但最终,我希望传达的感觉是百分百实际的、真实的和可信的。
界面文化: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维基百科对你的介绍中,有一句话是:“二重身是你的小说中一个重复性的母题。”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霍华德·雅各布森:不同意。我大概明白这个说法的意思。我尤其喜欢让男性对话。世界范围内有很多描述女性友谊的小说,但出于某种原因,却没有很多描写男性友谊的小说。这当然和小说的读者,和什么样的男性在阅读小说有很大关系。只有很少数男性阅读文学性的小说,男性读小说通常会选择读惊悚或侦探小说。因此我写的小说,女性读者比男性读者多,比较像简·奥斯汀或是勃朗特姐妹作品的情况。但我喜欢写男性友谊,喜欢写男性和男性之间的对话。
说到这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用“二重身”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小说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文学化的形容,因为我并不是从这个词出发去思考和组织我的小说的。
《爱情迫害狂》
[英]霍华德·雅各布森 著 张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2月
界面文化:刚刚你也提到,小说中的夏洛克很健谈,他和斯特鲁洛维奇有很多很多对话,这些对话也帮助读者走进了夏洛克的内心世界。在写夏洛克的独白和对话的过程中,在语言上你是否遇到过一些困难?
霍华德·雅各布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如何确立一个身处于现代世界的活生生的角色,而非仅仅是一种遗迹、一种莎士比亚的鬼魂;如何让这个角色开口说话,但同时确保他的语言保留着莎翁笔下的严肃和响亮。当莎士比亚笔下的角色开口说话时,他们有一种特定的庄严,尤其是在他的悲剧中。实际上,夏洛克很多时候都是用一种幽默的口气在说话,但你能感觉到对于莎士比亚而言,角色所说的语言是多么重要。常常有那么一丝丝的严肃,太过严肃就变成了夸张,不够严肃就沦为了庸常。我该如何避免我的夏洛克沦为庸常?
一件我常常会做的,早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开始做的事情,是阅读大量的莎士比亚作品。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成为一个小说家之前,我写的第一本学术书就是关于莎士比亚的,我也在大学教授文学,主要是19世纪的小说和莎士比亚。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充满了莎士比亚,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故事,还有他剧中的角色,我时常“听到”莎士比亚。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这成为了我的一个优势。
我希望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句子出现在我小说里的各个地方,并不是要以此为乐,而是要用一些偶然的隐喻、典故和描述,来呼应莎士比亚的世界。书中有来自《威尼斯商人》的,也有来自他很多其他作品的引用,有些显而易见,有些隐藏颇深。对此最好的描述可能是,如果你一直“听着”莎士比亚“音乐”,那么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你绝对不会离他太远。
关于莎士比亚:
除了莎士比亚,我想不到第二个可以通过书写来发掘关于人的真理的作家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莎士比亚爱好者,在你看来,为何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莎士比亚?
霍华德·雅各布森:我认为我们如今十分需要文学,因为文学将我们从庸常的政治生活和观点中拯救。文学能将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空间,一个无偏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作家不必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一直觉得作家其实不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应该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做什么。
我认为莎士比亚是就是这种出类拔萃的作家,他不是一个带有意识形态的作家,严格来说,他不是一个由想法构成的作家。当然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但如果要说莎士比亚笃信什么,我觉得很困难,就像讨论莎士比亚的政治一样困难,比如什么是莎士比亚的性别政治?他的种族政治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从莎士比亚身上感受到的是那种强有力的想象,它质疑一切,是一种极具怀疑精神的想象力,所有的一切都亟待被重新发掘。我们也许认为,科里奥兰纳斯是一位贵族的、精英的怪物,当你进入他的世界时,就觉得需要重新了解这个人物。麦克白是一个谋杀者,但麦克白的想象力却是文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想象力,这需要解释。莎士比亚这种广阔无私的想象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在“写作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件事情上,莎士比亚是所有作家的典范。自由写作应该远离意识形态,远离所有这些让文学沦为庸常政治生活附庸的危险因素。文学世界应该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除了莎士比亚之外,我想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作家,他通过书写(writing)来发掘关于人的真理。
威廉·莎士比亚
回忆一下我之前提到的夏洛克是鳏夫的场景,莎士比亚并没有像小说家一样告诉我们——夏洛克有一个妻子,并且现在因为失去妻子而难过。就是那样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夏洛克发现戒指被女儿拿走了,他对身边的人说,“那是我的绿玉戒指,是我跟莉娅还没结婚的时候她送给我的。哪怕人家用漫山遍野的猴子来跟我交换,也别想我会答应呀。”一个绝妙的描述,漫山遍野的猴子(I would not have given it fora wilderness of monkeys)。我当时想把这本书命名为《漫山遍野的猴子》,漫山遍野的猴子是一个能产生回响的表达。夏洛克在这里使用这个比喻,描述了他内心的那种孤寂荒芜,一片荒原,一个除了猴子——这种不受约束的、贪婪的、丑陋的动物——之外一无所有之地。这就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当我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听到这个句子,它将我们的想象力抛出这个世界之外。这句话很重要,它不仅将我们带进夏洛克的头脑,还带进他的内心。在那一刻,我们看到夏洛克内心的色彩、阴影、声音、噪音以及那种空空荡荡。
莎士比亚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通过词语发现世界,词语就是媒介。他并非先思考,然后搜寻传达想法的语言,对他来说,一切始于语言。通过语言,故事才能被讲述;通过语言,我们的感受发生变化;通过语言,戏剧发现自己的意义之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作品始于最纯粹的艺术,并且一直保持着最纯粹的艺术的状态。对我来说,这是莎士比亚在当下的、甚至是永恒的重要之处。他是纯粹之纯粹的艺术家。
界面文化:你曾经在大学教授过莎士比亚,学生们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反映和反馈如何?
霍华德·雅各布森:在我教书的时候,他们确实很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已经很久不教书了,所以不知道现在同学们的喜好。我知道的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人们现在无法很好地阅读了,人们很难集中注意力,他们的注意力被手机、社会媒体和各种屏幕毁掉。人们如今变成了非常糟糕的读者,并且认为阅读行为十分困难。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回大学教书,我可能会发现即使是最好的学生,也读不了莎士比亚。
但另一方面,大家会去剧院看戏,莎士比亚的剧还是一直在上演,整个英国爱戴莎士比亚。因此我认为,剧院中的莎士比亚仍然是鲜活的,但真正的问题是阅读莎士比亚,人们如今不像从前一样能读莎士比亚了。这是个问题,但这不仅仅是和莎士比亚相关的问题。当我和在高校工作的朋友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如今让学生阅读有难度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但其实我们知道,越是困难的阅读体验,对你就越有益。
界面文化:那你认为在精英教育体制中,是否有神化莎士比亚的倾向?
霍华德·雅各布森:我不认为现在还有这种情况了,我倒是希望有。在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知识分子生活以及教育生活中,都有一种反对这种精英化的倾向。因此现在有一些很好的学校,他们不愿意教授莎士比亚,他们会建议教授现代戏剧。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将莎士比亚看得过高,而是我们根本没有给予莎士比亚足够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