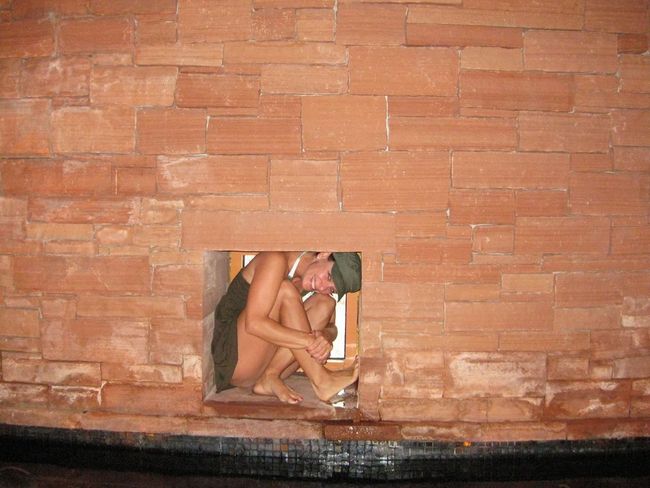首先声明一点,因各种需要,我偶尔会去北上广,本人对北上广也完全没有任何偏见。
说实话,哪怕全世界只剩下北上广,我估计自己也没法在那儿生存上一年。这完全是基于对自我的了解而做出的客观结论。也因为自叹不如,所以我对所有奋斗在北上广的人们,都充满了敬意。你们确实是有着非凡的本事,才能自如地在那儿生活和工作。我对你们的生存能力深感钦佩。
我喜欢旅游,也跑了不少地方。但每次有同学和朋友邀我去北上广时,我都会很犹豫。我知道好多好玩儿的事儿只有北上广才有,比如像样的表演和一些有趣的活动。可是一想到去北上广会面临的诸多麻烦,头已经开始大。我对很多事,都感到害怕。
北上广开车不是件享受的事儿,常常一堵堵得绵绵无绝期。步行只需20分钟的路,开车往往需要开一个钟。想骑自行车?那也得有自行车道才行啊。为了省时间和方便,我们常不得已要挤地铁。
我有过从地铁门外被乾坤大挪移,硬生生双脚离地就进了地铁的体验;也有过原本排在地铁门口第一个,门才打开不到一秒钟,我已光速般被甩到门边的经历。待排了几轮终于进了地铁,有时还会不得已跟一些面无表情的男女老少,随着车的开动、停止和摇摆,跳起了贴面舞。那场面很热辣,只可惜很难有快感。
心理学家说,40~120厘米是有分寸感的距离,40厘米以内是亲密距离,适合恋人和夫妻。看来在地铁上,每个人都是彼此的爱人,甚至比爱人还要更加亲昵一些。常看到新闻报道公交地铁性骚扰的事件,这让人愤慨。可是,这么亲密相对的公共交通,难道不是滋生性骚扰的温床吗?
偶尔运气好了,车厢空着,有些人低头玩手机或休息,但有更多的男女老少拿起手机,大声地煲电话粥乔事情,唯恐全世界不知道ta待会儿要去吃羊肉火锅。如果更加幸运,还会看到许多限制级画面,比如叉开两腿的女孩儿,把脚架在座位上的老汉,或被父母大声斥骂得哇哇大哭的小孩儿。这一切都太有生机、太具冲击力,我现在这虚弱的小心脏已经不太能够承受。
挤完地铁,到了餐馆里,期待着能喘口气,享受美食,大快朵颐。然而餐馆也同样刺激。绝大多数好吃的餐馆,都是人满为患。餐馆里人头汹涌,门外排着一条长龙。排队的人拿着号,三三两两玩手机或聊天。如果没有预约,常常要等上一小时。待终于排进去了,人声鼎沸、各种味道混杂着菜香,充斥着整个空间。闻着充盈的味道,就已经差不多饱了大半。
终于开吃了,常常不到半小时,我的头就已经被高音浪震得开始疼。我们为何不可以低声谈笑、享受美食呢?合理的说话声,应该只让需要的人听到即可。然而吃饭时,常会被无私地馈赠四面八法拋过来的各种段子,有些关于对父母的不满,有些关于对男女朋友的抱怨,更多的,是对工作发的牢骚。偶尔有点正能量的话语,也多被声浪吞没了。我喜欢在一个有人气,但分贝能控制在60以内,不要超过80分贝的餐馆吃饭。只可惜,这样的餐馆并不多见。
饭毕回到酒店想好好休息,躺下想睡时常会听到砰砰砰的砸门声。很奇怪,很多酒店看似高级,不知为何隔音却做得这么差。是开关门的人没有想到砸门声会影响到他人,是关门处没有做好缓冲的处理,还是房间根本没有隔音?好一点的酒店窗户已经安装了双重玻璃,将外面的车水马龙隔绝住,但遗憾却没有对户内噪音做处理。每次到北上广,基本都只能挑四星以上的酒店,多少还会有些保障。尽管这样,在订房前,还得反复反复看评论。一旦看到有“太吵”之类的评论,就只能果断地选别家。
在路上更是可怖,司机们都患了一种“不按喇叭不开心症”。有事儿按一下,没事儿也按一下。嘟嘟嘟嘟,此起彼伏。有时乘的士遇到躁狂的司机,更是苦不堪言。他每两分钟按一通,似乎前方满是危险。然而当我定睛观察前方,似乎完全没有提醒的必要。问为什么要按,他会说提醒前面的人开快一点或让他们闪开。为了减少对司机的刺激,我通常会暗示他尽量别按。可司机面带一抹轻蔑的微笑,按了一下不过瘾,还要继续按两下、三下,直到前方的司机接收到信号,着了魔似的也开始回按。很快,前后两个司机像是要比一比谁的喇叭质量更高,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按喇叭大赛。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只能默默地拿出随身带的耳塞,堵住我那脆弱的双耳。
据研究,人正常谈话的声音是40~60分贝。声音一旦到了85分贝,长期作用下就会引起听力损伤了。噪音是会极大地影响人的情绪和身体健康的。有时我们出门会觉得头痛、心慌,甚至还会变得心烦、易怒等,这还真不一定是因为工作压力,搞不好是因为生活的环境有噪音源。
我们常骂日本,但日本人对噪声的认知让人钦佩。日本人认为消除噪声靠自律,也制定了《环境基本法》,规定在市民居住区白天55分贝,夜里不能超过45分贝;住宅和商业、工业混合区白天60分贝,夜里50分贝以下。他们在生活中也是小心翼翼,生怕给他人带来麻烦。
在瑞典,晚上不能用吸尘器。在荷兰,晚上8点后不会用吸尘器、电钻等。居民区里不能按喇叭,高速上除非是遇到紧急危险的情形需要提醒对方,否则不会按喇叭。三年来,我们似乎只按过两次喇叭,都是因为对头车忘了开车灯。公共交通上更是自觉。上了车,不管有座没座,人人都会都会拿出书来看,或者低头玩手机。说话的人声音也会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你隐约听到有人说话却又听不清谈话的内容。
记得看过一篇报道,有英国科学家利用噪音的共鸣来发电。看到报道的当下,我真的是喜出望外。我们赶紧引进这技术吧!到北上广人多的地方采集噪音,这电力,绝对杠杠滴,还取之不竭。
除了交通和高分贝,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钱包、手机不见”。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扒手也是厉害的,但比起北上广的神偷们,他们明显段数太低。这中间,绝不仅仅是东方不败和童百熊之间的差距而已。我在北上广出门时,包包都会抱在胸前,这看起来很不美观非常不淑女,但实属无奈。
我对包包的保护欲强、反应大,这一点完全没有夸张。今年4月,跟妹妹同游布拉格时,两个人随时都处于战备状态。妹妹因为生活在深圳,表现得比我还夸张一些。某天两个人要出门吃饭,一路上习惯性地抱着包包走。到了一个餐厅坐定,习惯性地摸了摸,突然发现手机不在。只记得当时嗡地一声,整个人就炸开了。我极速地扫了一遍整个包包,都没!有!手!机!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很多可怕的想法:“网上银行!聊天记录!!联络名单!!!这下糟了,全都要被坏人利用了!”那一刻,我已想象得到坏人正一遍一遍地尝试着不同的密码,想要把网银上的钱转走的狰狞样子。
我一直翻一直翻,越翻越乱。服务员站在身旁,耐心地等着我们点菜。我抬起头,用欲哭无泪的声音说:“我的手机被盗了,请问该怎么办?我要报警吗?” 服务员惊讶地看着我,耸了耸肩,说:“我不知道啊。”
拉起妹妹,两个人极速奔回酒店。当我们满身是汗地回到酒店时,没想到手机正好好地躺在桌子上,一场虚惊。我真是病得不轻。
如果非要为自己辩解,我得说,这神经质的反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小,就被家人和朋友教育:出门要注意,包包要抱在胸前;手机不要拿出来边走边看,容易被抢;出门不要背太漂亮的包包,容易招坏人;走路不要太靠近路边,很多摩托党可能会抢了包包就呼啸而去,追都追不上!再加上在广州和深圳等地手机和钱包被摸过N次,留下极大的心理阴影,这病,就这么种下了。
在欧洲,很少看到反应这么过度的人。人们悠闲地度假,享受着阳光和美景,钱包和手机放在包里,随意摆在旁边,完全没有那么多的思想负担。而我们,就像是演技拙劣的喜剧演员,极尽夸张地用浮夸的演技演着“出门小心坏人”的戏码。
但最怕的,还是呼吸。早些年,我每次到广州都会大病一场。先是晚上睡觉时会觉得喉咙痛。第二天起来,会觉得鼻子堵堵的,一擤,两团黑乎乎的东西会跑出来。好容易扛过十天一周的,离开广州,整个人就开始大咳,不花一两星期把脏东西都排掉,是怎么也好不了的。到北京和上海也差不多,一睡下去,会觉得喉咙和鼻子都很干,整晚地干咳。出趟门回来,卸妆棉是黑色的,鼻子会觉得不舒服,一擤,也是黑色的。
我想,我是患了“天生不适合在北上广生存症”。我没有强健的体格和容纳百川的肺,轻易不敢挑战。
想当年,我是真的努力尝试过,立志要在北上广生存的。大学毕业那年,我曾经在深圳工作过。很幸运的是,一投简历就被录用了,工资比多数同年毕业的朋友高出一倍。用工资的1/4不到,在福田区中心租了一套单间,比起很多在深圳刚起步的年轻人,我那时的工作和生活算是不错的,没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也曾想过,如果我在深圳待到现在,估计也是背着三十年贷款,住在80/100平米的房子里,朝九晚五着吧?可我,是真的没用,做了几个月就仓皇而逃了。记得那半年里,我每天晚上都看到自己的灵魂飘在半空,冷冷地看着我,面带嫌弃和嘲讽,好像随时要弃我而去。我那时胆子比较小,很害怕不小心把灵魂丢了,所以找到机会就跑了。
你说得没错,在北上广,我确实没法活下去。偶尔去一趟,探探亲戚朋友吃吃饭,看看电影和演唱会,待个一周,我就会想要逃。你要说我没出息,注定无法飞黄腾达,我也只能点点头,认了。我想要抬头就能看见蓝天白云,能畅快地呼吸新鲜的空气,生活在安静怡人的环境和自由地出行而已,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以上内容纯属个人感受,请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那一定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