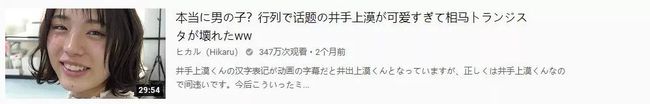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多「千年一遇」美少年?
从1988年开始,日本知名的时尚杂志「JUNON」每年都会举办名为「JunonSuper Boy」的美少年选拔大赛,邀请13-22岁没有经纪公司的男性参加,让许多有明星梦的少年被日本艺能事务所发掘,从而活跃在电影、电视剧和歌手舞台上。
被日本网友评价为“世纪末美少年”的柏原崇与刚刚在《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中有出色表演的菅田将晖都曾参加过这一比赛。柏原崇获得了第六届的优胜,而菅田将晖入围了最终十三名。
上:柏原崇《白线流》 下:菅田将晖《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
2018年,被称为「无性别美少年」的井手上漠进入决赛,获得大众广泛关注。因为单从照片来看,他更像是一位美少女,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美少年的容貌。日本大型经纪公司的杰尼斯事务所也有如道枝骏佑这样的新生力量,被日媒评价为「千年一遇」美少年,预言会是下一个柏原崇。
井手上漠的相关视频在YouTube上有很高的播放量
在日本,似乎每年都会多一位「千年一遇」的美少年,可以想见,还有很多美丽的少年淹没在了我们平常的关注的信息流里,但同样在被他们的粉丝关注和追捧着。这种对于美少年的喜爱不单单是审美的需要,同样触及到了日本美学的核心。
正如伊恩·布鲁玛在《日本之镜》中讨论的《第三种性别》:真正的男人不可能有女装扮相者一样美的扮相,就好比女人扮演的女性在震撼力上绝对不及能娴熟扮演女性的男演员。这其中恰有一种“男女合一的理想”。而在这种理想的背后,是难以脱离幼童世界、长大成人,但又崇拜青春与死亡的日本人。
《宝石之国》:各类宝石无性别之分,但语气上有偏向男性或偏向女性的差异。宝石之间以「兄」、「弟」相称。不须繁衍,没有性征与生殖器。主要以上半身如少年般纤细、下半身如少女般优美的「意识」来呈现宝石身形的美感。
1.
少男少女借“美少年”寻找成人世界出口
纵然西方的女子漫画里也充斥着长睫毛、亮眼眸的绝世美男子,但他们依然是男人无疑;他们开着跑车在海边兜风,最后邂逅幸运的女孩。正如我们先前所见,在日本,男主人公的性别暧昧不明,有时还会同性相吸。对于这些亦男亦女的年轻主人公,还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描绘他们,叫作“美少年”。
少女漫画——甚至有时少年漫画也算在内——的封面上经常出现美少年的形象。宝冢戏里那些令人心跳的万人迷往往都是美少年。穿着褶边衬衫,一笑就泛起酒窝的青少年电视“偶像明星”也是美少年。
如今再度走红的著名漫画家高畠华宵除了美少年外,不画任何其他题材,他的作品至今仍能在流行漫画上见到。典型的高畠作品里一般有一个身穿短和服或水手服的美少年,听着年长的小伙子传授骑术或剑术。
2019年1月,高畠華宵的画作在弥生美术馆展出
另一个流行的主题是美少年落难,比如说他被大孩子欺负,或者在海上遭遇了可怕的暴风。每每获救时,向他伸出援手的总是年纪稍大的前辈,后者用坚实的臂膀挽起少年的杨柳腰。当美少年独自出现在画面中时,要么像阿多尼斯那样吹着长笛,要么眼神迷离地举头望月,要么正在沐浴,要么躺卧在草地上,灵巧的手中捧着一本诗集。
高畠华宵
这些画的基调似乎带有同性恋色情的成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一本名为《JUNE》的少女漫画将这点表现得十分露骨。画中,身穿天鹅绒晚礼服、堕落腐朽的英国贵族在水晶吊灯下勾引精致的美少年。这份杂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少女品味,但它同样充斥着浪漫的爱情故事和惊心动魄的罪恶勾当,这一对结合既令人血脉贲张,也勾勒出部分少女漫画的特色。这些书并不以裸体少年与老淫棍交媾作为卖点。
依我之见,有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故事的标题有些神秘,叫作《钟上的带子》。故事讲述了一个美少年,十二岁丧母,十四岁被妓女收养,后来娶了一位富有的伯爵夫人,却发现自己更喜欢男人,于是做起了牛郎。
很难揣测年轻读者在阅读这部漫画时会有什么想法。读者来信也没提供什么信息,不过有位姑娘给出了提示。她写道:“这个幻想世界让我的脊背因为兴奋而簌簌发抖。”由于日本人十分注重外表,而忽略其背后真正的含义,我们就此或许可以认为,这些青年梦想家中的不少人比他们的淫秽梦境所暗示的要纯洁得多。
美国电影《虎口巡航》(Cruising,1980)在日本首映期间,成群结队的学生蜂拥前去购买纪念品项链、网眼背心等纽约同性恋地下组织的装束和物件。总而言之,青年梦想家和学生一样单纯。他们觉得这么做很“格好いい”(很帅、很酷之意)。“格好いい”这个词很难译成英语,意大利语里倒是有个近义词:叫bella figura,意指出尽风头。
《虎口巡航》剧照
许许多多的少女——少男则要少一些——或许觉得成人世界迫使他们变得工于算计,因循守旧,逐渐磨灭了天性,因而在同性恋幻想中寻找宣泄的出口。这种幻想与他们的生活相去甚远,并不令人感到威胁;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浪漫理想,比方说“梦中的巴黎”。美少年,不管是不是同性恋,下场一如吸血鬼或外星生物。他们个个是弃儿,是腐朽的成人世界里纯洁无瑕和青春永驻的牺牲品。
当然了,或多或少有所掩饰的同性恋色情幻想在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中间都很普遍。它在日本断然不像在西方那般禁忌。它从未被视为是罪恶的越轨,或者是一种疾病。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较少与人谈及罢了。况且只要社会的礼仪规范(比如说结婚)得到遵守,那它就完全是被许可的。
2.
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对美少年的迷恋
作为一种理想的爱情形式,同性间的爱情早在少女漫画或宝冢歌剧团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几个世纪以来,同性恋不仅受到宽容,甚至因为其象征了一种更为纯粹的爱情而得到鼓励。
以斯巴达和普鲁士这两个最显著的代表为例,同性恋是武士传统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成为出色的军人,至少人们希望如此。在镰仓时代,武士的势力盛极一时,女人被贬低为下等生物,是用来传宗接代的“借用的洞”。只有男人之间的爱情才被认为配得上真正的武士。
到了江户时代早期,也就是17世纪初,仗打完了,狼烟散尽。两个半世纪的幕府统治带来了和平,但武士们也因此郁郁不得志。除了教训教训个别无耻的农民或商贾外,他们几乎再无用武之地。然而,理想中的“武士道”在完成其使命后依然绵延许久,并继而进化为一种风流倜傥的做派,其中包括了男男之爱和对美少年的迷恋。
这种情况像极了中世纪才出现的骑士精神,后者也是骑士们无所事事,终日只能在马背上比试枪法和追求高不可攀的贵妇之余才蔚然成风的。
折磨人心、没有结果的爱情被看得比什么都要纯洁。借某位末代吟游诗人的话来讲:
如今我看着受过甜蜜创伤的爱情,
正带着结出的果实一点点地消逝。
武士间的同性恋(“少年愛”)也许是日本人所拥有的最接近西方浪漫爱情理想的事物。
大岛渚 《御法度》
《叶隐》这部讲述武士道德的18世纪作品颇具影响力,它教导道:“一旦(向男孩)表白,这份爱情就会失色。只有将秘密压在心底,带进坟墓,这才是最高贵、最圣洁的真爱。”
三岛由纪夫就此撰文道:“美少年象征了完美的形象——他就是单相思这一理想的化身。”这种说法同近松作品中以殉情告终的炙热情欲很不一样,同有着金子般内心的妓女的母性情怀也是大相径庭。
毫无疑问,同性恋者的骑士精神,就像骑士对他们心上人的爱一样,是以自我奉献为基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日本,是以死为基础的。由于再也无法在战场上证明一个人忠诚与否,殉情的理想便取而代之。这与近松的殉情戏不同,因为在他的笔下,死往往是恋情为社会所不容时的唯一出路。相反,在男同之间,死更象征着十足的忠诚和荣耀——至少人们是这么看的。
大岛渚 《御法度》
有关美少年效仿前辈以各种方式切腹自杀的故事可谓不胜枚举,其中一种痛苦万分,死者要用刀在肚子上割出朋友的名字。这种自残做法实际上恐怕十分罕见,但故事之多说明了理想之强大。
这种理想至今依旧存在,只是其形式多少已改头换面。诸如高仓健和高桥英树这样的黑帮片主人公(他俩的黄金年代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很接近理想中的美少年:年轻、英俊、心灵纯洁、孝敬母亲——尤其是高仓健,总把母亲挂在嘴边——真诚得叫人吃惊,单纯得惹人怜爱,而且还充满了日本人所谓的斯多葛主义,即他们舍弃了对异性的爱。
高仓健《追捕》剧照
不爱女人,则彼此相爱。他们几乎千篇一律地在与占压倒性多数的敌人做悲壮的殊死一搏时双双殒命,通常,也只有在这种性高潮般的结尾,观众才能看到他们幸福的神情。一部由高桥英树主演的电影片长九十分钟,前八十分钟里,主人公一直是郁郁寡欢,哀伤,低落,陷入深深的迷茫和绝望。他天性中的诚挚和单纯质朴遭到了万恶世道的压抑和践踏。但在最后他终于迎来了救赎:他被获准赴死。
他和好友,另一位忧郁的亡命徒,面对着占尽人数优势的敌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录音带上的主题歌越来越激昂,两位英雄互相逗笑,尽情地嬉闹玩耍,仿佛是去赶集的学童。他们边笑边褪下和服,露出骇人的刺青。两人冲进敌人的老巢,在无所畏惧地疯狂砍杀了约五分钟后,双双半裸着身体、浑身是血地栽倒在泥土里。他俩手挽着手,用沙哑的嗓音最后一次互诉衷肠;他们终于收获了幸福。
上述文字旨在说明,日本的同性恋武士精神传统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性恋色情的影响至今在日本的流行爱情故事中依然十分明显。当然,对美男子的迷恋并不局限于日本少女和以同性为恋爱对象的人。美少年的理想同艺伎和“女形”一样,均在日本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三者是存在关联的。
鳥居清廣 画/浮世絵 (1750年 - 1760年頃)
女形:歌舞伎中男扮女装的艺术,想要模仿的更多是理想化中的女人。
3.
迷恋“美少年”的终极意义就是崇拜死亡
作家野坂昭如尝言,一位真正的“女形”演员身上必须有一股邪气。或许因为其脆弱性,纯洁的少年形象会让人感慨世事无常,也就联想到死亡。根据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1971)能在日本长盛不衰,绝非偶然。
《魂断威尼斯》剧照
在歌舞伎舞台上,饰演美少年的是“女形”,正如彼得·潘的扮演者历来都是女伶一样。以下是三岛由纪夫在一则短篇小说中对某位传统“女形”的描写:
增山感到……有股黑泉一样的东西正从舞台上这个人的身上喷涌而出,他是如此温和、脆弱、优雅、娇柔和具有女性魅力……
增山觉得,这是一种奇怪而邪魅的存在,是演员最后一丝感染力,是一股诱人的魔力,让男人误入歧途,使他们溺毙在片刻之美中。这一切,正是他所察觉的这股黑泉的真实本质。
三岛在他名作之一的《禁色》中塑造了邪恶美少年的范本,一位同谷崎润一郎笔下原型相似的男性版“奈绪美”。悠一是完美的男性艺术品。一位厌恶女人的老作家教会他如何佯装感情,虚情假意地去爱女人——“扮演他人是创作的最高境界”(三岛语)——目的是打击她们。他既美得天然,也假得到家,和“女形”的美是一回事。可是这种美无法维系长久,这恰恰是其意义所在。
同性恋问题学者兼专家的稻垣足穗曾写道:“女人的美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有味道,而少男的生命仅如夏季里的一天,是花开的前一天。下次再见到他时,他只不过是一片枯叶。他一旦长成男青年,散发出生殖器的味道,一切就都完了。”
在《男色大鉴》(1687)中,西鹤写道:“要是少男能永葆青春,那可真是好极了。远州这个老淫棍过去常说,少男和盆栽应该永远都不要长大。”日语里的盆栽指的是人工栽培的矮树,在幼苗阶段因为受到折压和弯曲而停止生长,这一审美符号有时也被拿来形容日本人自己。
总而言之,盆栽同将青春定格在纯真瞬间的梦想必然有所关联。然而,不同于只要医学条件许可便竭力维持青春假象的美国人,日本人总体而言较为有风度地接受了青春短暂的本质。事实上,青春之所以美,正是缘于其短暂。在日本,樱花的花期只有一周左右,“樱花热”和迷恋美少年是一个道理,二者还常被拿来做对比。
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死亡崇拜。按照《叶隐》的说法:“迷恋少男的终极意义就是崇拜死亡。”西鹤的某部讲述同性情爱的作品开篇写道:“最美丽的芳草和树木因为花开得绚烂多姿而枯萎衰亡。而人类也是一样;许多人香消玉殒,是因为他们太美了。”
同一则故事里,年轻的主人公身穿绣有秋花的白色丝绸和服,自语道:“世间的美无法长久。我很庆幸能在自己芳华绝代、容颜尚未像花朵般凋谢前就死去。”说罢便用匕首剖开了自己的肚子。不管人们如何解读三岛死时极为困苦的表情,他在做出惊人的自杀之举时,脑海里一定闪现过类似的想法。
同理,在大好青春年华便一命呜呼的神风飞行员也会激发大众的想象力。漫画和电影依然对他们大加歌颂,他们也总被人比作樱花。一点不假,载着他们撞向美国战舰的“爆裂的棺材”就叫“樱花”。其留下的诗文和歌曲也充满了樱花的形象,比方说下面这首俳句,作者是即将最后一次踏上征程的二十二岁神风队员。
最好我们凋零得,
就像春天的樱花,
如此纯洁和绚烂。
死亡是保障青春完美无瑕的唯一纯洁和恰当的结局。史籍、传说和现代流行文化中的美少年主人公几乎都难逃一死。还是以少女漫画为例,当代美少年的一个典范名叫安吉勒斯(Angeles)。他其实是个很具日本特色的主人公,尽管长着一头金发,且一半是人,一半是吸血鬼(人的那一半源自其“神之后裔”的父亲,另一半则来自其德国的母亲,是她给了他“不洁之血”)。
唯一懂得安吉勒斯纯洁和美丽的是个“热爱海涅、拜伦、莎士比亚和爱情”的女孩。她的母亲是个恶人,故事的结尾处爆发了一番可怕的争斗,冲突一方是恶母和警察,另一方是女孩和安吉勒斯。美少年吸血鬼死在了心上人的怀抱里,眼看着他的城堡被一团超现实熊熊烈焰所吞噬,临终前吐出一句痛苦的遗言:“城堡是我们的青春。”
大岛渚《御法度》
【相关图书】
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伊恩·布鲁玛 著
《日本之镜》通过对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和神话传说鞭辟入里的分析,剥开附在日本文化表面的层层面纱,解释日本民族这些两极又矛盾的文化特性,同时勾勒出日本人如何映照出自身的样貌。
无论是黑泽明的电影、三岛由纪夫的小说、文乐《忠臣藏》、宫本武藏的传说,或是黑帮片与家庭剧,伊恩·布鲁玛都信手拈来,幽默风趣地探索有如镜子般反射出现实的戏剧性幻想。他对日本大众文化中病态怪诞的行为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让读者能理解这个被迫温文尔雅的民族如何借由“人为”的风格化与仪式感,寻求压抑自我的解放。
转载:请联系后台
商业合作或投稿:[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