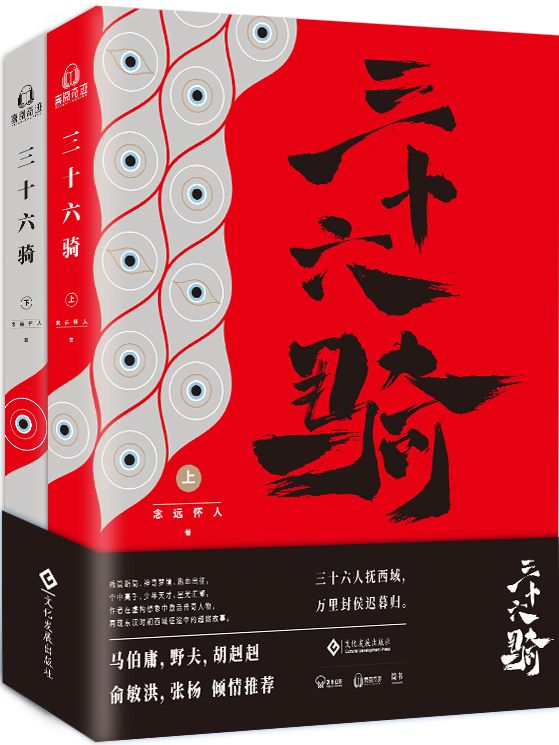文 | 阿改
《三十六骑》的作者念远怀人,早年曾患失眠。
似乎是大学肄业后,做着水电装修工、小餐馆老板或在草创的报社里做记者的某一个阶段吧,睡不着的那些光景,他就没日没夜地看书。文学、历史、哲学,杂书、闲书乃至辞书,都囫囵吞枣,就着夜色咽下去。作为一个美术生,念远怀人本有很大的几率成为艺术家,但却因了梦和书,从此转身成为一个文化人。
因此多年后,当他写下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十六骑》,并让主人公——东汉史家班彪之子、班固之弟——班超也患上失眠症时,这一安排可谓毫不令人意外。
偶尔入眠时,班超会看见无尽的文字行住坐卧,排列组合成一出出诡谲多变的剧;剧虽各有其故事,然而其背景嘈杂喧嚣,语义不明,仿佛一个个来自上古的谜。
那些谜——譬如老子为何要西出岐关,出关后又如何?譬如天地交接之处何在?是在昆仑山吗?西王母又果真是何人?诸如此类。
我有个私见——书中这些梦,才是念远怀人隐藏在史诗般瑰丽的小说背后真正想说的话,哪怕是梦话。
念远怀人的确在小说叙事之始就从梦里开始切入谜题——那时候班超正担任兰台令史,有一天他在梦里问老子,为何要西出岐关,老子对他说:东极到海,西方却没有尽头,天下之大,远超我们的想象。
接着老子不无惋惜地说:……只是上古颛顼帝绝地天通后,你们的视野愈发小了,不识天地,天地也视尔等为刍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上的这句名言,今人多半以“宇宙”视角来理解它的意思:放到宇宙的尺度里,世间并无一物值得特殊对待;但念远怀人恐怕有别的想法,因此在梦见老子不久后,他就让班超与兄长班固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班固:“……你将自己埋首在上古的残篇断简、诡异传说之中,实在有违史家传承。”
班超:“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史家传人。”
班固认为,“史家立言,首推一个信字”,而班超依凭的尽是飘渺虚诞之残章断句,能有什么建树呢?对此班超不以为然地回应:“立言当然重要,立行更不可废”。他甚至觉得,兄长与父亲虽为史官,但却与儒家“没什么两样了,还算史家吗?”
“倒回去看,我史家的前身,本是天官,通星宿天道之变,现在却失落了,给帝王记记信史而已。史家现在的荣耀最高就是助帝王封禅泰山,其实颛顼帝绝地天通前,神山当是昆仑……”班超接着说,“或许昆仑才是我史家所宗的源头。”
与班固“天道已远,庄敬便是;人道在侧,更当躬行”的立场不同,班超的梦想是去探一探那个“天”。这一内在驱动力,加上外在的理由——东汉皇帝梦见西方金人、因此特谴班超出使西域迎接西方神仙以求长生不老,促使班超最终率领三十六骑,一路向西。
《三十六骑》毫无疑问是一部顶级好看的类型小说:神话、历史、军事、外交、武侠、玄幻乃至同人,诸般要素多样风格都被念远怀人揉杂为一体,变成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探险故事。单看这三十六骑的组成就知道有多过瘾:内里有羽林军的神箭手和骑兵陆战队,有剑家天才少年带领的剑侍,有纹身打铁、精通奇门遁甲和机关布阵的墨家弟子,有盗跖传人、易容有术的神偷,有驱虫下蛊而又风情万种的毒手寡妇,有望气之神通的妹妹班昭,还有一个贵霜异族圣女——其名“仙奴”实则来自作者那只通体白毛、一见来客就会飞速窜消失的猫。
念远怀人的这部小说,还是“借壳”讲古。史书上载,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大胜敌军后,另率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诸国。斩杀匈奴使者、令鄯善王归汉;降服于阗,疏勒废王,大败大月氏,平定龟兹、焉耆等国,打通西域北道……《三十六骑》大体不离这一史实框架,不过,如前所述,值得留意的仍然是故事的“言外之意”——那是最值留意的作者的“梦话”。
让我们来继续讨论“史家”这一问题——离开莎车国,前往疏勒的途中,三十六骑遭狼群追击,最后被困在麦田怪阵中,濒临绝境时,班超与书中第一反派鱼又玄通有一番“知识考古”般的对话。
按照鱼又玄的说法,其祖上亦是史官,殷商时纣王暴虐,史官出逃,除了鱼氏,其他各家诸如尹氏、微氏和班氏都投奔周文王。从周武王灭商,连春秋战国浩浩八百年,史家辗转流离,史学终于式微。对此鱼又玄有何评价呢?听听他的话,不得不承认有点意思:
“……我们史家是解天命的人呐,结果各氏要么惨被暴君屠戮,要么成了给君王说漂亮话的弄臣。”鱼又玄眼里竟迸出泪来,也不擦拭,“这天下可能不再需要预言苦难和灾祸的人啦,可是史官就是这样的猫头鹰,啊啊啊地叫着晦气,惹人讨厌。”
他进而问班超:“你知道鲁国的史书叫《春秋》,而楚国的史书为什么叫《梼杌》吗?”
“梼杌”为断木,断木上有年轮,以“春秋”和“梼杌”为史书名称,其旨皆与时间相关。但鱼又玄却引“梼杌”之古意申之:“梼杌其实是密林中的凶兽,永不可被驯化,所以才被人讨厌。但这才是史书的真正意义!”
在念远怀人的笔下,这个有着侏儒形状的鱼又玄算不上一个卑鄙小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其悲剧在于——如果与班超相比的话,鱼又玄偏执地以天官自居,相信“天命”的唯一性和必然性,因此凭着一则史家的谶言,就断定班超是七宿中的角宿凶星,班超西行,就是应了上天的预言,开“天门”,要给天道带来大难。以“匡复天道”为使命的鱼又玄因此认为,班超非死不可。
班超真的是凶宿吗?作者当然要为他辩护一番。在后来的一个梦里,班超问父亲,自己是不是凶宿,后者沉默半响后告诉他:“你是歧路。”
班彪对儿子说道,世间每一个人的历程,都像一棵树。从根部出发,走向躯干和枝桠,每到一个分叉,你都得做出选择,而无论选择哪边,都意味着你会错过另一边。如此不停地走,不停地选择,你会觉得命运是无端的,一切都是偶然,“可是有一天,你老了,像我这样,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往来的路上看,会发现有一条清晰的路线,必然让你回溯到出发的根部。那时你会觉得,命运是注定的,一切都是必然的”。
他说——这个时候我们所听到的也许是念远怀人自己的声音:“我们史家,就是在路边回望过去的人,用笔记下人类那命定的路途。可是未来,满是歧路,任谁,用笔也捕捉不到。”
历史和命运都是歧路,也是变数,选择的和错过的,永远一样多。因此历史没有真假,只有对错——念远怀人借班彪之口质疑历史的客观性,但毫不怀疑历史学的价值立场——没有价值判断的史家,又何以当得起史家这一“天官”之职呢?写到这里,几乎可以想象作者会用他习惯的拆字法来解释“史”的本意:按《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又”为持笔记述之意;“中”,“仲”也,正也,仲裁决断之意。
然而,如果对史家的讨论仅止步于“仲裁者”这一层意思,念远怀人显然不会满足,《三十六骑》也不足以成为一部以虚构求真实的魅力之书。在后续的剧情里,念远怀人让班超那个拥有天眼通能力的妹妹班昭,去建构这一庞大命题的另一半。
众神借以上下天地的天梯“都广”,日落棲止之处“虞渊”,垂荫四极的“寻木”,《山海经》里的大鸟“嚣”、守玉兽“狰狞”,“其力不能胜芥”的“弱水”,乃至西王母神国,都在稍后一一现形出场。也亏了班昭,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建在“百仞无枝,立而无影”的天下第一大树“建木”上的西王母神国,以及言语不足描述其艳绝之万一的九天玄女。
再一次,写作者借剧中人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按照九天玄女的自述,她是天地母神西王母在世间最早的成象女娲,后来女娲成象出伏羲作为自己的对偶神,女娲为巫,伏羲为觋,前者造人,是巫统的开端,伏羲画八卦,遂成史统的开端。
诚如班昭所疑惑的,八卦不是占卜之术吗?如何能算是史统的开端呢?九天玄女回答:“巫是感应,直接通达;八卦是数理推演,想制定占卜的公式,其实算作学问和记录了,这记录便是史统的萌生。到后来史官仓颉造字,只是八卦的余荫。”
到此,作者进一步揭示出“史”的意思:史,就是记录、文字、知识和积淀。伏羲史统这一脉之所以越来越强大,是因为文化可以积累叠加,而颛顼帝斩断建木、绝地天通后,巫史两脉从此分离。就像九天玄女所说,“巫是难以琢磨和窥探的,史却是可以看见和理解的”,因此巫的失落,在所难免。
不仅九天玄女,被念远怀人搬出来当“解说员”的还有老子——骑青牛西遁后,他果然是去了西王母神国。老聃对班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实有别的解法:“这一是西王母,二是女娲,三是伏羲。不是伏羲造了万物,而是他命名了万物。这命名便是知,便是动,动便牵及万物。西王母,包括女娲或九天玄女,代表这生死两端,起点和终点。伏羲却昭示了期间的过程。”
在老子看来,不敢玄思起源和死亡的孔夫子虽然过于迷恋出生入死这一过程中的进退和平衡,但也自有其道理。“巫史分离后,史定过去,巫判未来。史要评对错,巫却无是非。……巫的内心是恐惧,史的本质是敬意。”为梦魇所困的班超,其实正在巫史之间,为两种道统所撕扯,不得安宁——如此来看,这是班超眼前最大的歧路,也是横亘在作为统一体的人类面前最大的歧路,只不过,以今日的眼光回望,“人”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选择了哪个方向,答案已不言而喻。
这是巨大的错误和遗憾吗?作者没有下论断。在小说的最后,他再次借班超解梦,给这个悖论作一开放性的结语:
“我在梦里,父亲老跟我说一句话,说没有真假,只有对错。我一直不明白,现在好像有点理解了。真就是实在不虚的存在,老子说过,如果人只认实在的事,或许以后就会出现臣杀君,子杀父的情况……其实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会识别真实,而是偏偏把好似虚无莫名的东西,当作对的。只有人能如此,做着许多无聊无益的坚持,只因认为是对的。若不如此,我们真成了天地之间的刍狗了。真假无情,对错是情……也不知解得对不对。”
跳出来看《三十六骑》,其叙事其实有三条线索:出使西域、驱逐匈奴、平定诸国、重开丝路是“表”,巫史之辩是“里”,但在这一表里的互动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
在西王母神国,不识老聃的班昭问他是不是仙人,有着少年容颜的老聃说,自己不是仙人,而是“散人”,“就是局边人——不在局内,也不在局外”。私揣之,这是作者以蜻蜓点水之笔,表述了他对道家的看法。可是,真正的第三条线索,不在道家,而是释家——东汉明帝为求长生,遣使西行迎梦中的仙人。但东渡而来的,不是仙人,而是“佛”——经班超一行护送抵达中土的大比丘所传的佛法,其影响远甚于重开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正如护法者法兰对跟墨家传人齐欢所说的,佛法东渡,是要给中土带去“浮屠之眼”,“我们此行,就是想让汉地的人可通过此眼,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念远怀人曾说,《三十六骑》是用想象力,还原一个神话与历史尚未完全割裂的时代,是“在历史的规定动作间,恣意秀一些自选动作”,那是游戏,也包含了一点解释的野心。三十六骑一路西行,“他们只是蝴蝶振翅,却改变整个历史”。这是念远怀人——曾经的失眠症患者想象瑰丽的梦游记,也是他游离于春秋之外的春秋大义;是人类过往之“命”的休止符,也是人类未来之“运”的待续的开始。
任谁能想到,一部以好看为鹄的的类型小说里,能藏着这么磅礴幽深的见识和世界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