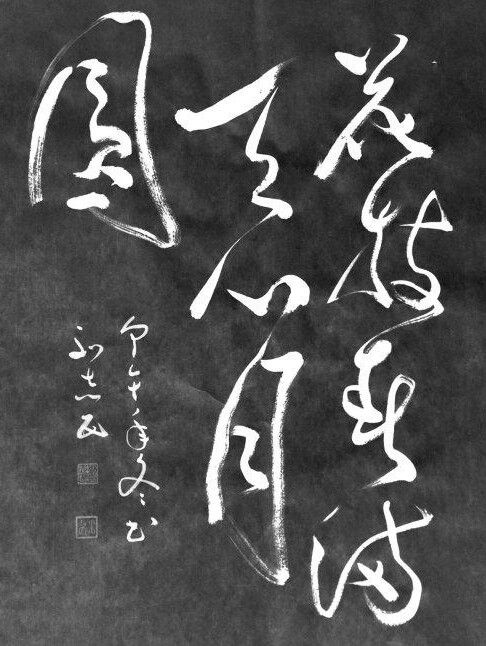一
昨夜我忽然梦见了燕子。在梦中我仍像少年时一样,怀揣着刚到手的某个奇思妙议,一派欢喜雀跃,眉飞色舞地跑去她面前,献宝般地说:“唉呀,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叫熊逸的家伙,写的书当真有趣极了!”。
甫一出口,梦即醒来。
醒来,窗外月光皎洁,超然清冷,前尘往事若隔世,遍洒大地,漫上心田。
有些人对我们的一生有重大的影响,可奇怪的是,他们就像航行于暗夜大海上忽然出现的烟火,半空中砰然一响,光明大放,华彩烁目。眼前蒙昧脑中混沌均为之开,事无巨细都是纤毫毕现地清澈,仿佛第一次张开眼睛,懂得何为之看。
烟火转瞬即逝,刹那光明仿佛只是一场幻觉,幻觉中让人看清方向,明灭间让人依稀有所悟。
对我而言,燕子正是这一场光明烟火。
燕子是我的中学同学,标准学霸,尤其数学,初中时代一直霸居年级第一,是数学老师眼中无法掩饰的最爱。而彼时的我,懵懂未明,成绩单如心电图,起起伏伏的线条和农民伯伯的收成一样,时而神憎,时而神助。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两个世界的人,井水不犯河水,但恰巧分在同一个宿舍,于是,每晚的卧谈会,让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初中的小屁孩会卧谈什么呢?大千世界,无限好奇,高深一点的胡扯红楼梦胡扯红与黑,但我猜,没几个会去胡扯黑格尔吧,那个政治课上用于批判的辨证唯心主义白胡子老爹。我当然不记得那些卧谈会内容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听她胡扯黑格尔时心中泛起的诧异与好奇:她为什么会这样想呀?黑格尔到底说了啥呢?
对一个智商只属正常的屁孩子来说,黑格尔再让人好奇,也仅限于好奇,第二日起床铃声大作时,无论前一晚多么激动人心的胡说八道,脑后就是九霄外。
转眼初中毕业,转眼高考结束。她发挥得不好,只上了大专,而我,怀揣着隐秘的小得意,一门心思地想着终于可以去把鱼鳃放入人体,造一个属于我的麦克·哈里斯。嗯,他将不是来自大西洋底的人,而是游往大西洋底的人。
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是另一番天地,忙着解剖忙着实验还要忙着恋爱,各种梦要忙,当然梦醒后的失望失落与迷茫更让人忙。我们没有联系,一直到大学毕业重聚家乡,才又一次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仿佛四年从未分开,谈话从未中断。
一个正常智商的人会在什么时候迷上艰深的哲学呢?一要衣食无忧,二要诸多闲暇,三要心生迷茫,尤其迷茫必得足够深,头脑中充塞无数的为什么,挥之不去,无法以诗化解,无法以歌驱散,唯其如此,三颗龙珠集齐,哲之大神可招唤。
彼时混进大学教英语的我,不仅集齐三颗龙珠,更有燕子在旁巨大影响,从此哲学类书籍居然占据自家书架半壁江山。
从攀枝花教育学院到攀钢自动化部差不多45分钟距离:出教院步行10分钟,乘车,至大渡口桥转车,车过桥后继续坐两站,下车,步行10-15分钟,就是她家所在的小区。傍晚时分,她常常会出小区来接我,我们会先去旁边的铁轨道上散步,月光沿着铁轨一路叮当跳跃,融入茫茫夜色,江风把思绪顺着飞扬的发丝吹向浩瀚天际,是的,这是当年我最熟悉也最喜欢的一条路,一周行过数次,熟悉和喜欢得和回家的路一样。
奇怪的是,自从离开攀枝花,我居然从未想起过这条路,当然,除了已化为警言金句的只言片语,我也完全不记得当年我们都热烈地讨论过什么,直到近日读熊逸的《周易江湖》 ,读到梅花易数,读到天地人三才,读到取55而49,6,7,8,9,老阴少阴老阳少阳,变爻变卦……
我的个天!我居然完完全全不记得我曾经钻研过这么玄之又玄的东东!当年我们都在看些什么呢?当年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呢?
果然,最是荒唐数少年!
二
现在想来,有好些书如果不是因为她读过,恐怕我永远都不会去读,例如《周易》,例如《金刚经》,例如《坛经》,还有那些玄虚好玩的机锋公案。
因为知道她的作息,所以有时我会不告而至,某个傍晚又是如此,兴之所至,我跳上公车跑去江对岸。行至小区门口,天已擦暗,见她正缓步行来。我开心地迎上去,不无诧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呀?”
她说:“我算了一卦,说你差不多该到了。”
我自然讶异不已,难道《周易》当真如此了得?
虽然早知她在看周易,但那玩艺儿对我而言,实在是太过艰深又不知所谓,除了摆在书店最高处,每每经过时合什拜拜,我恐怕永远都不会去碰,不曾想《周易》可以如此神奇,竟算得出我自己前一刻都不曾动的心思,于是乎,我自然跟着狠啃了好一阵子。
如果你问我看懂了吗,也学会卜算别人自家都不明的心思了吗?老实说,我真没看懂,当然也算不出。可如果你问我可以摆摊算卦收钱了吗?老实说,只要我舍得下脸皮,还真不是问题。
可我当年竟然从来没想过更没去问过她:“你是怎么算出我会在那一晚来看你的呀?是哪一卦哪一爻?辞上又是怎么说的呢?”
你看,我们对自己年少时就祟拜不已的偶像总是很难做到平视,对方随口一句玩笑就是金科玉律。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我当时想得到去疑问她如何占得出那一卦,估计回应我的也是一记爆栗而已。打机锋时,我的脑门上可真没少吃。
彼时她好国学,如今细想,我们那时感兴趣的书重叠处并不多,而有重叠也大多是我追随而读。我读的最后一本古书是《老残游记》,映像之所以深刻,一是文字当真优美,二是看得我真想吐,不是修辞上的想吐,而是生理上真正地想吐,由此可知刘鄂文字何等传神。读罢此书,我对国学再兴不起任何兴趣。
多年后当读王小波《关于幽闭型小说》,我才明白何以文字极佳的《老残游记》却看得我想吐不止:“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
三
《生活大爆炸》里有一集谢耳朵决定离家出走,死党莱纳德前来送行,临别时终于鼓足勇气抒了一把情:“Hi,我会想你的”。谢耳朵回道:“你当然会想我的。”然后一脸诧异与不耐烦:这么显然的事实,你干嘛陈述它?有什么意义?你太奇怪了,不要说这些废话,浪费时间。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鼓足勇气也抒一把情,估计燕子也会这样回复我吧。
在我和燕子的关系里,我是莱纳德,是华生,是黑斯廷斯,是凡人;她是谢耳朵,是卷福,是波洛,是精灵。智力太过发达的人看到的世界总和我们这些正常人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毕业回攀三年后,我又一次离开了家乡,这一次我不再做梦去造一个属于我的麦克·哈里斯了,我打算老老实实地做个财经人,赚钱看世界。我的一堆狐朋狗友们都来车站送我,她当然没来,也不会来。我们就这样从此分别,仿佛一场谈话结束,各自回家,过几日又会再聚再聊,没什么必要互道平安,甚至没必要互留在人间的联系方式。嗯,仿佛心电感应是每个人都必备的器官一样,精灵们就是这么想的吧。-_-||
只是一别而去的不是几日而是十多年。
2009年老妈诊出癌症,像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我们心神无定手忙脚乱,往日啃进脑子里的书比吃进肚子里的肉还不如,吃肉长肉总能让我们在危急时跑得快些或支撑得久些,书却没能让我们宁神安心,淡然面对生死。
求医问药末路处,总是神佛。听一直在攀的同学说燕子早就皈依了,且一直在藏区修行,当晚恰好她们约了撸串,不如三家一起相聚。同学说她先生是孔圣人家族的第N代子弟,平时在广东这边打工,她们母子在藏区,儿子比同学的女儿略长一岁。
待得她们一家到来,十多年未见,仍能一眼认出,只是原来略显孱弱的她,现在中气十足,面色红润,眉宇颇为疏朗,原来让人觉得清冷孤傲有些拒人的一身书卷气,仿佛消失了,但又没染世俗味。她先生果然一派温润,着衬衫长裤,却让人恍惚着的是长衫,安静地一旁微笑撸串,偶尔招呼一下儿子,颇为自如。儿子却虎头虎脑,野性十足得很,也灵性十足得很,当初就常听她说天生之人天养活之这些玄论,如今望去,确实不同那些长于家宅中的小儿。可惜小子恰是初慕少艾的年龄,一餐饭把同学的小女儿欺负得嗷嗷直叫。我们就在这嗷嗷不停的熊孩子嚎叫声中,终于再聚。
一别十多年,往日的交谈却仿佛从未中断。得知我母亲情况后,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你相信因果吗?”
没有寒暄,也无例行的惊讶叹息与安慰,仍和以前一样,直击问题关键。这让早已习惯了例行前奏的我,一时张口结舌,不知从何作答。
转眼十多年,我几乎忘了如何直截了当地谈心。在直击人心前,我们总要周旋周旋再周旋,甚至周旋到忘却原本的目的。我以为自己终于成熟了呢。
多亏旁边嗷嗷直叫的熊孩子们,讪讪半晌,我终于重拾昔日谈话的方式。我老实地告诉她:我不知道,我啃过的佛学书早已忘爪哇国了,就算残留的几个概念和结论,也只是半信半疑。什么叫因果呢?蝴蝶一振翅,千万年后千万里外浪涛天,从理论上我当然是信的,但身处惊涛骇浪处,除了咬牙硬捱,又能怎么化解?信,就真能逆天重回当日,摁住了那对扑闪的蝶翅么?只要时光不可逆,生命的轨迹又能如何画圆呢?画不圆,佛理的逻辑又如何讲得通呢?更何况,若再细析,千丝万缕交织而成的一个matrix,怎么拆解?能拆解吗?作为信仰作为警醒甚至作为抒怀寄情的诗,神佛当然是可信的,甚至可朝夕相伴,但作为逻辑,可以像1+1=2那样依持吗?偶然和必然到底是智者了然于心,手中闲暇把玩的骰子,还是我们这些愚人心中因妄而生的痴迷呢?
好吧,尽管当年脑门上被敲了无数爆栗,我仍是未开窍的那头蠢牛,悟不得也,悟不得。
旁边的熊孩子真讨厌啊!即或我们仍如往日般直言不虚,交谈也只能时断时续。不过无论真信还是不信因果,到得此时,我也只能选择信。喧嚣声中我们约定第二日去庙里祈神祷福放生,总之做足一切可以做的封建迷信活动。
第二日事毕,互留电话,尘世缠身各自忙,我们再无年少清谈的时间,从此又是分别。
一年后母亲过逝,电话告诉她结果,然后以母亲的名义捐了些书,只是是给她所在的藏区学校,还是另一位信众的学校,当时诸多繁杂,却是记不得了。
换手机时总会整理通信录,每每看到她的电话,难免会停顿片刻,我从未打过去,当然,我也从未接到过。昔日一周数次,步行转车再步行,折腾近一个钟,仍乐此不疲;今日电话就手,却是觅路而不得。
太白吟月: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其实何止人月如此呢?翻开大数据,世上有多少自童蒙至白首仍相随的友情?成长总是移步换景,因缘方得聚,刹那已明灭,长歌唏嘘感伤意,本是人间寻常见。
这一回,我算得上是了然必然的智者了吧。
四
近日读《周易江湖》和《八戒谈禅》,常常惊叹不已,时时捧腹不止。
夜来因之成梦,在梦中我仍像少年时一样,怀揣着刚到手的某个奇思妙议,一派欢喜雀跃,眉飞色舞地跑去燕子面前,献宝般地说:“唉呀,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叫熊逸的家伙,写的书当真有趣极了!”。
甫一出口,梦即醒来。
窗畔伫立良久,如果回得梦里,我会说什么呢?我想我会说:不过,我们先别聊这些书了。告诉我这些年你的生活吧,告诉我你走过的千万里路,告诉我你每一日的点滴日常。这,才是我最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