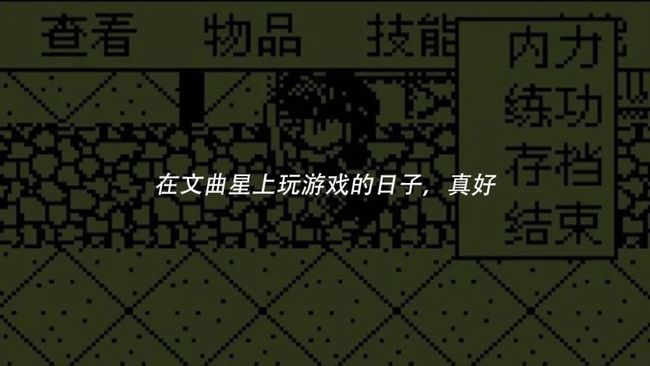“做自己喜欢的游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点击上边的“机核”关注我们,这里不止是游戏
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从一个玩家,到一个游戏制作人,将近10年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这是雷亚游戏过去十几年里的轨迹——但他们又不仅仅将自己视作一个游戏的开发商,而希望将创作的触角扩散到每个可能的地方。
所以,我与Gulu之间的聊天并不像是一次采访,更像是两个玩家对于自己游戏经历的交流。
“我是被人从街机厅里捡到的游戏制作人”
多年以后的某个下午,当Gulu坐在北京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面对我时,他首先想起的是差不多10年前在台北街头的机厅里和游名扬的对话。当时他是一名狂热的音游玩家,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游老板的猎物。
彼时的雷亚游戏尚未成型,旗下的第一款移动端音乐游戏《Cytus》正在开发之中,游名扬和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在寻找着那些“懂得音乐游戏又希望能够参与其中”的玩家们,希望能让他们加入这支前途未卜的新军。
工作照,黑衣者为Gulu
今天,雷亚游戏已经成为了华人游戏圈中的一面旗帜,出品的游戏也跨越多个平台,而当年那个用攒起来的硬币去出勤的小玩家Gulu,也已经成为了《Cytus II》的制作人——唯一没变的,还是那颗玩家的心。
我可以说是被游老板从机厅里捡回来的一个游戏制作人吧。十年来,其实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就只是不断地学习,学习怎么做游戏,学习怎么更好地做一个玩家。
移动端的游戏与街机游戏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是好游戏,终究都会获得人们的认可。
“讲一个好故事,是我们做游戏的方法”
就像人的性格不同,游戏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在制作《Cytus II》的过程之中,Gulu得到的并不仅仅是管理能力与技术上的进步,更多的是一种感性上的体会:
游戏中的温度,从开发伊始便存在着,如果作为制作者都无法体验到那种情感,那么这个游戏必定不会让那些期待者们满意。
《Cytus II》的前期是跟日本团队合作进行开发,我们(雷亚游戏)这边主要的配合方式都是远程合作。
每周一次的视讯会议,我身在台北和东京的开发团队沟通,在交流成本上存在一些天然无法克服的困难。日本团队非常敬业,也尽力配合我们的需求,但是在合作的效率上终究不是那么顺利。
因此,后来我们最终决定将项目的全部工作迁回到雷亚总部进行开发,那时候我才有一种感觉:“啊,身边就是开发的同事们,这个感觉才对。”
音乐游戏开发团队
作为一名游戏开发的老兵,Gulu虽然年轻,却已经历过雷亚游戏几乎所有上市游戏的研发工作。
《Cytus II》本身作为续作,其要求不仅仅是“优秀”,更需要让前作延续下来的那种“味道”成为自身传承、玩家认可的核心体验。
如果你问我远程协作与在本地开发最大的不同体验是什么,我觉得可以说是“默契”。这种默契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大概让我去描述的话,就是“共同的信任与期待”。
我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游戏制作人,但是我觉得,作为统筹整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最难的部分其实并不是那些技术上的东西,而是让一个团队里不同岗位的同事们明白: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每个人对于这个目标的理解都不同,但是要让这个愿景尽量的相似,并让最终的成品被每个人接受,这就是游戏制作人或者说项目管理者最大的使命。
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他们对游戏一定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想法,这时候倾听团队成员的意见相对重要,但这些想法与目标是否能实现的实际层面,跟团队成员的讨论也是相当重要,因为这个都关系到资源跟成本的问题。
在大家有共识的情况下,美术画一张图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有因为有共同目标在心中,而将这张图表现的更有感情;
在做程序设计的时候能够预想到游戏内的结构,未来是不是有什么扩展的空间,他们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能够尽量的去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理性地理解感性的美好,是做起来难、说起来更难的事情。Gulu依靠的是雷亚游戏自身基因里最擅长的方法:给团队里的所有人讲一个故事(字面意义)。
《Cytus II》的一个制作里程碑,是我们的一次“讲故事大会”。
我们的游戏策划与核心设计师,上台来向下面排排坐的所有成员把游戏的故事完整地讲一遍,包括起点与终点、剧情走向、角色的命运等等,这里面甚至会谈到角色性格与一些细节的呼应,这些内容往往也会被在游戏中还原出来。
各自岗位的同事们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就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设计师会考虑UI和美术中配合剧情与角色,加入什么样的描绘;程序团队会考虑到系统的设计方向。
所有的决定都是根据故事的纲领得出的,所有人都会理解到有关游戏走向的决定,其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如果对故事、对于玩家的沉浸感和体验感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不去做它,我们宁可花更多的精力让故事更完善、更诱人。
“吵起来是因为大家彼此尊重”
负责《Cytus II》开发任务的核心团队总共有大约30人。这样一支中小型团队的综合开发,很多时候信息的及时沟通就成为了关键。
Gulu觉得,之前他难以体验到的“温度”或者说默契感,很重要的地方就在于“是不是一转身就能喊到人”。
雷亚自己开发游戏的这种经验其实是比较特色的,或许对别的工作室、游戏开发商并不适合。但是就我自己来说,那种感觉其实是……可以说是很舒服的。
因为这种结构是一个很典型的扁平化结构,彼此之间的沟通非常紧密。
我在管理整个游戏开发进程时,花费最大精力的地方,除了描绘一个大目标——就是前面说到的“讲故事”——
之外,还必须帮助各个职能小团队,将他们的任务分解开,做很多很具体的规划,将“故事”量化成为明确到细节、数量、日期的工作。
将所有的事情都平摊开来,对于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来说可能很残酷,因为毕竟有着时间、人力各种成本的压力,但在我来讲,就必须平衡每个人能够做到的每件事。
包括美术在哪一个部分要出几张图;程序在什么时间节点必须完成什么样的功能;音乐团队要在限期内完成多少曲目的收录等等。
把这些事情一一分解开,不仅繁杂,而且在布置的时候最大的成本并不是“要他们去做”,而是“要他们理解为什么这样做”。
“命令式”地去下达任务可能是完成目标的一个方式,但我始终希望团队里的朋友们能够不断成长起来,对自己有信心,对游戏未来的样貌也很明确。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想要什么”,做出来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带给自己成就感。
磨合是需要成本的。在最开始,很多事情并不能得到统一的认识,不同身份的开发者们也会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观点。
当情绪被摆在桌面上时,理性并未因此退场——恰恰相反,当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时,带有情绪的沟通最终一定会转化为有价值的结果。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表面上来说大家都同意了某个意见,但是空气中有那种微妙的情绪,这时候我会意识到“认同只是表面”,事情的本质没有解决。
所以这时候我会跟同事们说:如果有任何不认同,我们一起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没有谁对谁错,只有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争论了。
我们那边说交流里面有一种东西叫“读空气”,这个事情其实很玄:按理说视频中看到的人和你身边的人并无区别,但是在视频中这些气息会被过滤掉。很多时候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
但如果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退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意见不合不要紧,其实大家想完成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这时并不需要用情绪去面对这件事情,反而是需要倾听跟共同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退一步去思考对方立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建立在团队成员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这里的尊重,不止是专业上的,更多的是将对方看作自己的伙伴、朋友、拍档。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吵起来是因为大家彼此都尊重对方。
每当这种时候,Gulu总会想起自己的“新人期”。他深知每个人的制作经历都是从无到有,都需要不断的认知和成长,才能让自己成为这个行业中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
制作一个完整的游戏,就是一个行业新手从入学到毕业的流程,很多开始时懵懂无知的人,到项目临近结束时已经能够完整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对工作目标的细节考量与量化分配。
这种无须语言描述的默契的建立,经常让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别留遗憾”
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会像预想得那么顺利,《Cytus II》的开发也是如此。这个游戏的故事主线以虚拟社交网络为原型,世界观里的不同角色通过碎片化的叙事串起一个完整的世界。
尽管在初期做过很多考量,但在游戏开发进入中后期的时候,Gulu经过反复的测试与尝试,认为目前的系统无法承载整个游戏的世界观呈现。
而在此时,距离最后上架的Deadline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我们的故事组在《Cytus II》里设计了非常多的明线、暗线与叙事碎片,去满足这个世界观里不同角色的状态。
我们想让玩家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如何通过虚拟网络去交流,通过游戏获取到各种线索,了解到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临发售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反复的评估,得出了一个结论:现有的系统并不能提供给玩家足够的信息量,也无法把故事结构呈现得非常完整。
当时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继续保持现状,之后再打补丁或想办法去解决它;另一种是开发一个全新的系统,从结构上进行颠覆,以便给玩家们带来更好的、更完整的体验。
Gulu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这种犹豫不仅来自于工期、成本以及其他资源,也包括程序组自身面临的压力:如果这个系统无法在时限内开发成功,团队所有人面对的障碍就不仅仅是目前评估的结果。
相对而言,保持现有状态或许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那天下午3点,我们团队一起开会,我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然后说了一句:一个新的系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所有的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大概的意思是我疯了。
然后程序部门那边集体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阵子之后,他们的Leader抬起头来说:我们能开发一个新系统,这样可以让游戏变得更好。所有人又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意思是他也疯了。
那一瞬间我非常感动,我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整体,在为一个目标努力。留给他们的开发时间只有三个月,包括测试等等,可以说是争分夺秒。
但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没有想过推卸责任或者其他的事情,只是希望让最终的目标更完美,不想让自己的工作留下遗憾。
作为一个游戏制作人,Gulu特别在乎的节点就是上架的那一刻。因为无论之后做什么,在那一刻交出的是一份面对玩家的答卷。
有些游戏上架时的内容可能只有30%甚至更少,但他一直希望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实现那些一开始就制订好的目标,尽量不要去舍弃任何我们想做的内容——
因为它是属于团队所有人的思想,所有人都认可的东西一定是有价值的。
Cytus II 游玩画面
尽管中间有很多波折,团队还是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的既定目标。
《Cytus II》上架的那天晚上,所有的团队成员都没有回家,大家窝在公司的会议室里,一起看着Youtube和Twitch上全世界玩家的实况直播。
《Cytus II》作为续集,我觉得可能是我做过最难的一个游戏。
因为制作一个游戏的续作,有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前作的玩家是否能够习惯”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们要继承经典的意志。
但是要将它强化到更高的档次,就再次对自己做一个超越,因为前作它本身是有一个标杆的,那就意味着续作的价值要比之前更好。
所以看到那些抢鲜玩到《Cytus II》的人,他们的反应是很有趣的,他们会直观体验到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亲切、熟悉的操作感,又会不断不断在里面发现全新的元素。
在学习游戏系统的过程之中,他们也没有很多负担——因为经验能够指引着他们不断前进,但当他们意识到我们埋在里面的新东西的时候,又会得到足够的惊喜。
“我有一颗喜欢冒险的大心脏”
如果是在10年前,游戏上架之后或许就意味着使命的完成;但是在今天,对于移动端游戏来说,上架仍然是个重要的节点,却只是一个开始。
让一个游戏的生命周期延续下去,需要更多的智慧、耐心与毅力,内容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只有内容。
游戏上架,其实就像跑道上的发令枪。在枪响之前,调动全身的力气,绷紧肌肉,准备起跑;枪响了之后,那种紧迫感和压力,其实是比之前更加严峻的——
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跑得最快;在努力使用所有资源和办法的情况下,跑得最远;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玩家喜新厌旧的时代里,跑得最久。
现在和我当“机厅小子”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我们是拼命去找新的游戏,而现在是游戏拼命地寻找新的玩家。
我觉得作为一个游戏制作人,考虑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和时间赛跑的不止是开始的创作,还有不断地保持新鲜感,不断地发出声音,让别人知道你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只有这样,才能让玩家始终关注到你的存在。
使用一定的商业策略,和作出优秀的内容并不是对立的,不是说我将精力用在这上面,就是对内容的不负责——恰恰相反,如果不去想办法维持产品的生命力,让团队的创作一下子就消失在资讯的大海里,那才是对创作的不负责。
所以我特别重视对市场的观察和认识,包括游戏的形式、内容导向以及更多的要素,哪些是玩家们当下喜欢的,哪些是能够形成讨论和传播倾向的。
竞品、对位的类型产品有什么样的优势,他们有什么长处是我们可以吸取的,这些都要纳入制作的框架里。我一定是带着理想,去做我的事情;
但我作出的成品,是一个商业作品,那么它必须以非常实际、符合商业要求的态度,来面对市场。
与此同时,随着游戏的不断迭代与更新,来自于玩家的讨论和意见也不断累积起来。
Gulu乐见于这种情况——他经常匿名潜伏在玩家社区里,观察玩家们对于人物角色、剧情走向以及音乐本身甚至是动态效果的讨论。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其实当一个文化产品完成之后,他拿到市面上去呈现给消费者的时候,其实这个作品就不再属于创作者本人了。
它变成了一个所有能接触到它的人共同创作的,或者说是共同支撑它的一个东西。我们只是负责将这样的游戏做出来,但后续的维护和成长,其实是全世界的玩家来共同完成的。
我们也要面对玩家的批评,从故事到人物到系统到付费结构全都有,还包括对硬件不满——旧手机玩起来慢这个也是要挨骂的。有时候一些玩家的批评可能会让团队里的人感到有点委屈,比如说剧情上有的玩家不满,他就来吐槽,在哈啦板上猛批。
但我就还好——或者说我可能有颗大心脏吧,我习惯了。对于我来说,所有的评论都是学习,输入给我一个信息,我自己经过调试之后,再在后续的作品中输出。
学习之后要去尝试,尝试的过程就是冒险,而我作为制作人,必须要承担冒险的收益与风险。团队成员们都很有创造力,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们的想象力得到验证,而这种验证就是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是否快乐,完成之后是否有突破的成就感。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对娱乐的选择,除了游戏之外,实在是太多了。
智能手机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习惯,游戏已经不再是过去一个“PacMan”能玩个三五年的东西了,如果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激发,其实单独一个游戏很难保持足够的新鲜感。
我们能保持与玩家的连接,不但要依靠充分的自信,还是要依靠整个玩家社区,去拿出能够让大多数人认可的作品,让大家保持对品牌的信心,对内容的信心。
“做出一个好游戏,带给我的是自豪的感动”
将游戏的制作过程分解为技术步骤,看起来似乎非常合理,而且这种技术的沉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成熟稳健。
但Gulu回忆起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感觉最怀念的,却还是雷亚最早开发游戏时的那种清晰的直觉。这种直觉贯彻在每一个创意、每一个美术上的想法、甚至每一个音符里,是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激动的指引”。
我有时候会想起《DEEMO》最开始创意阶段的故事。这个游戏是游名扬老板最开始的一个很模糊的想法:一个孤零零的空间里有一个黑色的生物,空间最上面有一扇窗子,会掉下来各种东西。
有一天它掉下来一架钢琴,这个生物就开始学习去弹钢琴;后来它发现琴声可以让一棵小树苗成长;之后又掉下来一个小女孩儿,她很害怕,想回家;黑色生物就想到弹琴让小树苗长成大树,送小女孩到窗子回家。
你可以看到《DEEMO》最后成品呈现的故事架构基本就是这样,它的主体几乎完全没有变动。
这个故事是当初讲出来之后,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有一种直觉的感动,它或许离做出来很远,也没法用理性去分析,分解到什么数据,它就是人类情感最基本的共鸣,但一个游戏或者说好的文化产品最珍贵的地方就在这里。
剩下来的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就是我们每个人用自己能够做出来的东西,策划、系统、美术、程序等等,去感染其他人,不断用自己的方式讲给别人听,直到最后,我们用一个游戏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给全世界。
这时候我们很感动,这种感动不是那种空泛的自我感动,而是完成了一件具体的事情,将美好的事物带给他人,这是一种自豪的感动。
今天的雷亚游戏已经不再是初创时期的小团队了。250多人的体量,同时开发几个项目,但Gulu认为它的方向与初衷仍然没有变化:做一个不负自身期待的内容创作者。
我们想孕育所有喜欢参与制作游戏的人才,让他们能在雷亚这个品牌下发挥自己的实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甚至说如果你有足够的想法和行动力,做非移动端的游戏——比如说我们重新做了《DEEMO》让它在PS4平台登陆——也可以;
想做街机、家用主机、掌机的内容也都可以,甚至说不做游戏都没问题,小说、电影这些,只要能讲好一个故事,创作属于你自己能够感动大家的内容,将它带到世界上来,那你的使命就完成了。
如果说有一个愿景的话,我们想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有自豪感的内容创作者。为了说出“我已经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我们会做很多准备,很多规划。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其实是能够理解这种自豪感的人,愿意和我们一起,无论是玩家还是开发者,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你能够理解这种自豪,我们的创作与付出,就都有了价值。
访谈临近尾声时,Gulu饶有兴趣地拿出了一些开发阶段的照片给我看。
就像机核办公室里日常的照片那样,这些随手拍摄的内容谈不上什么美感,但却充满了各种谐趣与惊喜,就像Gulu在访谈里说的那样,是“有温度的默契”。
Gulu说,他觉得能从事这个行业,是一种人生的幸运。
雷亚早期创业阶段,简单却有温度的办公空间
今天的雷亚保持传承的仍是“温度”
因为能做自己喜欢的游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做游戏的人”是有关游戏开发者的实验性纪实栏目。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开发者与玩家之间产生更多的认识、交流与理解。
如果你也是一位游戏开发者,有故事想与更多的人分享,请联系[email protected],或在站内私信@白广大,感谢。
精彩内容
(点击图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