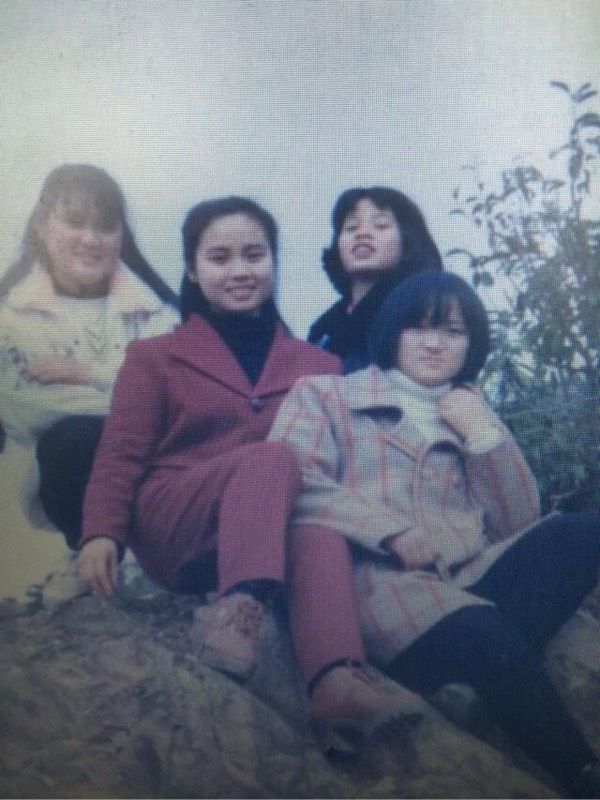儿时,过了冬至,年味便渐渐重了。
杀猪
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开始杀猪。我常常在后半夜被一声声惨烈的哀嚎声惊醒,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冲到门外,只见一盏昏黄的洋油灯挂在墙头,家里的那头肥猪躺在条凳上,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猪血汩汩从脖子里的刀口涌出来,流了大半个木桶。天气很冷,母亲把冻得索索发抖的我塞进被窝,于是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猪已被劈成两半用铁勾挂在长梯上,大锅里有烧熟的猪血,用稻杆挂起来的猪内脏还冒着热气。
猪大肠的末端是膀胱,我们俗称“小猪肚”,据说能治遗尿。年幼时我体弱,经常尿床,年末杀猪后,母亲便在小猪肚里塞入糯米,整个煮熟后切成片专门供我享用,看着姐妹们羡慕的眼神,我还会恬不知耻地说:“你们又不尿床!”
大部分的猪肉被拿到集市上卖掉,仅留下几块条肉用来祭祀,还有一些五花肉被切成小块腌成咸肉,几个月后,咸肉变成金黄色,拿出一小块放在菜干上,在饭锅里蒸一蒸,菜干被油浸润后,香喷喷的很下饭。猪骨头被放在一口大锅里熬到骨肉分离,骨头和肉被捞出来,剩下的肉汤加点酱油,倒在几个大陶罐里,凉了便成了美味的肉冻,春暖花开时,用调羹舀出一小勺放在嘴里,凉凉的肉冻逐渐在舌面融化,至今想来还是回味无穷。
突然想起了杜中食堂的免费红烧肉。我在杜中读了六年书,吃了好几次免费的红烧肉。杜中的公厕旁养了十几头猪,食堂的泔水把它们喂得膘肥体壮。我们在公厕外排队等着上厕所,手里拎着一根裤腰带,脑子里却在算计着杀猪的日子。元旦前后,食堂杀猪的日子是学生们喜庆的日子,开饭的时候,食堂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人手一只搪瓷牙罐,对于天天吃咸菜的学生,两勺免费的红烧肉无疑是一顿饕餮大餐。自从我毕业后分配到杜桥中学,每年从食堂分到的肉有十几斤了,外加一蛇皮袋学校农场分的桔子。我把猪肉挂在车把手上,蛇皮袋捆在书包架上,推着自行车一路招摇,碰到熟人打声招呼特别有面子。朋友圈里有个学姐说:“读了多少课本做了多少练习早忘记了,杜中食堂杀猪免费红烧肉和运动会馒头香味犹存,经久不散。”
如今,杜桥的养猪户几乎绝迹,要买到真正的土猪肉只能到大山里了。偶尔在农村路过一家猪圈,远远的我就把鼻子捏住了,我似乎已经忘了,小时候的我和猪同住一片屋檐下,还天天给猪喂食呢。
做年糕捣麻糍
年糕和麻糍是过年祭祀的必备品,家家户户都要做。杜桥有好几个年糕加工点,我们家通常在离家近的米行街加工。因为父母白天忙于生计,我们家每年都在晚上做年糕。糯米和粳米按比例浸泡十分钟,淘洗后放入脚篓内,让其自行晾干。父亲把脚篓挑到加工点后便走了,我们几个孩子守着脚篓排队,每隔几分钟便把脚篓往前面挪一挪。加工点灯火通明,蒸气腾腾,机器通宵达旦轰隆隆响个不停,年糕的香味飘得老远。 轮到我们家时往往快午夜了,睡意沉沉的我们被抱回家睡觉,不知什么时候,母亲轻轻把我们唤醒,在我们的手里塞一团温热的炊饭团或年糕,里面夹着红糖。第二天醒来,发现家里的竹席上整整齐齐地排着条形的年糕和正方形或长方形麻糍,隔几个小时我就把年糕逐一翻个身。
年糕和麻糍阴晾一周左右便可入缸浸水储藏。浸年糕的水也是十分讲究的, 一定要用冬水浸年糕,如果用立春后的春水浸泡,年糕就容易变质。自家做的年糕嚼起来特别有劲道,蒸熟的年糕片和芥菜豆面汤是最完美的搭档。杜桥的麻糍是台州名小吃,麻糍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至金黄后裹上蛋液,再加入冬笋、豆腐干、咸菜,谁闻了都会咽口水。春三月,放年糕的水面会出现一层白色泡沫,年糕和麻糍开始变质。再过一个月,表皮长出霉变的斑点,还是舍不得扔,用刀把斑点刮干净后继续吃,毕竟还要过半年才能吃到新的年糕。
现如今,我们天天都可以在菜市场买到新鲜的年糕和麻糍,我家已有好几年没有做年糕了,吃着买来的年糕却再也嚼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
穿新衣收压岁钱
小时候家境贫寒,但我的母亲有两件事坚持做到我们出嫁:每年过年的时候给我们添一身新衣;每个除夕夜给我们发压岁钱。
70年代几乎没有成衣店,母亲去布店扯两块布,带着四个女儿去裁缝店量体裁衣。我和姐姐的衣裤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妹妹的也是一样的,新鞋新袜也会给我们准备好。新衣服买好后,母亲会把它们逐一纳入衣柜 ,直到除夕夜才拿出来放到我们的床头。
自从老车站旁开了一家小商品市场,去裁缝店做新衣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年年跟着母亲买衣服,慢慢的也学会了讨价还价。我上高中后,母亲就把给姐妹们买新衣的重任交给了我。
记得有一年,我给自己买了一件双面穿的羽绒服,一面是红色的,另一面是白色的,羽绒服很厚实,里面的填充物是正宗的鸭毛。没想到这件羽绒服把我折腾的够呛,穿上后全身发痒,羽绒服严重钻毛,每次脱下来我就好像刚从鸭窝里钻出来一样,毛衣上插满威风凛凛的鸭毛,我家小妹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拔鸭毛,还乐此不疲。本来还想着正月开学那一天去学校晒晒新衣服,谁知道羽绒服洗了一次后严重褪色,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根本没法穿了。
临近年关,母亲会刻意攒一些崭新的纸币,把它们夹在一本旧书里,作为我们的压岁钱。压岁钱年年涨一点,以2或者8为尾数,5角2、5角8、6角2、6角8……,母亲会刻意避开4和7这两个数字。压岁钱用一张红纸包成方块,再用饭粒封好口。除夕夜,我们睡着后,母亲把压岁钱塞到我们的床头。大年初一,我们早早地就醒了,先摸摸床头找压岁钱,再穿上新衣服等着出去撒欢。出门前,母亲总是叮咛我们要保管好压岁钱,回家后,总要摸摸我们的口袋,但她从来不会把我们的压岁钱收回去。我的祖母就住在隔壁,我们吃早饭时,她就在那边喊话了:“饭吃了到我这儿拿压岁钱。”祖母有18个小辈,毎年正月初一她都会给我们发压岁钱,每人5角2,直到她去逝。工作后,母亲还是坚持给我压岁钱直到我出嫁。结婚那一年,我的婆婆给我一笔压岁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过压岁钱。
和母亲比起来,我不是一个尽职的母亲。儿子出生后,每年买的送的新衣服不少,拿到家后就给他穿了。我从没刻意要在过年时给他添一身新衣,总觉得衣服差不多都是新的没必要再买。儿子每年从长辈们手中收到的压岁钱不少,还沒捂热就被我占为己有,直到儿子上了初中,逐渐对我的这一行为颇有微词,我这才在银行给他开了一个账户,把压岁钱存到银行里,有时候手头紧,又偷偷把钱转到自己的账户,就这样转来转去,我现在也不知道儿子到底有多少压岁钱了。
备年货
在我们眼里,年货即零食。80年代初,父亲在山地种了几棵桔树。十一月份,桔子采摘后大部分被卖掉了,留下一脚篓用稻草贮藏起来,作为当年的年货。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我们偷吃了只剩半脚篓。母亲只好把桔子装进一个塑料袋,高高地挂在屋顶。我们天天瞅着那袋桔子却束手无策。幸亏桔子烂的快,每隔几天,母亲就站在条凳上把袋子解下来,把烂桔子挑出来给我们吃,剩下的又挂回屋顶。等到过年,袋子里完好无损的桔子只剩十几个了,刚好可以用来祭祀。
秋收后,蕃薯把墙角堆得满满的。削皮切成条放在锅里煮一下,挑几个晴朗的日子放在竹席上晒干。除夕夜,左邻右舍聚在一起炒年货,蕃薯干、川豆、花生和瓜子被倒进一口大锅里用沙子翻炒,风箱拉得呼呼作响,炉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母亲最喜欢坐在炉膛前添柴火,跳跃的红火把她的脸映得发亮,炉膛里窜出来的热风轻拂着她的头发,那一刻,我的母亲看起来比平时还要美。有时候年货要炒到天亮才能完工,孩子们熬不了夜,早已在“沙沙”的翻炒声中进入梦乡。
炒好的年货储藏在几个腹大口小的瓮里。正月里,我们的衣兜鼓鼓的塞满炒货,家里最先见底的是放花生瓜子的瓮,因为本来数量就不多,接着是炒豆,最后见底的是放蕃薯干的瓮,这是家里最大的一个瓮,高约一米,口却极小,我伸手进去抓蕃薯干时还得把棉袄脱掉,再过几天,手已经够不着剩下的蕃薯干了,小妹的手更是够不着。我常常看见她像杂技演员一样倒立在瓮上,一只手扶着瓮,另一只手在瓮里摸索着,小脸儿憋得通红,两条腿在空中挣扎。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把瓮放倒在地上滚来滚出,就这样,我们四个智慧超群的姐妹在开学前就把所有的年货消灭了,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辞旧迎新
春节的大扫除,我们叫作“掸尘”。母亲在长竹竿的一端系一些竹枝,穿上旧衣服,头戴斗笠,挥动竹竿对老房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布满墙壁的蜘蛛网、屋顶瓦片和横梁上的积灰被禅了下来,屋子里尘土飞扬。盖了一冬的被子和床单被拆出来拿到河边清洗,晒干后重新摊在竹席上缝好。之后把米粉烧成浆糊贴春联,红彤彤的春联更添了几分年味。贴春联后是隆重的祭神活动——谢年,每家每户选的时辰都不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天到晚不绝于耳。
除夕夜,母亲会烧一桌丰盛的菜祭祖,她总是告诫我们祭祖结束前,桌子上的食物不能动,否则老祖宗会怪罪的。我可是一点儿也不信邪,总是趁她一转身,马上从碟子里偷一块肉塞到嘴里,等到祭祖结束,我的肚子已经半饱了。我们称这一餐为“吃分岁”,言下之意是吃了这顿饭又长一岁了。临睡前,父亲会在门外放几响鞭炮,叫关门炮,放了关门炮我们就不能开门或出门了。正月初一全家起床后,父亲打开大门放开门炮,放了开门炮,新的一年才正式拉开帷幕。
走亲戚
正月是一段悠闲的时光,走亲访友必不可少。在杜桥,正月初二是不能走亲戚的,这一古风习俗延续至今。到了正月初三下午,小路上便会三三两两出现提着大红纸包,挑着甘蔗回娘家的小夫妻,我们这儿称“拜岁”。第一年来拜岁时,小夫妻会被娘家亲戚捉弄一番,把他们关在大门外不让进来,我们在院子里哈哈大笑,他们站在院门外一脸尴尬。丈母娘把送来的甘蔗切成长约两寸的小段,分遍全村。正月初六下午,小夫妻挑着娘家送的金团高高兴兴回家,婆家也要把金团分遍全村。
小时候我们最喜欢正月里去外婆家住一段时间,娘姨们也会带着孩子回娘家,外婆把浆洗好的蓝色粗布被褥铺在地板上,小孩子全都睡在地上。外公是教书的,家里有很多书,有时候也会抽一本看看,但他的书基本上是我看不懂的教学参考书,等我到了能看得懂的年龄,他却病逝了。已经记不得外婆给我们烧过什么好吃的,但亲戚们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氛围至少难忘。
闹元宵
小时候我们桑园村有一个传统节目——舞龙灯。正月初三开始,村里的能工巧匠就开始扎龙头,一块二十米长的绸布把龙头龙肚龙尾三部分连在一起。龙灯做好后,在一阵阵啰鼓声中,十几个青壮年举着神气活现的龙灯绕村巡游一圈,后面跟着一群小屁孩,家家户户在门口点上香蜡烛祈福。正月十四下午,龙灯从老爷殿移到我家门前的晒谷场,母亲早早地做好甜羹和咸羹,我们吃饱后等着夜幕降临,隔壁的村民们都来了,把晒谷场围的严严实实的。七点钟左右,人群开始骚动,耍龙灯开始了,龙头时而腾起,时而俯冲,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大有腾云驾雾之势,蔚为壮观。
父亲年轻的时候也会参与舞龙灯,但他总是猫着腰排在最后摇龙尾巴,裤脚常常被小鞭炮炸出几个洞。去年元宵节,我带着孩子回娘家,又看到了多年不见的龙灯。当年的舞龙健将们都已垂垂老矣,看到人群中父亲那张苍老的脸,心底不由泛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2017年春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曾经那么盼着过年的我却不愿意过年了,过了年意味着又长了一岁。年味一年比一年淡了,很多过年的古风习俗正在慢慢消失。一件新衣服、一个炊饭团、一节甘蔗都曾经让儿时的我们幸福感爆棚。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但我们的幸福感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 那么,我们的幸福感被什么偷走了呢?
2016年12月31日 临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