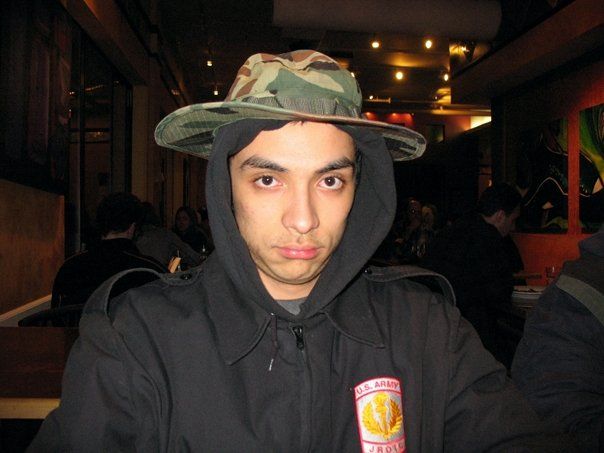从美帝回来快一个月了,一直想写一写此行的感受。毕竟也是向往了很久的地方,朝思夜想,终于借着Draper University这个项目成行。
Draper University是一个青年创业者培训营,由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公司德丰杰(DFJ Venture)设立。DU每个季度从世界各地招募三四十个带着创业想法的青年,并用不同的方法减免奖学金(协助PR,获取未来公司的股份等等)。把这帮人拢到一起后,就是满满当当的各种讲座和团队活动,讲座主讲人不乏各个领域的牛人。团队活动也千奇百怪,每天被折腾的神经紧张,但又觉得有趣。活动有很高大上的商业计划展示,也有如何用很简陋的材料制作辅助模型让鸡蛋从8楼落下来安然无恙(文科生我当时被这个任务折磨得快疯掉,结果在小伙伴指点之下,用包装纸,吸管,皮筋,纸杯做了一个破破烂烂的纸降落伞,结果鸡蛋幸存了……)
我原本对创业没什么兴趣,就是想借机去美帝看看,就报了名。几番申请折腾,又忽悠来奖学金,免去75%费用,终于欢天喜地飞往加州。
直到我去了Draper University。
推开Draper University的大门,见到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各色小伙伴,就更感觉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说是另一个世界一点也不为过。湾区码农扎堆,高教育高收入,处处弥漫着乐观迷醉的乌托邦气氛。DU更是这种异世界的微缩版。大多数入选的学员都二十出头,一身戾气,精力旺盛得头上要长出角来。三十来号人当中,有美帝本土选手,也有印度的,日本的,丹麦的,沙特的的,非洲的,荷兰的…… 出身背景宗教肤色都不一样,但是大家的世界观却出奇地和谐。多数人在来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创业项目,我作为一个两手空空的媒体砖工,刚开始有点儿懵。但没几个小时,就发现大家精神上是一个物种的。
接下来的7个星期,瞻仰了诺奖团队的神人,见识了搞DNA培育的邪魅狂狷男,目睹了twitter,Dropbox,facebook等一干geek们的风采。各界投行咨询风投界大牛悉数登场,每天演讲听到吐,各种投资创业大会参加到脚软。另外还打了枪,杀了鸡,在雨水里滚了四天泥巴……
流水账写下来未免无聊,但是人物志是必须写的。煽情地说一句,此次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好多有趣的灵魂。
接下来就是各路小伙伴们的人物志。多图哦。
1. Robert & Max
为什么第一个要写他?实在是为了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小帅哥五官粉雕玉琢,睫毛蒲扇一样忽闪忽闪,实在是本项目的一大福利。由于我是个不看重外表,注重男生内涵的人,我跟他的交流格外多。
Robert一口浓重的加州口音,身上的美国气质很重,优点和缺点都是。中学时代时他就发动低年级小伙伴,组成分销团队在学校倒卖糖果。他生在加州,长在加州,大学也是在加州念的,骨节宽大颀长,好像在湾区日光里泡久了的棕榈树。目标明确,欲求坚定,有一套自圆其说的价值观。杀气重。
Robert是学商的,本来的项目是做一个生活理财类的APP。参加项目不久,他结识了俄罗斯码农Max。Max堪称西伯利亚版Sheldon,我总觉得,他大脑的剖面是一块密密麻麻的电路板。Max日夜编程,开发出运用数据计算预测公司项目业绩指标的程序,但他语言表达能力受母语限制,来项目之后很久,大家对这个产品的印象都是“虽然不明白在做什么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Robert适时的出现,跟他组成了团队。Max负责开发,Robert推广。
Robert很快改变创业重心,紧锣密鼓地工作起来。每天就算接近深夜,路过食堂或休息室时,总能看见Robert和Max盯着电脑屏幕,眉头紧皱。就算如此,Robert第二天总能准时出现在早餐室里抹黄油,搅咖啡。Max则不一样,编了一夜程序,满眼血丝,每天冲进食堂叉走最后几片没被收走的水果。Max的特异功能还包括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秒速入睡,天地之间物我两忘,只有一只大白熊在西伯利亚的冰原上奔啊,奔啊……
Max的思维接近于编程语言,因为a所以b,加上c,一定会产生d。完全直来直去没有拐角的思维方式。而Max和Robert,是很有意思的一对组合。
Max的父母都是医生,祖父母是物理学家。Max祖上两代刚好经历了两大动乱时期,祖父母经历二战,父母经历冷战和苏联解体。祖父母在乱世里,珍惜一切抓得住的资源来做科学研究,父母恰逢苏联解体,丢掉了工作,只能打很多份工,没日没夜的补贴家用。
到Max,是第三代,总算碰上和平年代。但是家族传统被承袭了下来。
Max主修金融工程和CS,很快被湾区一家公司挖走。Max虽然在美国工作,从头到脚都还是那个Mother Russia孕育出来的,好似移居到亚热带还能自带寒带生态系统的北极熊,有层细胞膜,价值观只出不进。
比如,他可以一边希望苏联重组,一边用程序为湾区的资产阶级公司们服务。因为他坚信,苏联的体制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效率,一切井然有序,就像程序一样,只要输入了规定值,就一定能得出一定的效果。此外,父母在苏联解体时失去工作的切肤之痛,也让他坚信当下才是“礼崩乐坏”。秩序是他的信仰。
他相信公司的业绩可以被一套电脑程序预测。他相信他的代码,比咨询公司的人力资料收集要靠谱百倍。有一次风投大会,我看到Max端着酒杯,一脸不高兴,问他原因,他说那些投资人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们以为自己懂,但其实根本不明白。我不喜欢这种会议。”
“可是这种场合很宝贵,很多投资就是这样拉到的啊。”
“我不喜欢。我觉得他们在浪费我的时间。”
这时候Robert只好无奈地笑笑,“他不喜欢的事情就只有我来做了。”
Max曾经在一次团队任务中,用纸片和弹珠做了一个三维弹球结构的系统,而这个小系统又是一个更复杂的大系统的子集……我去观摩时,面前出现N条横七竖八的线,跟《偷天换日》里的激光保护系统似的。Max一直摆弄到深夜。如果时间足够,让他赤手空拳造一台发动机估计也没问题。于是Max成了一个众人争相观摩的存在。能不能合群根本不算个问题,也是Max从来不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Robert是斩钉截铁的美国人,并且有种美帝少年“何不食肉糜”的世界观。而这对冷战组合居然出奇地和谐,可见Draper University奇异的熔炉环境。
Robert和Max在最终的商业计划展示环节,在一帮风投和天使投资人的评审下,拿到了第二名。他们筹到了一些钱,但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项目还是正式启动了起来。最后一次聚餐时,Robert戴着软帽,脸在热气下有些泛红,目光也柔和娇憨了起来。Max不知道又在哪儿睡着了。
2. Adi
Adi也是我的队友。她原籍尼日利亚,爷爷当过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长,而她本人在英国长大,姑且算一个“官三代”。Adi主攻金融,毕业后在风险投资公司当分析师。Adi气场强劲,举手投足都杀气腾腾。她是一个潇洒的T,把漂亮女朋友照片拿给我们看时,众爷们儿纷纷羡慕嫉妒恨。
Adi做任何事都很有底气。这跟年龄经验没有必然的关系,纯粹是内心强大与否决定的。她想成立一个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专门针对少数群体(发展中国家妇女、囚犯、残障人士、有色人种等)。因为这一类人群通常是风投不愿意关注的,他们的各类资源欠缺,经验缺乏,投资的效果一般不好。Adi深信这让这个群体的翻身走向了万劫不复——因为没有资源,所以得不到投资,得不到投资,就更不能翻身致富。Adi想打造一个半风投半孵化器性质的基金,一方面针对少数群体提供人脉的牵引,技术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一方面把这个当做一种特殊的投资,而不是单一的募捐慈善。Adi二十多岁,但她的目标是把这个基金打造成一个全球性的投资性孵化器,从资本的角度改变少数群体目前的现状。从务实的角度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Money talks, idealism doesn’t。她丝毫不被困扰。她的想法很大,但是敢想敢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Adi的思路非常清晰。她奔波于硅谷和欧洲之间,和几个合伙人日夜兼顾募资和各类规划。在DU的日子里,大多数时间见到她,她都在对着电脑专注地忙碌着。我有很多疑问和困惑,也都会去征求她的建议。她是队伍里常常提出尖锐质疑的那个人,理性、冷静而又强悍。有的时候锋芒会有些扎眼,估计和她的经历也有关系,底气充沛往往就会如此。
我问她将来打算如何。她说,估计满世界奔波的日子还要持续很久,但她希望能和女朋友尽快完婚,然后把她尽量带在身边。”官三代“这个标签,在她身上满满的都是正能量。聪明,出身好,受过高等教育,自身努力,有追求,并为之付诸行动——有人说,很多时候,可怕的不是别人比你更聪明,而是聪明的人比你还要努力。这种”聪明“再加上一个高平台和好出身,外加努力,恐怕杀伤力无穷吧。
3.印度帮
印度人在硅谷的存在感极强。DU的项目共不到40名学员,印度人就有5个,其中3个是印度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多为码农出身,技术过硬,极为务实。像气味扑鼻的咖喱酱,实用、百搭、高性价比。
同组的队友Raman,就是班加罗尔来的印度码农。Raman有种诡异的幽默感,配合咖喱味儿的口音,十分欢乐。Raman没有手机,随时随地手持一个讲不出牌子的7寸安卓平板,该平板什么功能都有,还能打电话,颇具深圳华强北气息。Raman每次接电话都像在往自己脸上糊砖。
Raman比较低调,一般情况下不怎么言语,但是接触深了,感觉还是一个比较踏实可靠的实干派。比如他来这个项目,学费居然是众筹来的。他入选项目之后就跟一帮印度企业家说,我现在要去硅谷了,可以把你们的名片带过去,很多潜在的机会哦呵呵呵呵呵。东拼西凑,居然cover掉了所有学费,还顺便买了机票。本期学员37个人,要么全款缴费,要么努力讨价还价争取奖学金,像Raman这样把互联网众筹精神拿出来弄钱的,仅此一人。
项目一共7个星期,结束之前会有商业计划大赛,表现优异者可得到投资。大多数人的商业计划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实际的产品,毕竟在7个星期内弄出一个成型产品,谈何容易(而且还是日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7个星期)。但是,有成型产品比没有产品,无形中多了很多筹码。Raman的起点和别人差不多,他选择在大赛两个星期前,花1000美刀外包另一个印度码农把他的产品雏形做出来。“讨价还价才敲定是1000美刀的,希望他能一周内搞定吧。搞不定我就完蛋啦。”Raman精打细算,连来这里的费用都想尽办法不从自己腰包里出,而该花的投资他掏起钱来却毫不含糊。比起找合伙人——筹钱——做产品这条路,他选择花钱外包个雏形出来再说。最终产品顺利成型,界面虽然简陋,但也算五脏俱全(而且无缝对接Raman的安卓平板!)。Raman拿到了一小笔投资留在了硅谷,继续奔走筹钱,一步步创业。
我觉得他的“实用”思维是极其能够成事的。走一步是一步,能搭多少东西就先搭建多少,手头资源不够(例如来这里的费用没能力自己掏钱)就想法子争取资源。Raman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闷身发大财……
项目结束后,三位来自印度本土的学员都成功拿到了小笔投资留了下来,他们的PPT可能做得不够光鲜,团体活动时也不那么显眼。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简单而务实。我在硅谷,被灌了太多美帝乐观主义的迷魂汤——不能说不好,但很多东西放在资源和机会要靠抢的发展中国家,显然行不通。我在DU的项目里,从印度帮身上学到的东西,不比从任何人身上学到的少。
4. Daniel Chin
丹尼尔陈同学是美国公民,也是波多黎各和中国混血。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姑且叫他小陈。
小陈的家境并不富裕,银根相当吃紧。美帝大学学费出了名的高,但是小陈成绩优异,顺利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四年全额奖学金。如果事情一直顺利下去,就是个喜闻乐见的屌丝逆袭故事了——屌丝逆袭的故事有什么好写的呢?小陈进入大学两年后,被查出在填写家庭收入申报时漏掉了项目,具体原因很复杂,总之,校方认为小陈没有如实填写,取消了全额奖学金。小陈没有了学费来源,只有退学。随后他加入了美国海军。
然后就是小陈现在的样子了,平头,迷彩T恤,下摆扎进高腰工装裤里,拎一个军用水壶,一股军队做派,有种走错了片场的感觉。小陈的嘴角总挂着似有似无的讪笑,也可能他的嘴巴形状就是那样的……小陈聪明,反应灵敏,心直口快,浑身上下都是戾气。这种戾气和Robert的完全不一样,是一种苦大仇深摸爬滚打后的自我保护。
DU每天的日程中,都会安排很多各界知名人士前来演讲。其中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学教授,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团队中的一员。教授侃侃而谈,内容各种高大上,宇宙的奥秘什么的,我这种文科败类自然是一个字都听不懂的——这位教授居然是小陈在伯克利时的老师。小陈坐在第一排,听得都快醉了,那种“这种高大上的宇宙奥秘你懂我也懂”的默契和共鸣啊……小陈就这么跟诺奖教授一唱一和了一整个小时。还是平头、T恤、迷彩服和工装裤。我不知道那一刻小陈的心里有何想法,他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待在伯克利的课堂上,却被一脚踢了出去,在大海上一漂就是一个月。
小陈跟我说过他在军队的经历。他不是舞刀弄枪的士兵,大学学的是工程,在军队里的职位还是工程类的,负责押运海上运输的武器和各类设备,俨然一个美国版镖师。在大海上一漂可能就是一个月。问他辛苦吗?他说,不觉得,就是无聊。守着一船枪支弹药,环视天水无际。苏子云,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我陡然又想起王小波在云南放牛的时光,愣愣的盯着天上的半明半暗的云。这两个类比很别扭,因为小陈到底是个不会讲中文的美国人。但他身上的有些悲戚是中国式的。
小陈日后的理想是建一个专注工程学教育的网上平台,希望打造一个工程学方向的可汗学院,同时和需要相关人才的大型企业对接。但在此之前,他必须按承诺在军队里再待两年,或者说,在大海上再漂两年。他有那么多的时间在海天一色里思考人生,正式开始闯荡后的日子,肯定不会无聊。
5. Arun
DU会给所有学员分组,我所在的组里一共5人,印度人占两个半。
首先是印度裔美国青年Arun,移民二代范本。披着印度人的皮,宝莱坞舞蹈跳的风生水起,思维性格世界观却美国到了骨子里。
Arun的口头禅是“我才不担心”,半眯着眼睛,靠在软垫上嘻嘻哈哈是他的常态。他家乡在波士顿,大学在多伦多念的。Arun气质里并没有任何侵略性,小组任务时却是全队的大脑——说是大脑其实也不太恰当,但是他在五人团队里,有一个强力黏合剂的作用。美国有一种典型的DIY文化,通俗点说,“门外汉”文化。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强迫性地束手束脚,总是质疑“这件事真的是我们的能力所及吗?”Arun没有这种思想包袱。奇怪的是,他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学霸,也不是Max那样技术过硬的码农。暂时没头绪,就想办法找头绪。需要什么技术他不会,就再去学。这种逻辑很简单直接,也很有效——直接省去了纠结的评估、思想斗争和瞻前顾后。确定目标——确定目标所需技术和资源——学习或获取技术和资源——达成目标。
简单说,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能力不够就再去练级。有的时候我会质疑这种思路,是否把一切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可是,问题真的有那么复杂吗?
Arun二十出头,就得过两次癌症。先得了一次,然后癌细胞转移,又得了一个名字不一样的。两次治疗他都熬了过来,四肢变得纤细瘦弱,每天也必须服用药物(“如果忘了吃药我就会,’哎呀’”,他脖子一歪,做了个断气的动作)。但他从头到脚都是生命力。Arun整天慢慢悠悠地晃荡着,嬉笑怒骂,眉头都很少皱一下。顶着一张印度脸,一到有音乐的地方就大跳宝莱坞舞蹈,身体柔韧得出奇。而且放得开,完全放得开。跳舞是最能够展现一个人内心性格的——并不是技术上好不好,有没有经验的区别。有的人完全乱舞一气,但是四肢是舒展的,打开的。Arun就是这样,跳舞未必有章法,但就是能打开,盛开得肆无忌惮。我跳舞是僵硬的,想要动起来,每个关节都不对劲,瞻前顾后,手也不知道往哪里摆。
我看起来很外向,其实放不开。天朝人的共性也好,我自身的焦虑也罢,总之,随后通通释放出了负面作用。在DU的这段时间里,尽管不愿意承认,我自身性格中的焦虑、悲观被拎出来放在了我面前——我对这些问题向来是装聋作哑的。Arun像一面镜子,把它们照得清清楚楚。
在DU的培训项目里,有一项是类似荒野生存的训练。我从来不运动,也不喜欢户外,焦虑的神经时时绷着。而且我体质不好,走路又慢,几公里的山路,渐渐地就落在了后面。DU的小组之间是有计分对抗的,我毫无疑问是队里最弱的一环,也拖了队友后腿——Arun是得过两次癌症的人,可整个过程下来,我好像才是那个病恹恹的。
快到结束的一次比赛里,比赛哪一组最先到达海滩的终点。我的精神被折磨到极点,整个人快垮了。队友为了照顾我的体力,走一段停一段。同组的另一个队友Raman说,要不要咱们想个办法走快点?
Arun说,走快干嘛?为了那一点团队分数和名次吗?谁在乎?
另一个队友队友Adi坚定地看着我,叫我不要担心,也不要放弃。
最后队友商量好,其他人步行,由最强壮的队友Robin骑自行车先送我走完近10公里的路去海滩,然后Robin折返去接其他人。最后我先到了海滩,没有走多少路,等队里其他人到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散了。我们小组是最后一个到的。名次更不用谈了。
这种支持和照顾,还有在你撑不住时拉你一把的举动,着实让人窝心。Arun说的那句话,我也永远都不会忘记。
6. 松岛君
DU里的黄种人面孔一共就三个。而日本人松岛君,是几十名小伙伴里唯一被公司派遣来学习的。松岛长得不太像传统的日本人,皮肤黝黑,头发微卷,倒像东南亚来的。他的英文不错,毫无槽点。
他对英语挺感兴趣,大学学了英语语言学。大学gap了两年,去了一家澳大利亚的水上运动公司打工当导游。“当时去澳洲,就是想提高英语水平吧,觉得在日本学不到实用的口语,就去英语国家学习了。”澳洲之行后他回到日本,拿到了一家日本软件测试公司的offer,因为他英文好,就被派遣到这个项目来培训了。
松岛非常谦虚,向我请教英语口语的学习方法。我和他的背景迥异,但在DU却有一个同样的标签——“非典型东亚人”,因为比较努力学习英文,争取到了机会,得以来到陌生新鲜的环境里体验生活。松岛和我表面上看,都没有一般约定俗成印象里黄种人的拘谨。我记得有几回,一队日本人过来学习旁听,个个西装革履,正襟危坐,气场是紧绷着的,好似物种入侵。松岛一身休闲服,靠在软垫上,在一群异族人里眺望自己的同类,场面实在诡异。
但是归根结底,他还是日本人,抹不掉这个烙印,思维方式是日式的。这种自我认同上的矛盾,就像他的东亚脸盘上的黝黑皮肤和卷发一样,又好比一件缀满了铆钉亮片的和服,猎奇向。我能理解他,是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矛盾存在。从十三四岁就开始听英文摇滚,学英语,看美剧,看外国小说,好像随时整装待发要细软跑。我到旧金山之后,多数当地人会误认为我已经在美帝待了很久。但异乡客的印记是甩不掉的,你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旁观者。我再努力地模仿美式发音,吐字还是一股淡淡的天朝味儿。圆月时的狼人变身变一半,啪,忽然停了。獠牙只生了半边嘴,光屁股长一根毛乎乎的长尾巴那种感觉。
他表面上看,是完全融入到DU这个圈子,毫不突兀的。团队活动时他是思维缜密的执行者,低着头默默地把事情做好,一副随时准备接受考核的样子。他会教大家打日本扑克,唱蛋疼的歌很蛋疼的舞,然后大家会说,松岛你真的不像日本人啊。
可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在这里“表现不好”,他被公司派来,总觉得要为公司争光。我笑着说这是东亚思维,总觉得大家都在盯着自己,很自然的把自己放到一个排名体系里,觉得自己配不上面前的东西。他还说,他觉得自己不一样,言的限制让他觉得很多东西无法表达,很多观点无法倾诉。有一种孤立感。这里的人们也不够了解他。
真正的“融入”一个迥异的文化,真的那么重要吗?而在美国这样一种熔炉里,真的有所谓的“完全融入”吗?
在那场荒野生存训练里,我的衣服全部湿透,牛仔裤也找不到,眼看着就要穿着湿漉漉的裤子哆哆嗦嗦地露营。松岛知道后,把他仅剩的一条干的运动裤借给了我。我把肥大的裤脚卷了好几道,总算熬过了两天。这么说来,我和松岛也算是“穿过一条裤子”的兄弟啦。
小结
人物志告一段落,但也可能还会继续写下去。我在DU遇上这么多有意思的人,这次经历简直是莫大的幸运。世界真的很大,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铿锵有力的活着。有的时候,我会质问自己,被抛在朝九晚五的滚轮里,每天雷同的生活还算不算真的是“生活”?我们都爱看鸡汤文,看到屌丝逆袭的故事,都会肾上腺素狂飙个几分钟,自然而然的臆想自己也可以做到。可是,“逆袭”之前,我们是否有力的“生活”了呢?
我曾经把这种生活态度的差异归结于国情问题。天朝哪有资本主义那些良好的保障和氛围以供年轻人施展拳脚呢?但是DU里的这些人,来自哪里的都有,他们有自己国家特色的压力,和往前冲时会遇到的坎儿。土壤固然重要,关键还是看个人有没有这份“我要活得不一样”的心思。天朝纵然脏乱,但好歹不是死水一滩——脏与乱中是有着机会与活力的。相信在天朝的年轻人里,也会有越来越多比这个精彩千倍的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