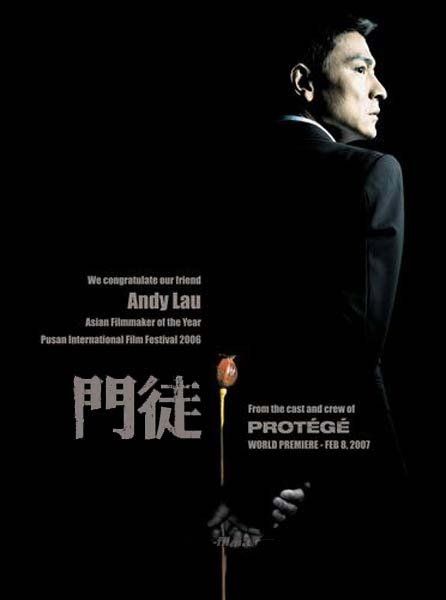一
戒毒第三天的时候,秦飞感觉身子被几万条蚂蚁撕咬,时而刺痒难耐时而疼痛难忍。
吸毒二十五年,打从吸毒的第一天开始,他从没想过要戒。但此时,秦飞却躺在卧室的床上,旁边的茶几上放着安定和口服的美沙酮。海洛因成瘾的症状强烈,身体依赖和心理依赖并存,秦飞只能靠大量的安定帮助他能够偶尔睡着,再靠美沙酮这种戒毒类毒品来缓解身体强烈的戒断反应。
但是秦飞知道,仅靠这两样药,不可能彻底戒掉海洛因。他还需要强大的毅力和绝对自愿的决心。毕竟溪城吸毒的千千万,真正戒掉的只有王行。他再一次想起了王行,这是这三天来唯一一个不停在脑中浮现的名字。他想,或许所有溪城的瘾君子,都应该恨一个人,就是王行。
秦飞的第一针不是为了快感,是为了止痛。
那会儿他被个狠角色用砍刀在后背划开了二十厘米的大口子,整个背部血肉横飞。都是道上混的人,秦飞不能报警,只能找王行陪着,去民办医院缝针。民办小医院便宜,不用住院,不通知家人,也不用联系单位派人陪护。只是很多国营医院的基础药物,他们没有,比如麻药。那时候家里孩子多,打架斗殴稀松平常,这种诊所除了平常给感冒病人挂挂点滴,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服务这群社会闲散人员,缝个针堕个胎。他们称呼秦飞这群人,叫社会人。
秦飞忍着痛坚持缝上了伤口,但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坐着或者趴着睡觉,因为躺下或者侧身都会因为皮肉撕扯伤口,从而在背后传来剧烈的疼痛,每当这时候,秦飞的周身的汗就像河水一般流淌下来,汗水透过纱布浸入伤口,就会再一次加剧疼痛。
“二哥,今天怎么样,好点儿没有?”王行一下班,就来到红蜘蛛大舞厅的角落沙发里找秦飞。
“好个鸡巴,大声说话都疼,让你在医院给我弄来药没有!找你办点儿事儿怎么那么费劲!你不认识不少大夫么!”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骂着王行。
“二哥,药倒是带来了,但是你可想好,这玩儿意上瘾。”王行坐到秦飞的身边小声的说。
“滚你妈的,药还他妈能上瘾,你给我弄的大烟啊?只要能不疼,你就是给我的是弄大烟也行啊!”秦飞问。
“不是大烟,不过也差不多,谁知道你能不能挺得住。打完这针,浑身都舒服,比干什么都得劲儿,比跟小姑娘干那个事儿都好受!”王行从兜里拿出了一盒药,里面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十支玻璃瓶,他用砂轮在玻璃瓶的颈部熟练的划了一道,抄起打火机,砰的一声就在上面敲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随后,王行把注射器的针头插进去,用食指和中指夹着注射器的尾部,一手倾斜药瓶一手缓慢的向外抽取,不一会儿,药瓶里干干净净。
“这个叫杜冷丁,止痛效果非常好。”王行把注射器放到一边,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焦黄的橡皮绳,示意秦飞伸胳膊。
秦飞没有多想,就把左臂交给了王行,舞厅恰好放着一首节奏缓慢充满挑逗的歌,灯光忽然随着现场的暧昧氛围昏暗下来。王行把橡皮绳绑在秦飞的胳膊上,借着仅剩的微弱光亮和娴熟的手感,精准的把针头扎进秦飞的静脉里。秦飞看不见王行的表情,只觉得冰凉的液体缓缓混入血液,整个小臂都像被冰水冲刷一样,感觉不疼不痒,不明不白。
很快秦飞的背脊就一点儿也不疼了,他不自觉的把一直绷着的身体放松下来,靠在了沙发上。王行坐在他旁边关切的问:“二哥,不疼了吧?还疼的话就再打半支,不过应该差不多了,这些就不少了。”
“嗯,不疼了,真好,这几天可折磨死我了。”秦飞的眼睛慢慢合拢,又慢慢张开。他看着在舞厅里不停旋转的人,觉得他们跳的比以往更加轻盈,连平常听腻了的歌,也觉着那么悦耳动听。秦飞的眼睛彻底闭了下来,嘴里还在嘟囔着,真好,真好!
二
连续几天注射下来,秦飞真的如王行所说的一样,打上了瘾。
回头想想那一年,王行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开始打起了杜冷丁,他们管这个叫打小针儿。王行每天从医院不停的大量往外拿药,免费送给朋友们。一传十,十传百,在社会人的圈子里,打小针儿成为一种时尚,成了年轻人最有面子也最快乐的事情,王行拿出来的药根本供不应求。没过多久,王行终于从一个吸毒者,变成了溪城第一批贩毒的人。
杜冷丁是常用药,所有大医院每天都有固定的患者可以得到用来止痛。王行从医院买出来,七毛钱一支,一盒十支七块钱。他单支卖三块,一盒二十五,对于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块的溪城,想打得起小针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秦飞还记得那年除夕,雪下的老厚,他放完凌晨的鞭炮就跑到王行家买药。王行从楼上下来,好大不情愿的说:“过年好!二哥,这大过年的你也不让人消停,没有了,都卖了,剩下的是我自己打的了。”
“别没有啊,我那天让二毛告诉你给我留一盒啊,赶紧的,家里下着饺子等我呢!”秦飞冻得搓着手踱着脚,不耐烦的说。
“真没有了,儿子唬你一点儿,早上大林子他们过来全买走了,人家一盒给我一百,我也不能不卖啊!挺两天吧,等我再有的!”王行说。
“放你妈屁,这玩意是挺的事儿么!你现在行了啊,二哥也没有面子了?是不是?”秦飞气急败坏,一把拽住了王行的脖领子。
“二哥,你要这么唠嗑就没意思,怎么的你还要打我啊?别说我没有,我就是有我不卖给你就不行么?”王行缓和了一下语气接着说:“你要挺不住,我自己打的你先拿走,三十。”
秦飞松开王行的衣领,伸手掏出来一百块钱,递给王行:“别三十,他们一百拿的,我也给你一百,大过年的,贵点儿就贵点儿。”
“三十块钱一支,二哥,少买两支过过瘾得了。你要不要我扭头就走,这都是我自己打的。”王行一边整理衣领,一边漫不经心的说。
回到家里的时候,秦飞兜里的二百块钱分文不剩,老婆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他面前,他夹了两个,说饺子咸了,不爱吃。就丢下老婆孩子在屋里,一个人走进了卫生间,把门反锁。
秦飞憋了一肚子气,但是他不知道该冲谁发这股火儿。他拿出注射器,抽了两瓶药打进布满针眼结痂的胳膊上,收拾好东西以后,老婆和儿子已经吃完了饺子,电视里的联欢晚会播放着难忘今宵,这年就算过完了。秦飞觉得气也已经消了,所有的不快都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他觉得周遭一切都是好的,外面起伏的鞭炮,窗前悬挂的灯笼,妻子和孩子,甚至王行和他自己,都是好的。他钻进插着电热毯的被窝,儿子跪到床前给他拜年:“爸爸过年好,妈妈过年好!”老婆从枕头下面抽出一张十元钱递给孩子,秦飞眯着眼睛,对儿子点头,说:“真好,真好!”
三
秦飞艰难的从床上坐起来,他想喝一口美沙酮,但还是忍住了,最后倒了杯水,吃了几片安定,到客厅和老婆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又爬到卧室的床上。
他突然想打个电话给王行,虽然从王行戒毒以后,他们很少联系。秦飞抄起手机,按下号码。
“喂,二哥,怎么了,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王行熟悉的声音从话筒另一边传了过来。
“没啥事儿,唠唠嗑儿。”接通以后,秦飞才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想和王行说的。
“我大侄儿要结婚了?”王行试探着问。
“没有,那臭小子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没个稳当时候,我他妈的也不催他了,爱结不结。你最近干嘛呢啊?”
“混吃等死被,不怎么出门,咱家老爷子这两年身体不行了,三天两头上医院,我就得陪着。”王行自嘲的说。
“哪天上家来吧,让你嫂子炒俩菜,咱俩喝点儿。”秦飞说。
“行啊,不过咱们先说好啊,那些玩意我可不碰,土埋半截的人了,咱们可别整那些没用的。”
“你有脸和我说这话么?”秦飞冷着声音问王行。
“二哥,我当时是不对,但是海洛因可是你带着大家伙上的道儿,要没脸咱俩都没脸。我命都差点儿没了,我要个鸡巴脸。”王行讪笑的说,但是字里行间都带着刺儿。
放下电话,秦飞仰面朝天的躺在椅子上。王行的话没错,如果溪城吸毒的人第一步是王行牵着走的,那么最后掉进火坑,就得算是秦飞推的了。海洛因比杜冷丁,危险十倍。
秦飞之所以贩毒,起初是因为溪城仅有的几个卖针渠道全都越来越贵。由于溪城吸毒成瘾者在短短几年大幅增加,公安部门开始大力打击吸毒贩毒行为,医院方面也严查药品处方和流通渠道。原本癌症患者领了药可以回家注射,现在都要求现场注射才能离开医院。虽然毒贩在临近几个城市的医院都有关系,但是和原来的供应量相比,就显得有点儿微不足道。况且,风险大了,打通医生也需要花更多的钱。到最后,作为最大贩毒商的王行自己都快承受不起杜冷丁的价格了,五十一支,一盒五百,而且时常断货。
那段时间,整个溪城吸毒者都如同丧家之犬一样,逢人就问有没有针。要是恰好朋友手里有一支,几个人用一个注射器,你打一点儿,我打一点儿,还总是因为谁多打了一点儿而大动干戈。
四
秦飞不愿意这样,王行也不愿意这样,这个城市里的吸毒者都不愿意这样。所以秦飞决定南下,去沿海的地方碰碰运气,当真买的到港台录像片里说的那种白粉,从此就再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求王行卖他点儿杜冷丁了。
想好了办法,秦飞开始和身边的人透露,说自己有路子搞到白粉,要的话就先拿钱,冒一次险就要尽可能的多带回来点儿。
先后有十几个人给秦飞拿了钱,最大的一笔是王行给他的,两千块,另外,还有两盒杜冷丁。
筹够了钱,秦飞买了张车票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告诉老婆:“我去倒腾点儿港台货,回来做点儿小买卖,如果一个月没回来,你就赶紧回娘家避一避。”
老婆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蹲在地上大声的哭喊:“儿子,你快过来,你爸不要咱们娘儿俩了!”
秦飞的儿子从房间走出来,不解的看着父亲和母亲,不敢说话。
“哭你妈了个逼,我还能死了是怎么的,我怕那帮人来跟你要钱,家里没钱,我不得想办法去挣么?就他妈知道哭,你能哭出钱来,能嚎出儿子的补课费?”秦飞看着不争气的媳妇,扯着嗓子骂到。
秦飞没有路子,他压根不知道海洛因什么样,只听说像白面像石膏,但是除了在录像机里以外,他从没看见过。
下了南城的火车秦飞立即找了间小旅馆住下,他甚至有些后悔自己太鲁莽。空手套白狼的事儿他没干过,一旦这一次没买到东西,秦飞回去在社会上就彻底没了面子,以后将寸步难行。
足足半个月,他没有结交到和他一样混社会的朋友,也没发现吸毒者的据点儿。正值下海经商的浪潮突起,南城的街道上的行人总是行色匆匆,表情凝重严肃或者欣喜若狂。秦飞不知道他们在难过什么,也不清楚他们在开心什么,他想,一定不是毒品的事儿,因为他们的小臂外侧上,没有针眼,那里是最顺手的地方,任何吸毒者都不会放弃那里的血管。
不过,最终秦飞还是找到了卖家。如今想来,秦飞不知道是他和溪城人的幸运,还是不幸。
那是秦飞即将返程的最后一天,秦飞照例从看守所,警察局,医院,歌舞厅寻找看起来像吸毒的人,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突破口,但是依旧无果。他询问的人要么骂一句他听不懂的南方粗口,要么就看他一眼快步离开,连搭话的人都没有。
回到旅馆,秦飞准备把最后一支药打了,然后明天就回溪城。还没等关上门,门外一个熟悉的口音传了进来:“哥们儿,你这两天都忙啥呢,住半个多月了吧?”
秦飞回头,从对面房间敞开着的门里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东北的啊?怎么意思?”秦飞问他。
“你进屋,咱俩唠唠。”那人冲秦飞招了招手,秦飞就跟没了魂一样,不由自主的往男人的屋子里走,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半个身子已经进了房门,再想退出来已经晚了。秦飞突然觉得面前的那人有着寻常人没有的气场,让人难以拒绝,而且不怒自威。
“老弟,来嘎哈来了,跟哥哥说说,我没准能帮上你忙,看你也不找工作,也不往回背货,也没人来谈事儿,你大老远从东北到南城,这是来找人了吧?”男人示意秦飞坐,丢了根儿烟给他。
“这事儿你可帮不了我大哥,本来就冒懵儿来的,没想到还真遇不上,找不着就拉到,回去夹着尾巴做人就完了。”秦飞有些失落,垂头丧气的抽着烟。
“瞧出来了,老弟真是范了难了,跟大哥说说怕什么的,难不成就准备折这了?”男人话里有话,但是秦飞依然不敢挑明,虽然是东北老乡,可不知根不知低,跟他说太多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嗯,认栽,牛逼吹炸了,给脸崩了。”秦飞苦笑道:“大哥来南城是嘎哈啊,啥时候回去咱俩搭个伴儿。”
“来取点儿东西,明儿就走。”男人抻了个懒腰,站起身一把抓住秦飞拿着烟的那条胳膊,秦飞一哆嗦,烟头掉落在地上。男人伸脚踩灭,指了指秦飞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来买药吧?”
秦飞暗道不好,脑袋上的汗瞬间就渗了出来,但只能故作镇定,祈祷他不是警察。抬起眼睛看向对方:“啥意思啊大哥,买什么药啊?”
“别跟我装了,我来第一天咱俩并排在卫生间洗脸的时候就看见你这些针眼儿了,东北来南城买药的我看多了。打小针儿的是不是?”男人松开秦飞接着说:“你要说句痛快的,像个老爷们的话,我给你条道儿,你要范倔打死不认,那就拉倒,咱们缘分不够,大哥让你信不过了,也没啥。”
秦飞大口喘着气,心扑腾扑腾地跳,沉默许久,终于咬牙了咬牙,冲着男人点了点头。毕竟自己没有买到,而且打小针撑死拘留,他也不能把自己咋的。
“嗯,没找到正主,都说这里卖那玩意的多,但是没人介绍,进不了人家那个圈儿。”
“哈哈哈哈,可把我给憋死了,看你挺硬个人,怎么遇事儿范怂呢?你身上也没有,你怕什么。”男人走到门口,把门反锁。回过身来坐到秦飞的对面。
“你要找正主,我帮不了你,你要是拿东西,我这有。过一手翻一倍,肯定比正主贵。”男人收起笑容,严肃的对秦飞说。
“多少钱?”秦飞吃惊的看着眼前这个住在自己房间对面的人,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费尽心思找的东西,就离自己一墙之隔。
“先别说多少钱,你家哪的?”
“溪城的。”
“溪城打针的人多少,就说你知道的。”男人掐灭了烟。
“几百个吧,大部分打花针,就是有就打没有就挺着,天天打的不多,几十个吧。”秦飞想了想说到。
“我来这里拿货,一克二百,你到曲市找我拿,一克四百五,那五十是风险钱。明天咱们就回东北,你不用跟我一起走,我不连累人,出了事儿都是自己的。到曲市你也下车,右手边的轻纺招待所住下,等我找你。”男人小声的说。
“为什么愿意给我?咱俩头一回见面,你就不怕我是警察钓鱼的?”秦飞想到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放松了下来。
“大哥我看你挺对我脾气,而且小老弟说话沉稳,所以可以试试,日子长着呢,你要是不是那块料,有第一次就绝对没有第二次。"男人接着说:"至于你说的警察的事儿,你真是不懂法,抓贩毒的至少两名警察以上,一个是为了互相照应,再一个为了互相作证。比如你真的是警察,地下放了五克海洛因,你要抓我是抓不了的,因为你没有证据表明,这药不是你硬塞给我栽赃陷害的,因为这不是我家。”男人狡猾的咧着嘴笑,秦飞才终于明白,贩毒这条道的水有多深。
五
秦飞从曲市回到溪城的时候,老婆和孩子已经跑回了娘家。他把东西藏了起来,然后去接老婆孩子。原来他走的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问,二哥去哪了,钱什么时候还或者东西什么时候带回来。妻子怕耽误孩子学习,没几天就搬回娘家住了。
“哎呀,有点儿事儿耽误了,要不还能早几天。”秦飞惭愧的对老丈母娘说。
“给你屁股擦干净再来接我们娘俩儿,这几天就这住,孩子要期末考试了,我能跟你闹腾,我大儿子可不能让你耽误。”秦飞的老婆数落着秦飞,但是显然已经放下了悬着的心。
秦飞之所以晚了几天,是因为他在曲市和那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大哥学了几天能耐。比如白粉的纯度,口感,色泽怎么分辨,吸食的用量,注射的配比。大哥说,一般情况,由于海洛因价格昂贵,没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是舍不得吸食的,最主要的方式还是注射。不同纯度的海洛因叫法不同,四号,在国内基本不存在,所有能够到达吸毒者手里的海洛因,都是掺杂着大量杂质的劣等品。为了达到快感,只能选择用部分镇定类药品稀释而后注射。
懂了这些,大哥送给他一个黑色的电子秤,这个只有巴掌大的称就是用来称量毒品的,秦飞试了试,竟然精准到毫克。
大哥没有留给秦飞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只是告诉他:“如果你要货,就来这间招待所住下,一般三天,我肯定到,如果超过三天,你就多等三天,可能你来的时候我恰好去拿货。如果再长,你就赶紧走,过半个月再来,连续一个月没看见我,估计我就是出了事儿。当然,我出事儿的可能性很小,以后慢慢跟你说吧。”
王行是第一个知道秦飞回来的人,秦飞列了一项清单,让王行去把海洛因注射的配制小药买齐,走进屋子锁上门,不一会儿就配出了十几矿泉水瓶的透明液体。他把其中药最多的那瓶丢给王行说:“你试试这个,杜冷丁你就再也不想打了,省着点儿,这玩意也不便宜。”
王行略显迟疑的接过塑料瓶,用随身带着的针管吸了一点儿,直接就扎进了血管。药水都推进身体里以后,王行靠在床上,仅仅几分钟,就进入了贤者状态。当他再度清醒的时候,发现秦飞坐在一旁笑呵呵的看着他。
“怎么样,这个劲头行不,上劲儿么?”秦飞问。
“这个比杜冷丁好啊,这个好。”王行由衷的感叹道,真好,真好!
当秦飞把药分别拿给毒友的以后,上门来找秦飞的人就络绎不绝了。但是秦飞记得大哥的话,不能什么人都卖,不能什么风险都担。如果全溪城只有你一家,那就在下面找三个下线。所以王行成了秦飞的三个下线的其中一个,他本身就卖毒品,所以轻车熟路。秦飞按一克800的价钱给王行,把配药的方法也告诉了他,提醒他,多放小药少兑海洛因,一克粉能出1200的药,实在不行,就兑凉水。
从那时起,溪城的吸毒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六
在秦飞卖起海洛因的几年里,溪城乃至全国的毒品圈逐渐分裂成两个派别,镇静类和兴奋类。前者指海洛因,后者指麻古和冰毒。黑话里玩儿白粉儿的,叫热的,溜冰毒的,叫凉的。但是不管凉的热的,那几年溪城都死了太多人。
冰毒起势的前期,八零后逐渐步入吸毒者的行列,效仿国外,抽大麻吃摇头丸。每当儿子和朋友们去迪厅,晚上他都睡不好觉,直到等孩子回来,跟他聊几句,看看儿子的状态是否兴奋异常,才肯接着回屋睡觉。秦飞想,如果儿子吸毒,他一定把他的腿打断,然后宁可就这样养他一辈子。不过,除了不能沾染毒品,秦飞几乎不会关注儿子在做什么。
毒品市场被冰毒冲击,找他买药的人越来越少,他去曲城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不过还是很赚钱。当年身材魁梧的大哥已经骨瘦如柴,但依旧精神抖擞。两个人已经像亲兄弟一般要好,可秦飞依旧只能守在招待所里等着他来。大哥跟秦飞说:“孙子要上学了,自己也差不多金盆洗手不干了。等我收手那天,我把上线交给你,以后你就自己去南城拿货吧。”
秦飞也已经快五十岁,提到毒品,再也不像曾经那样胆战心惊小心翼翼。海洛因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和吃饭睡觉一样寻常。
秦飞平静的说:“你不干了,我也停手。十多年前你给我的这条路,如今你都走不动了,那咱俩就都不走了。”
大哥若有所思的看着秦飞,最后欣慰的点了点头。然后说:“知道为什么我基本不出事儿是为什么么,今天我告诉你,我其实是警察。”
秦飞瞪着眼睛,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七
王行最后一次找他拿药的时候留着眼泪说:“二哥,这药不能打了,真不能打了。”
秦飞沉着脸看王行,不屑的说:“哭什么,你妈死了啊,说事儿,怎么了?”
王行低着头,眼泪噼里啪啦的打在秦飞家客厅的地板上,哽咽着说:“不是我妈,是大林子,还有小艺也死了。头几天二毛来找我拿药,说什么不让我兑,要回家自己配。今天早上他们告诉我,他们三个昨晚吸毒过量,都死二毛家了。二哥,在这样下去,溪城的老弟兄们都活不了。你想想,整个溪城社会圈里,除了你我,谁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咱们做了孽了,我现在天天做噩梦,我快疯了。”
秦飞忽然站起身一脚把王行踹倒,照着王行的脑袋上猛的踢了两脚,浑身颤抖的说:“平常你他妈懒,直接给粉也就算了。这次我特地告诉你纯度高,你他妈的怎么能直接给药,能不打死么?你怎么不打死呢?操你妈的。别人死不死我不管,可我他妈的没说么,不准卖二毛子他们几个药,你想钱想疯了么?我早就答应毛毛,说管着她爸,不让她爸吸毒。王行啊王行,你他妈不是人么?兄弟这么多年,就坏你身上了,都他妈坏你身上了,操你妈的王行,什么事儿都坏你身上,你就是个扫把星!”
说完秦飞也瘫倒在沙发上,他想起二十多岁的时候,和二毛,林子,小艺还有王行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的日子,那会儿没有杜冷丁,也没有海洛因麻古可非冰毒。虽然那时候浑,可都健健康康,和人动起手来吃了亏,三天五天就又生龙活虎的出现在街面上。
可有了毒品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吸毒的人,不爱吃饭,不爱社交,甚至不爱性交。摄入毒品以后,感受快乐的神经被大量透支,从此之后,除了吸毒,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够感到开心快乐。等到静脉被打烂,他们就把海洛因注射进身体的血库里,脖子上,大腿根下。毒瘾更大的,甚至不再使用配药稀释毒品,而是把白粉倒入注射器,抽出身体里的血来稀释海洛因,然后再把混着白粉的血打回身体里,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刚开始吸毒能够达到的快感。
其实秦飞知道,即使没有王行的失误,溪城最早吸毒的一拨人,离死也已经不远了。
秦飞这些年深切的感受到,吸毒者的尊严和生命都一文不值。他碰到过没有钱买毒品就跪在自己家楼下不停磕头的人,遇见过抛妻弃子把房子全都押给秦飞而后拿着药消失不见的人,见过接过药在大街上就脱下裤子往大腿里扎的漂亮女人。他们为了吸一口或者扎一针,可以为秦飞做任何事情,男的愿意为他出去砍人,女的愿意为他脱掉光鲜亮丽的衣服。秦飞最觉得痛心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不再惹祸,每天去市场摆摊卖蔬菜,攒下的钱如数交给秦飞,她说:“我儿子告诉我,这个药溪城就你这里卖的最便宜,你是批发价,我不懂他害了什么病,但是你那个药能治。大兄弟你行行好,卖大娘一点儿。”
在秦飞看来,吸毒的人已经提前过完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用很短的时间得到了极致的幸福感。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只能为这份透支来慢慢还债。包括秦飞自己,他除了不需要为毒资奔波卖命,剩下的和这些人别无两样。
参加完二毛他们的葬礼以后,王行就再也没找秦飞拿过药。道上的朋友告诉秦飞,王行让家人把自己锁在屋里,整整十天,只留最写水和面包香肠。等人们再次见到王行的时候,王行已经不再吸毒,而且逢人就劝:“不吸毒以后连吃饭都比往常香了很多。真好,真好。”
八
第五天,毒瘾渐渐平复了。秦飞把美沙酮和安定倒进卫生间,虽然心瘾还在无时无刻的侵扰着他,但是他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之所以这么多年,他还能相对健康的活着,就是因为他有极强的自控力。这也是后来大哥告诉秦飞,他身上最能让人放心的地方。
王行戒毒以后的日子里,城买得起毒品的人越来越少,秦飞从曲市拿回五十克粉,回来要卖三个月,还经常赊账,或者拿一些东西抵押。大哥把南城的联络人留给了秦飞,又白送给秦飞一批货,就消失不见。他告诉秦飞,如果有一天,真的不想碰了,真能戒掉,就再来这间招待所住下,不然的话,永远也别来曲市。咱们哥俩儿的缘分,差不多也就尽了。
秦飞没有再卖毒品,也没有去南城拿货。大哥留下的白粉够他自己一个人用三年。他买了套新房子,全家悄声无息的就搬走了。又换了电话卡,只留号码给了几个过命的不吸毒的朋友。不过,王行却一次也没有找过他。
别的朋友们偶尔来找秦飞,会告诉他最近溪城的黑道上都发生了什么。
秦飞很好奇,问朋友:“这帮孙子没有白粉了,都戒毒了么?”
“戒个鸡巴,不知道谁在外面传,说你被抓起来了。海洛因再也没有了,要想戒毒,必须用冰毒顶,吸七天冰毒,就再也不用打白粉了。”朋友说。
秦飞哑然失笑,接着问:“那有效果么?”
“要说效果也确实有,就是针管儿变成吸管儿了,现在溪城的吸毒者都在家支着长枪短炮溜冰。你知道那玩意,抽完特能聊,据说还能金枪不倒,持久弥坚。骚冰,困粉儿,都不是好玩意。二哥你这么多年终于收手了,哥们几个都替你高兴,要能戒了可就再好不过了。”朋友说。
海洛因逐渐淡出吸毒者视野以后,冰毒占据了毒品圈的大半个江山。人们说,冰毒好,不上瘾,一个月玩儿几次,没什么影响。男人女人做爱的时候,可以弄一点儿助兴,客户谈生意的时候可以弄一点儿提神,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弄一点儿调节气氛。总之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东西,除了它是毒品,其余没有一点儿负面消息。
甚至秦飞的儿子都跑来问他:“爸,他们说的是真的么,我朋友中间有几个玩儿那个的,那东西不是毒品么,为什么和你卖的不一样呢?”
秦飞看着已经二十来岁的儿子,意味深长的说:“儿子,没有一种毒品的好处会大于坏处。你二毛叔,你林大大他们的下场你也都看见了,甚至可能你老爸也难得善终。我没有资格管你,但是我还是想劝劝你,离吸毒的人远一点,永远不要碰这种东西。”
他和大哥曾经聊过冰毒的事情,自己还特地买了点儿试吸。秦飞发现冰毒某些程度比海洛因更加可怕,因为白粉吸多了,无非就是自己死。但是冰毒吸多了,出现了幻觉,杀人放火什么事儿都可能干得出来。
儿子冷笑了一声:“呵呵,那你为什么还要贩毒?”
秦飞哑口无言,他想对儿子说自己为了赚钱养家,但是他说不出口,因为这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不过是想吸毒,想无忧无虑的得到毒品带给他的快感,赚钱不过是在这个意图之后捎带的事情。
儿子见秦飞没说话,接着说:“你还是戒了吧,像我王行叔那样,我准备把女朋友带回家,你不能再吸毒了。”
“我他妈吸毒跟你带女朋友有什么关系,我给你俩拿钱不就完了么?怎么以后你还能跟我和你妈一起住啊?你他妈找个警察啊?”秦飞突然就炸了,因为他做什么,从小到大都没人管得了,老婆不行,儿子也不行。
“没有,毛毛说了,你一天不戒毒,她一天不登家门。”儿子甩下这句话就摔门走了,丢下秦飞自己在屋里呆呆的发愣。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儿子要带回来的儿媳妇竟然是二毛子的女儿毛毛。
“操你妈,你怎么……她…你不知道…操你妈的!我不同意!”等秦飞回过神来破口大骂的时候,儿子已经出门走了。
秦飞的老婆关掉电视,走进屋子安慰秦飞:“这事儿不能怪孩子,他也不是诚心教叫你为难。人家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俩孩子从小到大,有感情了也是人之常情,你不能因为你们的事儿耽误了孩子的终身大事。”
秦飞捂着脸,眼泪又不争气的流了出来:“我对不起二毛子,我他妈,我他妈没有脸面对毛毛啊!”
秦飞老婆笑道:“我和毛毛谈过了,她喜欢咱们儿子,她爸的事儿也已经过去很久,孩子不恨你,只是想让你把毒品戒了。她不想你和她爸一样的下场,那孩子从小就懂事儿。毛毛说了,她爸走了,嫁到秦家,你就是她爸,你上次答应她的事儿没做到,这次希望你能做到。”
九
戒毒第十天,秦飞当着儿子的面把所有剩下的海洛因都冲进了下水道。一遍放水一遍还和儿子开玩笑:“这下水道里能不能涨出什么妖怪啊,这么多白粉,蛆要是吃了都得变异。”
秦飞的儿子惊奇的看着父亲,良久说不出话来,因为从他记事儿起,父亲就没有开过玩笑。每次看见他的时候,不是在吸毒,就是在贩毒,十几年从未停歇。没参加过自己的家长会,没参加自己大学的毕业礼,甚至有时候连自己多大了都要询问母亲。可是今天,父亲竟然破天荒的和儿子开起了玩笑。
秦飞也们然间意识到,一切好像都和以前不同了。他尴尬的收起笑容,不好意思的搓了搓脸。所有白粉都随着水流冲进下水道以后,秦飞走到窗台边点起只烟,时逢深秋,窗外的街道上的银杏树叶随风飘落,地上铺满了金黄色的落叶。车辆经过,满地的叶子像一层层的金色的巨浪向前涌动,人们踏在金黄里,表情凝重严肃或者欣喜若狂。秦飞不知道他们在难过什么,也不清楚他们在开心什么,他想,一定不是毒品的事儿,至少他不希望是。
秦飞回头看了看正在给女朋友毛毛打电话的儿子,他想,人们应该期盼的是更加真实的将来,无论艰难困苦还是风光无限,都不该和曾经的自己一样,追求毒品带来的短暂虚幻的快乐。
十
没有毒品的世界,真好,真好!
全文完
瑞瑞的江湖系列(一):搓澡的江湖
瑞瑞的江湖系列(二):扒手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