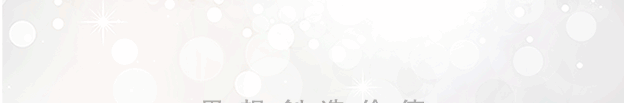近七成被误诊、平均花费5.3年确诊 罕见病诊疗困境需要被“正视”
华夏时报记者 崔笑天 济南报道
“我妈妈希望我长大快乐一点,所以叫我欢颜,我还有个妹妹叫美艳。”说起名字的来历,欢颜显得很开心,她患有成骨不全症,又叫“瓷娃娃”病,患者会频频出现自发性骨折。由于疾病的缘故,她看起来像一个小孩子。
成骨不全症是罕见病的一种,罕见病指的是发病率很低的一类疾病,这些疾病多为疑难杂症,是人类医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目前,国际确认的罕见病有近7000种,只有不到5%的罕见病有有效治疗方法。更令人惋惜的是,罕见病患者有一半都是孩子,他们在出生时或儿童期发病,约30%的罕见病儿童寿命不会超过15岁。

曾经,罕见病不为人所知,如今,随着“冰桶挑战”在全球引发关注,罕见病群体也渐渐走到阳光下,为自己发声,并努力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2018年,中国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以“发病率相对较高、疾病负担较重、可治性较强”为优先标准,收录了包括成骨不全症在内的121种疾病,而这也是中国的罕见病首次被“正名”。
现在,这些罕见病家庭正在尽力转变观念,积极融入社会,但是,无论是诊疗的可及性、教育资源的获得,还是就业等都面临着重重阻碍,需要社会给以他们更多的关注。
![]()
频繁误诊
摆在罕见病患者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疾病难以确诊、频繁误诊。欢颜出生在1992年,当时“瓷娃娃”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她平均每年要骨折2次。家中多次带她前往郑州、洛阳等大城市看求医问药,却失望而归。
“我每次躺在医院里,妈妈都会问医生‘你见过这样的孩子吗?能治吗?’当时没有人见过,也没有医生知道这是什么病。在这个过程中,家里一次次的绝望,我也反复的骨折。”欢颜说,“所以我之前没有治疗过,也不知道有什么治疗方式。像我这个年龄的病友都是这样,病情发展快,身体状况也比较差。”
后来,欢颜的家人只好放弃求医,只是在每次骨折的时候,带她去小医院打个石膏,进行保守治疗。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欢颜没有被错误治疗过。在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工作,她接触到一定比例的病友都有被错误治疗的经历。比如,“瓷娃娃”患者骨折后不能进行常见的钢板手术,因为他们的骨头太脆弱了,钢板手术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但是很多患者被打了钢板,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还有一位患者甚至因为错误治疗引发了严重的骨髓炎,危及到生命。
这并非个例,而是罕见病患者普遍的生存状况。《2018罕见病调研报告》显示,受访的2040位罕见病患者中,有近65%曾经被误诊过;大约有近58%的患者可以在求医的当年获得答案,余下的患者人均需要花费5.3年的时间才能够被确诊;不到四分之一的患者可以在首家求诊的医院获得明确的诊断,其余超过四分之三的患者平均需要去4.5家医院才能被确诊。这4.5家医院指的是当地最好的医院、省里最好的医院,再到北京、上海或广州的多家医院。
年仅9岁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DMD)患者子扬也有过误诊经历。DMD临床表现为缓慢进行性的肌肉萎缩,肌无力,以及不同程度的运动障碍。在子扬妈妈看来,DMD其实很好确诊,做一个心肌酶谱,查出来肌酸激酶特别高,再加上基因检测测出相关突变,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
但是,很多医生对罕见病的认识不足。“当时我们这边的妇幼保健院说孩子就是肝功损害,需要保肝治疗,治了两个多月也没好,后来推荐我们去传染病医院,也让住院治疗;最后到了省立医院才确诊为DMD。”子扬妈妈说。
对这些罕见病患者来说,频繁误诊带来的不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与家庭的绝望,更意味着疾病最佳的治疗时期被延误。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病痛挑战基金会项目总监孙荣甲曾经遇到一个贵州的“瓷娃娃”孩子,虽然疾病进展不太严重,但是从小到大在当地一直被误诊,做钢板,还喝了约10万块钱的中药。10年后,这个孩子才找到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这个时候他的腿骨质已经严重流失。“刚出生的时候孩子还会走路,如果接受正确治疗的话,他正常的学习、生活都没有问题。而且,他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误诊花光了他们几十万的积蓄,找到我们时已经拿不出钱做正确的治疗了。”孙荣甲感慨。
虽然罕见病的概念已经被社会关注,但是,部分医生对罕见病的认识依旧不足,除频繁误诊外,这也会导致很多罕见病患者出现其他疾病时,治疗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往往被忽视。子扬妈妈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前一段时间子扬摔倒了,鼻骨骨折错位,需要做手术。但是DMD的孩子在做手术的时候不能使用肌松类的药,不然会对孩子的呼吸有抑制作用,要是剂量控制不好的话,孩子可能就要永久使用呼吸机。“我当时需要和医生讲得特别详细他们才明白。我想呼吁一下医生朋友,多了解一些罕见病的知识。”子扬妈妈说。
孙荣甲告诉本报记者,罕见病诊治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病痛挑战基金会的罕见病医疗援助工程至今已接受了近40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求助,其中大约70%都在北京确诊。罕见病医疗援助工程的项目数据显示,诊治罕见病的前10家医院有6家在北京,2家是在上海,1家在重庆,1家在山东。
值得注意的是,确诊与治疗还存在错配。比如罕见病确诊大多在综合医院,但是后续的治疗则不一定,因为诊断和治疗不在一个部门。因此,多学科会诊(MDT)也成为罕见病重要的一种诊疗手段。
目前,为了改善罕见病患者的诊疗状况,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病痛挑战基金会等公益机构会不定期组织巡诊活动,带着对罕见病有经验的专家团队,去各地医院为医生做培训,也为地方患者义诊。
![]()
囿于孤独
除了有限的诊疗资源,罕见病患者也有社会生活的需要,他们渴望被人接纳、与人交流,更期待像普通人一样上学、就业。但是在这方面,无论是罕见病患者的家庭,还是学校、公司,均有不足之处。
一方面,有一定比例的学校、公司不愿意接收罕见病患者。据《华夏时报》记者了解,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会在每年的开学季接到很多家长的求助,很多学校不愿意让这些孩子入学,导致他们享受不到义务教育。对此,有一些家长选择陪读,也有一些家长与学校签免责协议,想尽办法让孩子上学。
另一方面,罕见病患者的家人也难以下定决心让他们主动去融入社会,或者在自己的陪伴下接触社会。这其中,有对于孩子病情、身体状况的担忧,也有“面子问题”。
24岁之前,欢颜一直呆在家里,除了“办身份证”这种大事,几乎足不出户。“曾经一间屋子一个电视就是我的世界。”欢颜说,“因为骨折太频繁,学习跟不上,也没有老师辅导,上完小学我就辍学在家。平时几乎不出门,如果电视没有节目的话,我就会很抓狂,觉得这一天无聊到没法过。”
但实际上,这些患者在内心是非常渴望与人接触、交往的。子扬妈妈在济南发起了DMD的病友组织,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她说,最初见到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小脸都挺抑郁的,但是走的时候都笑得很阳光,恋恋不舍的。
子扬妈妈曾见过一个10岁孩子的家长,他的孩子学习非常好,基本上在学校里都考年级前一二名,但是当他的孩子病情严重、不能行走的时候,他就不让孩子上学了。每次带着孩子从家里出去的时候要坐小三轮车,从来不敢让孩子坐着轮椅,他推着出去。
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家长与孩子共同努力去面对。子扬妈妈其实很理解家长的心态,“当时我孩子摔跟头,走路有点困难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有顾虑的,‘孩子坐轮椅了,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会不会碰到那种眼光?’但是后来我就在想,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快乐重要?我想通了,就跟孩子说,没事孩子,只不过是你走路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你用轮椅代步,你和别人没啥区别。”而一开始子扬也拒绝坐轮椅。“他让我把小轮椅推着,走出家门大概二三百米远,好像没有邻居、熟人了,没有同学了,再坐到小轮椅上。即便是这样,我也坚持一周把他推着出去一两次,当他真正一点也不能走的时候,再坐上轮椅就特别坦然。”子扬妈妈说。
子扬妈妈是一名单亲妈妈,独自承担起赚钱养家、照顾儿子等两个人都很难承受的重担,“我老公是个军人,在特殊岗位工作,在2014年的时候查出肺癌晚期,到2017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每天需要工作,还要带孩子。”但是,她依然坚持把孩子送到正常的学校中与其他小朋友一起上课。紧张的日程使得子扬妈妈天天要“三头跑”,先在早晨把子扬送到学校,再跑去上班,上午十一点再去把儿子接回家,下午还要带他去医院做康复训练。
即便是这么忙碌,她也从未想过不让儿子去上学。“我们的孩子基本上只有20岁左右的生命。在有限的生命里,我希望这些家庭能带孩子走出来,尽量让他去上学,不能上学的话,至少得要有个家长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子扬妈妈说,“子扬从上学开始到现在,没在学校上过一次厕所,都是我回来后给他接个小便,再把他从轮椅上抱下来,让他稍微站一下,但是他站也是站不住的,需要依靠我的力量,我就一直搂着他的腰,用自己的力气让他稍微能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
![]()
在阳光下生活
“假如说我们的孩子能活一天,我就希望他能在阳光下去生活。我不喜欢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子扬妈妈说。
对于罕见病患者来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数据显示,罕见病患者有一半都是孩子,他们在出生时或儿童期发病,约30%的罕见病儿童寿命不会超过15岁。在子扬妈妈发起的DMD病友组织中,去年有4个孩子去世,最大的一个20多岁,最小的一个才14岁,有的孩子在睡梦中就去世了。
“医生说‘瓷娃娃’病18岁趋于稳定,30岁之后骨密度就开始下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自己只有10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件事情,挺绝望的。”欢颜说。但她却做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来到北京的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工作。一开始,家人不支持她来北京,担心她骨折,更担心她没人依靠,但最终她还是说服了家人,在24岁时迈出了离开家的第一步。
欢颜向记者描述那种兴奋,“出来的感觉特别好,我自己想去哪就去哪,没有限制,这就是自由。”这给她性格带来的变化几乎是颠覆性的,曾经看着她成长的人都十分惊讶,“我之前的性格特别封闭自卑内向,不会讲话,语言特别混乱,逻辑什么的都不行。随着社会接触越来越多,慢慢才打开了自己。”
曾经令欢颜害怕的骨折也不再成为难以克服的困难,2019年下半年,她摔倒导致骨裂。“骨折的时候,我脑海里就回想着我妈妈说的那些话,‘你骨折了怎么办?谁来照顾你?’但是整个过程下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我到医院打了个石膏,然后回到住的地方,第二天还能坐着轮椅架着腿去上班。”欢颜说。
在他们勇敢“走出来”的过程中,社会对于罕见病群体的认知与接纳度也在不断提升。比如,“挤地铁”这样一件令上班族叫苦不迭的事,欢颜却很喜欢,“在挤地铁的时候我感觉融入了大家,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可以也挤地铁上下班。”她笑称轮椅在高峰期其实是对自己的“保护”,地铁的工作人员看到她,会主动帮她推到地铁上,再通报下一站的工作人员来接,“北京地铁的服务还是很好的。”
还有,子扬妈妈也会遇到一些退休的阿姨主动提出帮她接小孩,中国残联会为她提供每周4个小时的居家服务。“虽然可能也有挺伤人的眼光,但是我都特别坦然,没觉得怎么样。”她笑说。
走出家门是一切的开始,一个个罕见病家庭需要的是帮助,更是接纳。如今,罕见病群体已达到近2000万,他们并不罕见,只是需要被“看见”。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