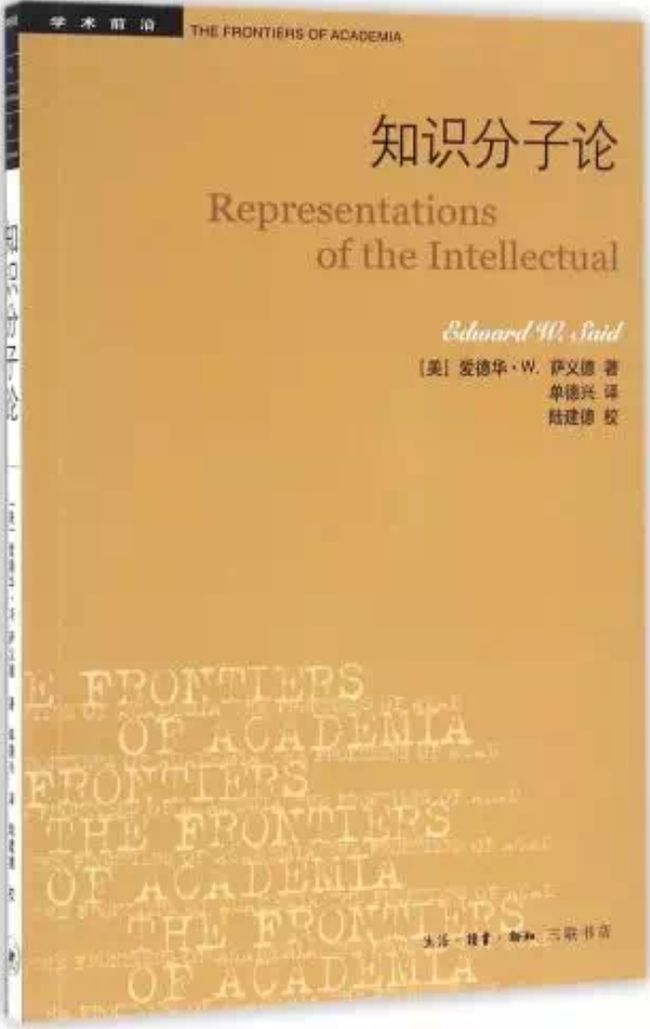- 斤斤计较的婚姻到底有多难?
白心之岂必有为
很多人私聊我会问到在哪个人群当中斤斤计较的人最多?我都会回答他,一般婚姻出现问题的斤斤计较的人士会非常多,以我多年经验,在婚姻落的一塌糊涂的人当中,斤斤计较的人数占比在20~30%以上,也就是说10个婚姻出现问题的斤斤计较的人有2-3个有多不减。在婚姻出问题当中,有大量的心理不平衡的、尖酸刻薄的怨妇。在婚姻中仅斤斤计较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物质上的,另一种是精神上的。在物质与精神上抠门已经严重的影响
- 芦花鞋一四
许叶晗
又是在一个寒冷的夏日里,青铜和葵花决定今天一起去卖芦花鞋,奶奶亲手给他们做了一碗热乎乎的粥对他们说:“就靠你们两挣生活费了这碗粥赶紧趁热喝了吧!”于是青铜和葵花喝完了奶奶给她们做的粥,就准备去镇上卖卢花鞋,这回青铜和葵花穿着新的芦花鞋来到了镇上。青铜这回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卖,用手势表达对葵花说:“这回有好多人在抢我们生意呢!我们必须得吆喝起来。”葵花点了点头。可是谁知他们也大声的叫,卖芦花喽!卖芦花
- 铭刻于星(四十二)
随风至
69夜晚,绍敏同学做完功课后,看了眼房外,没听到动静才敢从书包的夹层里拿出那个心形纸团。折痕压得很深,都有些旧了,想来是已经写好很久了。绍敏同学慢慢地、轻轻地捏开折叠处,待到全部拆开后,又反复抚平纸张,然后仔细地一字字默看。只是开头的三个字是第一次看到,让她心漏跳了几拍。“亲爱的绍敏:从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说,怕影响你学习。六年级的时候听说有人跟你表白,你接受了,我很难过,但
- 底层逆袭到底有多难,不甘平凡的你准备好了吗?让吴起给你说说
造命者说
底层逆袭到底有多难,不甘平凡的你准备好了吗?让吴起给你说说我叫吴起,生于公元前440年的战国初期,正是群雄并起、天下纷争不断的时候。后人说我是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是兵家代表人物。评价我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因变法得罪守旧贵族,被人乱箭射死。我出生在卫国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从年轻时候起就不甘平凡
- 2020-01-25
晴岚85
郑海燕坚持分享590天2020.1.24在生活中只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达成;另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前一个是行动的问题,后一个是结果的问题。通过制定具体的下一步行动,可以解决不知道如何开始行动的问题。而通过去想象结果,对结果做预估,可以解决找不着目标的问题。对于所有吸引我们注意力,想要完成的任务,你可以先想象一下,预期的结果究竟是什
- 随笔 | 仙一般的灵气
海思沧海
仙岛今天,我看了你全部,似乎已经进入你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梦幻,还是你仙一般的灵气吸引了我也许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追求,这样才能够符合人生的梦想,生活才能够充满着阳光与快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叹,是在感叹自己的人生,还是感叹自己一直没有孜孜不倦的追求只感觉虚度了光阴,每天活在自己的梦中,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是在逃避自己,还是在逃避周围的一切有时候我嘲笑自己,嘲笑自己如此的虚无,
- 【iOS】MVC设计模式
Magnetic_h
iosmvc设计模式objective-c学习ui
MVC前言如何设计一个程序的结构,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叫做"架构模式"(architecturalpattern),属于编程的方法论。MVC模式就是架构模式的一种。它是Apple官方推荐的App开发架构,也是一般开发者最先遇到、最经典的架构。MVC各层controller层Controller/ViewController/VC(控制器)负责协调Model和View,处理大部分逻辑它将数据从Mod
- OC语言多界面传值五大方式
Magnetic_h
iosui学习objective-c开发语言
前言在完成暑假仿写项目时,遇到了许多需要用到多界面传值的地方,这篇博客来总结一下比较常用的五种多界面传值的方式。属性传值属性传值一般用前一个界面向后一个界面传值,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访问后一个视图控制器的属性来为它赋值,通过这个属性来做到从前一个界面向后一个界面传值。首先在后一个界面中定义属性@interfaceBViewController:UIViewController@propertyNSSt
- UI学习——cell的复用和自定义cell
Magnetic_h
ui学习
目录cell的复用手动(非注册)自动(注册)自定义cellcell的复用在iOS开发中,单元格复用是一种提高表格(UITableView)和集合视图(UICollectionView)滚动性能的技术。当一个UITableViewCell或UICollectionViewCell首次需要显示时,如果没有可复用的单元格,则视图会创建一个新的单元格。一旦这个单元格滚动出屏幕,它就不会被销毁。相反,它被添
- element实现动态路由+面包屑
软件技术NINI
vue案例vue.js前端
el-breadcrumb是ElementUI组件库中的一个面包屑导航组件,它用于显示当前页面的路径,帮助用户快速理解和导航到应用的各个部分。在Vue.js项目中,如果你已经安装了ElementUI,就可以很方便地使用el-breadcrumb组件。以下是一个基本的使用示例:安装ElementUI(如果你还没有安装的话):你可以通过npm或yarn来安装ElementUI。bash复制代码npmi
- 10月|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读书笔记-01
Tracy的小书斋
本书的作者是俞敏洪,大家都很熟悉他了吧。俞敏洪老师是我行业的领头羊吧,也是我事业上的偶像。本日摘录他书中第一章中的金句:『一个人如果什么目标都没有,就会浑浑噩噩,感觉生命中缺少能量。能给我们能量的,是对未来的期待。第一件事,我始终为了进步而努力。与其追寻全世界的骏马,不如种植丰美的草原,到时骏马自然会来。第二件事,我始终有阶段性的目标。什么东西能给我能量?答案是对未来的期待。』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便
- 谢谢你们,爱你们!
鹿游儿
昨天家人去泡温泉,二个孩子也带着去,出发前一晚,匆匆下班,赶回家和孩子一起收拾。饭后,我拿出笔和本子(上次去澳门时做手帐的本子)写下了1\2\3\4\5\6\7\8\9,让后让小壹去思考,带什么出发去旅游呢?她在对应的数字旁边画上了,泳衣、泳圈、肖恩、内衣内裤、tapuy、拖鞋……画完后,就让她自己对着这个本子,将要带的,一一带上,没想到这次带的书还是这本《便便工厂》(晚上姑婆发照片过来,妹妹累得
- C语言如何定义宏函数?
小九格物
c语言
在C语言中,宏函数是通过预处理器定义的,它在编译之前替换代码中的宏调用。宏函数可以模拟函数的行为,但它们不是真正的函数,因为它们在编译时不会进行类型检查,也不会分配存储空间。宏函数的定义通常使用#define指令,后面跟着宏的名称和参数列表,以及宏展开后的代码。宏函数的定义方式:1.基本宏函数:这是最简单的宏函数形式,它直接定义一个表达式。#defineSQUARE(x)((x)*(x))2.带参
- 理解Gunicorn:Python WSGI服务器的基石
范范0825
ipythonlinux运维
理解Gunicorn:PythonWSGI服务器的基石介绍Gunicorn,全称GreenUnicorn,是一个为PythonWSGI(WebServerGatewayInterface)应用设计的高效、轻量级HTTP服务器。作为PythonWeb应用部署的常用工具,Gunicorn以其高性能和易用性著称。本文将介绍Gunicorn的基本概念、安装和配置,帮助初学者快速上手。1.什么是Gunico
- 小丽成长记(四十三)
玲玲54321
小丽发现,即使她好不容易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下一秒总会有不确定的伤脑筋的事出现,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人生就没有停下的时候,小问题不断出现。不过她今天看的书,她接受了人生就是不确定的,厉害的人就是不断创造确定性,在Ta的领域比别人多的确定性就能让自己脱颖而出,显示价值从而获得的比别人多的利益。正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从前修炼自己太少,使得她现在在人生道路上打怪起来困难重重,她似乎永远摆脱不了那种无力感,有种习
- 学点心理知识,呵护孩子健康
静候花开_7090
昨天听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张玲老师的《哪里才是学生心理健康的最后庇护所,超越教育与技术的思考》的讲座。今天又重新学习了一遍,收获匪浅。张玲博士也注意到了当今社会上的孩子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自残、自杀及伤害他人等恶性事件。她向我们普及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她说心理健康的一些基本命题,我们与我们通常的一些教育命题是不同的,她还举了几个例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原来以为的健康并非心理学上的健康。比如如果
- 瑶池防线
谜影梦蝶
冥华虽然逃过了影梦的军队,但他是一个忠臣,他选择上报战况。败给影梦后成逃兵,高层亡尔还活着,七重天失守......随便一条,即可处死冥华。冥华自然是知道以仙界高层的习性此信一发自己必死无疑,但他还选择上报实情,因为责任。同样此信送到仙宫后,知道此事的人,大多数人都认定冥华要完了,所以上到仙界高层,下到扫大街的,包括冥华自己,全都准备好迎接冥华之死。如果仙界现在还属于两方之争的话,冥华必死无疑。然而
- 《策划经理回忆录之二》
路基雅虎
话说三年变六年,飘了,飘了……眨眼,2013年5月,老吴回到了他的家乡——油城从新开启他的工作幻想症生涯。很庆幸,这是一家很有追求,同时敢于尝试的,且实力不容低调的新星房企——金源置业(前身泰源置业)更值得庆幸的是第一个盘就是油城十路的标杆之一:金源盛世。2013年5月,到2015年11月,两年的陪伴,迎来了一场大爆发。2000个筹,5万/筹,直接回笼1个亿!!!这……让我开始认真审视这座看似五线
- Long类型前后端数据不一致
igotyback
前端
响应给前端的数据浏览器控制台中response中看到的Long类型的数据是正常的到前端数据不一致前后端数据类型不匹配是一个常见问题,尤其是当后端使用Java的Long类型(64位)与前端JavaScript的Number类型(最大安全整数为2^53-1,即16位)进行数据交互时,很容易出现精度丢失的问题。这是因为JavaScript中的Number类型无法安全地表示超过16位的整数。为了解决这个问
- 如何在 Fork 的 GitHub 项目中保留自己的修改并同步上游更新?github_fork_update
iBaoxing
github
如何在Fork的GitHub项目中保留自己的修改并同步上游更新?在GitHub上Fork了一个项目后,你可能会对项目进行一些修改,同时原作者也在不断更新。如果想要在保留自己修改的基础上,同步原作者的最新更新,很多人会不知所措。本文将详细讲解如何在不丢失自己改动的情况下,将上游仓库的更新合并到自己的仓库中。问题描述假设你在GitHub上Fork了一个项目,并基于该项目做了一些修改,随后你发现原作者对
- 扫地机类清洁产品之直流无刷电机控制
悟空胆好小
清洁服务机器人单片机人工智能
扫地机类清洁产品之直流无刷电机控制1.1前言扫地机产品有很多的电机控制,滚刷电机1个,边刷电机1-2个,清水泵电机,风机一个,部分中高端产品支持抹布功能,也就是存在抹布盘电机,还有追觅科沃斯石头等边刷抬升电机,滚刷抬升电机等的,这些电机有直流有刷电机,直接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电磁阀,挪动泵等不同类型。电机的原理,驱动控制方式也不行。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几个文章会作个专题分析分享。直流有刷电机会自动持续
- 绘本讲师训练营【24期】8/21阅读原创《独生小孩》
1784e22615e0
24016-孟娟《独生小孩》图片发自App今天我想分享一个蛮特别的绘本,讲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是属于这个群体,80后的独生小孩。这是一本中国绘本,作者郭婧,也是一个80厚。全书一百多页,均为铅笔绘制,虽然为黑白色调,但并不显得沉闷。全书没有文字,犹如“默片”,但并不影响读者对该作品的理解,反而显得神秘,梦幻,給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作者在前蝴蝶页这样写到:“我更希望父母和孩子一起分享这本书,使他
- 30天风格练习-DAY2
黄希夷
Day2(重义)在一个周日/一周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位于市中心/市区繁华地带的一家购物中心/商场,中心内人很多/熙熙攘攘。我注意到/看见一个独行/孤身一人的年轻女孩/,留着一头引人注目/长过腰际的头发,上身穿一件暗红色/比正红色更深的衣服/穿在身体上的东西。走下扶梯的时候,她摔倒了/跌向地面,在她正要站起来/让身体离开地面的时候,过长/超过一般人长度的头发被支撑身体/躯干的手掌压/按在下面,她赶紧用
- 消息中间件有哪些常见类型
xmh-sxh-1314
java
消息中间件根据其设计理念和用途,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常见类型:点对点消息队列(Point-to-PointMessagingQueues):在这种模型中,消息被发送到特定的队列中,消费者从队列中取出并处理消息。队列中的消息只能被一个消费者消费,消费后即被删除。常见的实现包括IBM的MQSeries、RabbitMQ的部分使用场景等。适用于任务分发、负载均衡等场景。发布/订阅消息模型(Pub/Sub
- 高级编程--XML+socket练习题
masa010
java开发语言
1.北京华北2114.8万人上海华东2,500万人广州华南1292.68万人成都华西1417万人(1)使用dom4j将信息存入xml中(2)读取信息,并打印控制台(3)添加一个city节点与子节点(4)使用socketTCP协议编写服务端与客户端,客户端输入城市ID,服务器响应相应城市信息(5)使用socketTCP协议编写服务端与客户端,客户端要求用户输入city对象,服务端接收并使用dom4j
- 抖音乐买买怎么加入赚钱?赚钱方法是什么
测评君高省
你会在抖音买东西吗?如果会,那么一定要免费注册一个乐买买,抖音直播间,橱窗,小视频里的小黄车买东西都可以返佣金!省下来都是自己的,分享还可以赚钱乐买买是好省旗下的抖音返佣平台,乐买买分析社交电商的价值,乐买买属于今年难得的副业项目风口机会,2019年错过做好省的搞钱的黄金时期,那么2022年千万别再错过乐买买至于我为何转到高省呢?当然是高省APP佣金更高,模式更好,终端用户不流失。【高省】是一个自
- 那个抄袭的大张伟
猫小努
最近一直在追《即刻电音》这个综艺,除了觉得出场节目的音乐制作人有意思之外,也觉得有两个导师挺有趣的(另外一个就忽略了吧)。孙艺兴在上一篇文章里面已经说过了,那么这篇就说说我们的大老师,大张伟吧。其实在节目刚开始大张伟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属于导师里面来活跃气氛负责搞笑的,毕竟孙艺兴属于卖萌卖傻卖老实的,尚雯婕一般负责装逼耍狠的,而大张伟一贯以来上综艺的形象基本上都是蹦蹦跳跳带动气氛的。谁知道,两期
- 三大师传
beca酱
巴尔扎克的作品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是:“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一个原本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从地中海的某个海岛上,只身一人来到巴黎,没有朋友,也没有名望。作为一个一文不名的外乡人,凭着赤手空拳赢得了巴黎,征服了整个法兰西,并且赢得了世界。这个人就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
- 开心
蒋泳频
从无比抗拒来上课到接受,感动,收获~看着波哥成长,晶晶幸福笑容满面。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很开心!还有3个感召目标就是还有三个有缘人,哈哈。明天感召去明日计划:8:30-11:00小公益11:00-21点上班,感召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
- 2018-07-23-催眠日作业-#不一样的31天#-66小鹿
小鹿_33
预言日:人总是在逃避命运的路上,与之不期而遇。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名词,叫做自证预言;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定律叫做,墨菲定律;在灵修派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则,叫做吸引力法则。这3个领域的词,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在告诉人们一个现象:你越担心什么,就越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同样的道理,你越想得到什么,就应该要积极地去创造什么。无论是自证预言,墨菲定律还是吸引力法则,对人都有正反2个维度的影响
- ASM系列五 利用TreeApi 解析生成Class
lijingyao8206
ASM字节码动态生成ClassNodeTreeAPI
前面CoreApi的介绍部分基本涵盖了ASMCore包下面的主要API及功能,其中还有一部分关于MetaData的解析和生成就不再赘述。这篇开始介绍ASM另一部分主要的Api。TreeApi。这一部分源码是关联的asm-tree-5.0.4的版本。
在介绍前,先要知道一点, Tree工程的接口基本可以完
- 链表树——复合数据结构应用实例
bardo
数据结构树型结构表结构设计链表菜单排序
我们清楚:数据库设计中,表结构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程序的复杂度。所以,本文就无限级分类(目录)树与链表的复合在表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探讨。当然,什么是树,什么是链表,这里不作介绍。有兴趣可以去看相关的教材。
需求简介:
经常遇到这样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将保存在数据库中的树结构能够按确定的顺序读出来。比如,多级菜单、组织结构、商品分类。更具体的,我们希望某个二级菜单在这一级别中就是第一个。虽然它是最后
- 为啥要用位运算代替取模呢
chenchao051
位运算哈希汇编
在hash中查找key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用&取代%,先看两段代码吧,
JDK6中的HashMap中的indexFor方法:
/**
* Returns index for hash code h.
*/
static int indexFor(int h, int length) {
- 最近的情况
麦田的设计者
生活感悟计划软考想
今天是2015年4月27号
整理一下最近的思绪以及要完成的任务
1、最近在驾校科目二练车,每周四天,练三周。其实做什么都要用心,追求合理的途径解决。为
- PHP去掉字符串中最后一个字符的方法
IT独行者
PHP字符串
今天在PHP项目开发中遇到一个需求,去掉字符串中的最后一个字符 原字符串1,2,3,4,5,6, 去掉最后一个字符",",最终结果为1,2,3,4,5,6 代码如下:
$str = "1,2,3,4,5,6,";
$newstr = substr($str,0,strlen($str)-1);
echo $newstr;
- hadoop在linux上单机安装过程
_wy_
linuxhadoop
1、安装JDK
jdk版本最好是1.6以上,可以使用执行命令java -version查看当前JAVA版本号,如果报命令不存在或版本比较低,则需要安装一个高版本的JDK,并在/etc/profile的文件末尾,根据本机JDK实际的安装位置加上以下几行:
export JAVA_HOME=/usr/java/jdk1.7.0_25
- JAVA进阶----分布式事务的一种简单处理方法
无量
多系统交互分布式事务
每个方法都是原子操作:
提供第三方服务的系统,要同时提供执行方法和对应的回滚方法
A系统调用B,C,D系统完成分布式事务
=========执行开始========
A.aa();
try {
B.bb();
} catch(Exception e) {
A.rollbackAa();
}
try {
C.cc();
} catch(Excep
- 安墨移动广 告:移动DSP厚积薄发 引领未来广 告业发展命脉
矮蛋蛋
hadoop互联网
“谁掌握了强大的DSP技术,谁将引领未来的广 告行业发展命脉。”2014年,移动广 告行业的热点非移动DSP莫属。各个圈子都在纷纷谈论,认为移动DSP是行业突破点,一时间许多移动广 告联盟风起云涌,竞相推出专属移动DSP产品。
到底什么是移动DSP呢?
DSP(Demand-SidePlatform),就是需求方平台,为解决广 告主投放的各种需求,真正实现人群定位的精准广
- myelipse设置
alafqq
IP
在一个项目的完整的生命周期中,其维护费用,往往是其开发费用的数倍。因此项目的可维护性、可复用性是衡量一个项目好坏的关键。而注释则是可维护性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注释模板导入步骤
安装方法:
打开eclipse/myeclipse
选择 window-->Preferences-->JAVA-->Code-->Code
- java数组
百合不是茶
java数组
java数组的 声明 创建 初始化; java支持C语言
数组中的每个数都有唯一的一个下标
一维数组的定义 声明: int[] a = new int[3];声明数组中有三个数int[3]
int[] a 中有三个数,下标从0开始,可以同过for来遍历数组中的数
- javascript读取表单数据
bijian1013
JavaScript
利用javascript读取表单数据,可以利用以下三种方法获取:
1、通过表单ID属性: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x_x_x("id");
2、通过表单名称属性:var b = document.getElementsByName("name");
3、直接通过表单名字获取:var c = form.content.
- 探索JUnit4扩展:使用Theory
bijian1013
javaJUnitTheory
理论机制(Theory)
一.为什么要引用理论机制(Theory)
当今软件开发中,测试驱动开发(TDD — Test-driven development)越发流行。为什么 TDD 会如此流行呢?因为它确实拥有很多优点,它允许开发人员通过简单的例子来指定和表明他们代码的行为意图。
TDD 的优点:
&nb
- [Spring Data Mongo一]Spring Mongo Template操作MongoDB
bit1129
template
什么是Spring Data Mongo
Spring Data MongoDB项目对访问MongoDB的Java客户端API进行了封装,这种封装类似于Spring封装Hibernate和JDBC而提供的HibernateTemplate和JDBCTemplate,主要能力包括
1. 封装客户端跟MongoDB的链接管理
2. 文档-对象映射,通过注解:@Document(collectio
- 【Kafka八】Zookeeper上关于Kafka的配置信息
bit1129
zookeeper
问题:
1. Kafka的哪些信息记录在Zookeeper中 2. Consumer Group消费的每个Partition的Offset信息存放在什么位置
3. Topic的每个Partition存放在哪个Broker上的信息存放在哪里
4. Producer跟Zookeeper究竟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consumers、config、brokers、cont
- java OOM内存异常的四种类型及异常与解决方案
ronin47
java OOM 内存异常
OOM异常的四种类型:
一: StackOverflowError :通常因为递归函数引起(死递归,递归太深)。-Xss 128k 一般够用。
二: out Of memory: PermGen Space:通常是动态类大多,比如web 服务器自动更新部署时引起。-Xmx
- java-实现链表反转-递归和非递归实现
bylijinnan
java
20120422更新:
对链表中部分节点进行反转操作,这些节点相隔k个:
0->1->2->3->4->5->6->7->8->9
k=2
8->1->6->3->4->5->2->7->0->9
注意1 3 5 7 9 位置是不变的。
解法:
将链表拆成两部分:
a.0-&
- Netty源码学习-DelimiterBasedFrameDecoder
bylijinnan
javanetty
看DelimiterBasedFrameDecoder的API,有举例:
接收到的ChannelBuffer如下:
+--------------+
| ABC\nDEF\r\n |
+--------------+
经过DelimiterBasedFrameDecoder(Delimiters.lineDelimiter())之后,得到:
+-----+----
- linux的一些命令 -查看cc攻击-网口ip统计等
hotsunshine
linux
Linux判断CC攻击命令详解
2011年12月23日 ⁄ 安全 ⁄ 暂无评论
查看所有80端口的连接数
netstat -nat|grep -i '80'|wc -l
对连接的IP按连接数量进行排序
netstat -ntu | awk '{print $5}' | cut -d: -f1 | sort | uniq -c | sort -n
查看TCP连接状态
n
- Spring获取SessionFactory
ctrain
sessionFactory
String sql = "select sysdate from dual";
WebApplicationContext wac = ContextLoader.getCurrentWebApplicationContext();
String[] names = wac.getBeanDefinitionNames();
for(int i=0; i&
- Hive几种导出数据方式
daizj
hive数据导出
Hive几种导出数据方式
1.拷贝文件
如果数据文件恰好是用户需要的格式,那么只需要拷贝文件或文件夹就可以。
hadoop fs –cp source_path target_path
2.导出到本地文件系统
--不能使用insert into local directory来导出数据,会报错
--只能使用
- 编程之美
dcj3sjt126com
编程PHP重构
我个人的 PHP 编程经验中,递归调用常常与静态变量使用。静态变量的含义可以参考 PHP 手册。希望下面的代码,会更有利于对递归以及静态变量的理解
header("Content-type: text/plain");
function static_function () {
static $i = 0;
if ($i++ < 1
- Android保存用户名和密码
dcj3sjt126com
android
转自:http://www.2cto.com/kf/201401/272336.html
我们不管在开发一个项目或者使用别人的项目,都有用户登录功能,为了让用户的体验效果更好,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功能,叫做保存用户,这样做的目地就是为了让用户下一次再使用该程序不会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这里我使用3种方式来存储用户名和密码
1、通过普通 的txt文本存储
2、通过properties属性文件进行存
- Oracle 复习笔记之同义词
eksliang
Oracle 同义词Oracle synonym
转载请出自出处: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098861
1.什么是同义词
同义词是现有模式对象的一个别名。
概念性的东西,什么是模式呢?创建一个用户,就相应的创建了 一个模式。模式是指数据库对象,是对用户所创建的数据对象的总称。模式对象包括表、视图、索引、同义词、序列、过
- Ajax案例
gongmeitao
Ajaxjsp
数据库采用Sql Server2005
项目名称为:Ajax_Demo
1.com.demo.conn包
package com.demo.conn;
import java.sql.Connection;import java.sql.DriverManager;import java.sql.SQLException;
//获取数据库连接的类public class DBConnec
- ASP.NET中Request.RawUrl、Request.Url的区别
hvt
.netWebC#asp.nethovertree
如果访问的地址是:http://h.keleyi.com/guestbook/addmessage.aspx?key=hovertree%3C&n=myslider#zonemenu那么Request.Url.ToString() 的值是:http://h.keleyi.com/guestbook/addmessage.aspx?key=hovertree<&
- SVG 教程 (七)SVG 实例,SVG 参考手册
天梯梦
svg
SVG 实例 在线实例
下面的例子是把SVG代码直接嵌入到HTML代码中。
谷歌Chrome,火狐,Internet Explorer9,和Safari都支持。
注意:下面的例子将不会在Opera运行,即使Opera支持SVG - 它也不支持SVG在HTML代码中直接使用。 SVG 实例
SVG基本形状
一个圆
矩形
不透明矩形
一个矩形不透明2
一个带圆角矩
- 事务管理
luyulong
javaspring编程事务
事物管理
spring事物的好处
为不同的事物API提供了一致的编程模型
支持声明式事务管理
提供比大多数事务API更简单更易于使用的编程式事务管理API
整合spring的各种数据访问抽象
TransactionDefinition
定义了事务策略
int getIsolationLevel()得到当前事务的隔离级别
READ_COMMITTED
- 基础数据结构和算法十一:Red-black binary search tree
sunwinner
AlgorithmRed-black
The insertion algorithm for 2-3 trees just described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now, we will see that it is also not difficult to implement. We will consider a simple representation known
- centos同步时间
stunizhengjia
linux集群同步时间
做了集群,时间的同步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以下是查到的如何做时间同步。 在CentOS 5不再区分客户端和服务器,只要配置了NTP,它就会提供NTP服务。 1)确认已经ntp程序包: # yum install ntp 2)配置时间源(默认就行,不需要修改) # vi /etc/ntp.conf server pool.ntp.o
- ITeye 9月技术图书有奖试读获奖名单公布
ITeye管理员
ITeye
ITeye携手博文视点举办的9月技术图书有奖试读活动已圆满结束,非常感谢广大用户对本次活动的关注与参与。 9月试读活动回顾:http://webmaster.iteye.com/blog/2118112本次技术图书试读活动的优秀奖获奖名单及相应作品如下(优秀文章有很多,但名额有限,没获奖并不代表不优秀):
《NFC:Arduino、And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