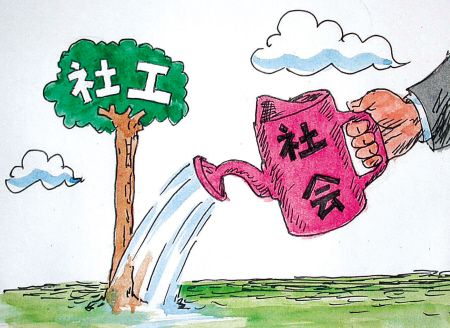本土化(Indigenization)这个词,虽然听起来颇为理论和专业,但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本土化的探索,小到沙县小吃开遍全国、青岛KFC出售啤酒套餐,大到一个专业、一项政策在本土当地的融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各种本土化的亲历者,可以说本土化是任何外来事物进入本地都不可避免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本土化的讨论和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并不是某一个学科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而是许多社会科学学科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一种学术研究的范式及实践逻辑。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与知识遭遇碰撞中,近二三十年接受高等教育栽培的各种社会科学的教育工作者均无可避免地、或生吞活剥,或东拉西扯、片片断断地“学习”着欧美知识。等到进入了某个特定环境,个人与群体的具体难题迎面扑来,必须“动手动脚”推进一线实务工作时,“尽信书不如无书”反倒是脚着陆、接地气的第一步。之后,在社会现场中,面对真实不逃不躲,卯力投身不怕狼狈,他者的容颜自然而然地柔软了工作者的身段,启迪着工作者的心灵。
当这样的践行之路走过数年,工作者自然而然会“长出”分辨与取舍“知识”的务实力,追寻着与自身实践相呼应的认识与理解。“知识”本身无中西之争,而是使用知识的知识人的问题。每一位理论产出的学者,都反应了他在某一种特定社会内部,某个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存在。辨识与取舍是读书人的责任。(夏林清,2016)
正是基于此,我特别想要和大家分享我本人对于本土化的理解。过去十年,我一直处在本土化的历程之中,无论是之前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还是现在在做的婴幼儿睡眠的本土化,无一不是真切发生的。
社会工作讲求“人在情境中”的视角,若是高屋建瓴地剥离出自己去看待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很难“嵌入”的。我经常看到本土化被抨击,甚至被“污名化”,认为本土化是不必要的,是某种新一轮的建构,或者是一种学术上的强占地盘,着实颇为痛心。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本土化”应该有哪些层次,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笔者将在接下来一一细表。
一、什么是“本土化”
“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语义上通常可以理解为外来某种事物与本国、本地、本民族存在环境和条件相互适应的程度, 以及内化为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特色事物的适用性程度的过程(纪德尚,2005)。可以说,本土化有两个基本的阶段,即外来“引入”阶段和“内化”阶段。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日常生活,其实都存在“本土化”的需求,从事物的普遍性上来说,“本土化”就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无论是理论上的学术取向,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经验取向,社会学科始终存在着外来知识体系与本土知识体系之间的学术交流,而这种观点的交融与碰撞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世界性范围内的由外来引入到内在根植的本土化过程。
本土化概念的普适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指在地域上具有的普适性,即这种“引入——内化”模式形成的本土化过程不是存在于某一个地域上的个别现象,而是适用于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一个具有普遍现象。
例如,我们常说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指外来知识在中国内化的本土化过程,以此类推还可以有美国化、印度化、日本化等等。尽管不同国家因外来知识的引进方式、转化机制等不同, 导致各国各学科本土化的路径和形态也不尽相同,但其内在的共性均是按照由“外来引入”转向“内在根植”模式的要求而亦步亦趋地发展着。
第二,是指学科发展上的普适性,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方法移植、成果应用等方面,一旦有了对某种学科理论发展的需求并且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就会出现相应的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倾向(纪德尚,2005)。
也就是说,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存在于学科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和选择,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或学科差异而有所限制。
第三,是演化过程的普适性,即本土化的过程不是事先设定要发生的,而是一种必然的倾向,具有其内在的特定生成过程的规律性。
这种规律性表明,只要它具备了“引入” 和“内化” 的基本生成条件,且合乎本土化生成过程的规律,本土化可以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发生。只要它具有对某种学科或理论发展的期求和学术取向,且不违背其本土化生成过程的规律,本土化可以在任何学科或理论发生。
如果我们认同本土化生成过程的普适性及其生成规律,那么就可以确认本土化是学科理论发展的一种基本范式。
二、如何理解本土化
在这一点上,我想以我之前在社会工作专业的浸润经历,来说明这个本土化的过程。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是指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即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发挥功能的过程,是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之后的适应性变化。(这里的中国社会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
可以说,本土化所反映的这种变化和过程,不但强调外来者对它所进入的社会文化区域的适应性变迁,而且特别强调后者的主体性,即它是站在后者的立场,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本土化对外来者来说是文化适应的过程,对本土来说则是文化选择、融合与接收的过程,它反映了两种行为模式、处理问题方式之间的互动(王思斌,2001)。
也有学者提出,本土化用“本土导向”这一概念阐发更为恰当。“本土导向”是本土化及专业化在本土的结合。本土化假设人类问题有普遍性和相似性,外来经验在外在场景是成功的。归纳国际经验,检验其多大程度上适应本土,并采用旋进思路形成适合本土的做法,可以有利于解决本土经验无法解决的问题。专业化则基于本土事物和外来事物的某些相近性,按照“专业”的框架提炼本土经验,并将其在本土未来和外在世界进行演绎,这正是对本土经验普适性的检验。本土导向的架构包括了两个过程:一是外来经验的本土化过程;二是本土经验的专业化过程。(顾东辉,2009)
Walton 和Abo el Nasr(1988)指出一开始使用本土化这个词语,是用来描述那些不适用于西方工作理论的其他社会结构下的工作。他们强调任何实务工作要遵循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特定特征,并且指出实务的本土化是从“引进(importing)”到“扎根(authentication)”的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把引入的西方工作体系中所包含的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特殊社会需求、价值观和文化体制来进行修正和改变。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当代很多实务工作(例如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等)中显现出了“专业霸权”,出现了一些西方工作者将西方理论和技术在不考虑本土文化和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现象。Midgley(1981)也批判了在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的观念、技术以及体制的这种状况。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并因此而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来建立一种新的专业霸权主义。
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冲突是相当明显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相关争论基本上基于两个核心预设:第一,社会工作是西方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下现代化的产物。第二,本土化的过程是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因为它是质疑西方社会工作的权威并且试图寻找可以与当地文化、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话的话语体系(Gray&Fook,2004)。
基于以上预设,Tsang 和 Yan(2001)讨论过是否有必要在引入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本土化的概念框架和体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他们认为在嵌入本土环境的过程中,本土化涉及到了社会工作实践的四个层面:
第一,意识形态或者说是行动逻辑。价值观层面的整合以及合法化可以凝聚起来处在共同意识形态下的共同体,并且决定他们行动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目的论。由文化场域来决定,并且受到到个体和社会的双重形塑;
第三,寻找相关的本土知识。作为本土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必须认识本土需要的多样性以及本土情境下的文化相关的实践发展;
第四,技术论。如果采用适当的文化相关的工作方法、技术,会使实践进行地更加有效,因此不用完全照搬西方体系。
Osei Hwedie(2011)强调,“本土化”是指作为实践基础的理论、价值观和哲学基础必须受到本土因素的影响的一个过程。本土化强调文化层面的转变,因为本土化与社会工作者的自身社会经验、共享图景、知识储备和所处社会的制度框架是相关联的。由一个跨文化的实践到“变为本土的”实践则是指所有的实践、思路、工作过程和技巧必须符合现有社会的社会建构的现实。
总的来说,由西方世界观、价值观、概念、理论、方法论等主导的知识体系在非西方国家运用时,应该适当修改或被重新定义以此来符合不同社会和文化情境的特点。故此,本土化的目的就是使得教育、研究和实践符合本土情境。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得出本土化过程应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K Yip,2005):
1、符合地方需要的西方工作实践的一种本土适应过程。(Payne,1997)
2、促使工作实践开展实施本土政治、社会、文化场域的过程。(Walton and Abo El Nasr,1998)
3、本土化的知识体系,意识形态以及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工作模型的技术及技巧的掌握。(Geertz,1983;Jinchao,1995;Mohan,1993;Yip,2001)
4、对于西方工作模式的专业霸权有所反思。(Drucker,1993;Midgley,1981;Nagpaul,1993)
5、根据本土社会结构及实践经验重组微观及宏观层面的工作模式的技术及技巧。(Roan,1980)
三、本土化的层次
西方的许多实践有一种程序化和标准化的倾向,如IFSW(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和IASSW(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中对于社会工作的全球化定义以及社会工作教育的全球化统一标准。
无论在建立全球统一标准的过程中,还是在发展文化相关的实践过程中,对于普适性的认同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元素。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文化的相关本身就挑战着普适的知识体系,以及主流言论的文化霸权(Wong,2002)。然而,“本土化“这个概念就是尝试带出更多元化的声音以及适合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方式,从而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本土工作实践的本土基础。
终究,本土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生和推展有它自身的阶段性,也有其本身内在的逻辑层次。
本土化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有西方的研究在前线,但不谈“化”而搞本土研究则会脱离现有的学术轨道,完全另立一套,导致两种学术体系无法对话。
所以,必须强调的是,本土化不要陷入建立中国工作模式知识体系的误区中,它是为专业体系加入一些中国议题的元素,是一种知识的拓展,进而推进整体上的发展。
四、本土化的路径
笔者这里要借助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阐述来说明本土化过程。在吉登斯的学术体系中,之所以用“现代性”而不用“现代化”这个词,主要是考虑到一度被认为是客观自然过程的“现代化”,实质上却通常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过程。
中国社会具有与现代性的起源地欧洲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现代性对它来说属于外来文化,政治精英和知识权威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土传统与外来新传统之间的关系。诚然,现在的很多社会学科也面临着类似的“现代性”的问题,知识权威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在引入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时就做出选择,以便这门专业学科得以在中国进行有效地传播和教授。随之而来的,才是如何将这些“去政治化”的专业知识运用在本土场域里的实践。
基于上述情况来看,学者们认为本土化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研究西方工作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容之处,再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
第二,对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促使国际的工作经验与本土社会工作的比较和碰撞;
第三,分析两种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化它们之间的亲和性;
第四,在此基础上从事实践,扩大两者之间的相容性,以实现优势互补。
这样就可能形成适合中国需要的专业某种实务工作,即本土化了的专业工作。(王思斌、马凤芝,2011)
就本土化过程本身而言,笔者认为不仅仅应该关注实践过程中的本土化,而且应该同时关注专业知识的本土化。即本土化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本土化
这一阶段的本土化是指将某个学科或者实务从西方引进中国的时期,对于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各方面进行“过滤”,主要的功能是“去政治敏感性”以及“去文化敏感性”,将在中国体制内合法性的部分,和西方知识过滤后的专业性的部分保留下来,传授给专业学习的学生或者从业人员。
2)第二阶段本土化
这一阶段的本土化是指当具有专业背景的实践者在中国场域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逐渐会感受到所学专业知识(经过第一阶段本土化后的专业知识)在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障碍,或者所学知识不具备良好的文化适切性,导致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价值理念产生冲突矛盾,这时就需要本土化。这个阶段可以称作是一种“专业性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层面。
值得反思的是,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专业对于政治体制和文化基础的依赖性。仍以社会工作为例,各种研究和实践表明,西方社会工作移植到中国之后,经过知识精英去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性之后,仍然会有不适应的状况。
我们所谈及的本土化是一种“选择性本土化”,即我们选择性地站在某些群体的立场,在某些群体的话语体系中进行一种策略性的转变,以求社会工作专业可以扎根中国。
就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存在这样的特点:政治体制的基础没有改变,专业工作的主体没有改变(如给原本的非专业性的社区工作者培育社会工作知识)。
社会工作经过“本土化策略”先是适应现实的体制现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然后经过长期的实践,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加入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相关的一些改良措施,最终回归专业的社会工作。
理论上来说,现时的国情及政治体制文化环境,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本土化过程来说是有所影响的,不过这不是今天要探讨的重点。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我们一线的实务实践者所接受的专业教育并非来源于西方第一手资料,但这并不妨碍实务者获取专业知识,并做出将西方形成的专业的工作理念积极内化的努力。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本土化并不是另立门户,不是什么“邪教”一般地自成体系。本土化的前提一定是专业理念不能变,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那可真的是搞事情了。
所谓的专业理念,必须有专业价值观的支撑,在专业价值观的支撑之下,去用更加本土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每一个实务工作者本身就嵌入在自身的逻辑圈里,在呈现专业自我的同时,作为个体都是自带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的,而这些生命智慧加诸于本土实践时,就会碰撞出新的经验。
无论何种咨询,本质上是服务的提供者与服务对象进行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强调增权和参与,这也是作为一个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进行互动的过程。
本土的工作模式应遵循”价值观——方法——过程——效果“的逻辑来发展,也就是“坚持专业价值观理念——程序方法的本土化和处境化——过程目标与结果目标的统一”的模式来建构范式。
就睡眠咨询而言,无论是在咨询过程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例如隔代养育、合睡、家庭边界不明晰等,还是在咨询关系本身,例如建立和维持专业关系、结束专业关系,专业自我的衡量等,还是更实际的,解决睡眠问题的方式方法,都会遇到本土化的需求,深刻嵌入的实务工作者是无理由没有感知的。
如何剥离本土经验和专业知识,或者说在怎样的范围和限度里运用本土经验和人生智慧来帮助实务工作者解决本土问题,确实没有定论,也没有一个严格的边界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本土经验和人生智慧有助于解决本土情境下派生的实际问题,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产生排斥。
前段时间用碎片时间看完了《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这本书,Ethan Watters在这本书里提到了诸如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流行心理疾病在非西方国家的形成和被认识历程。其中有一些观点令我印象深刻,他提到:
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如何思考心理和精神疾病——他们如何给症状分类和排序,如何医治并预期病程和疗效——这些都会影响疾病的本身。不管致病原因为何,我们无一例外地依靠自己的文化信念和传说来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文化对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内心的影响,通常是一种本地且私人的事。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全球通用的疾病模板,而是对左右该疾病的个人与文化力量的本土化理解。
诚然,睡眠问题(行为性的)并非疾患,但它的影响机制毫无疑问地冲击着家庭内部。我们在感谢发现并建立这个知识体系的人的同时,是否也需要保有一定的文化敏感性呢?
共勉!
Reference:
夏林清,2016: 林壑万里清——社会与个人的改变之道,社会治疗书系总序
纪德尚,2005:“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的再认识”,《河北学刊》 2005(6)
王思斌,2001:“试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2)
顾东辉,2009:“本土导向:灾后社区社会重建的实践智慧”,《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J Midgley.1981.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via:www.getcited.org
K Yip. 2005.“A dynamic Asian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in cross-cultural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September 48 (5):593-607
Osei Hwedie.2011.”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ly relevant social work: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indigen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January54 (1): 137-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