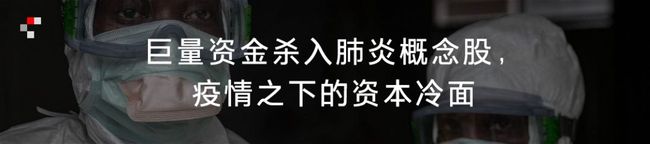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夫当观”(ifseetw),文:付一夫,题图源自图虫创意。
瘟疫,就是我们的影子。
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且不提人尽皆知的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单就我国而言,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诸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瘟疫都曾侵袭过这片土地。
也正是由于瘟疫与人类发展的相伴而行,每当有疫情爆发,人们总是本能地想要从历史中找寻答案。
其中最值得玩味的,莫过于鼠疫。
公开资料显示,世界所有国家卫生部的文件中,鼠疫都被列为第一号传染病;在我国,明文规定的甲级传染病只有鼠疫和霍乱两个,而声名显赫的非典、埃博拉、禽流感等病毒,都仅仅是被归于乙级传染病的行列中。
鼠疫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高的“待遇”,是因为它着实造了太大的孽。历史上共出现过三次鼠疫大流行,分别为公元前6世纪(520~565年)、14世纪中叶、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范围席卷亚、欧、美、非大陆上的众多国家,总共夺走了一亿多人的生命。这样的数据,足以佐证其“瘟疫之王”的地位,很难不让人谈之色变。
19世纪末的香港,正是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遭受重创的一座核心城市。
1
史料显示,自1894年5月10日起,香港居民中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病,主要症状为鼠蹊、腋窝、颈部等处淋巴结肿大,以及发烧等。当时的《申报》曾连续多日对此进行报道:
“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所染之症皆系两腿夹缝或两腋底或项际起一毒核,初时只如蚊虫所噬,转瞬即寒热交作,红肿异常,旋起有黑气一条蜿蜒至要害,随即云亡。”
基于这些较为详细的记载,不难断定香港遭受了鼠疫的侵袭,患者症状表现正符合了腺鼠疫的种种特点。与此同时,其间香港“疫气延及鼠子,所毙甚多”,大量的老鼠死亡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好好的香港,怎么突然就被鼠疫攻击了呢?
追根溯源,疫情的源头在云南。美国著名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曾提到,全球有三处古老的自然疫源地:一是介于印度和中国、缅甸的喜马拉雅山麓,二是位于中非的大湖地区,三是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由中国东北到乌克兰的区域。而云南恰恰处于第一个疫源地范围内。澳大利亚学者费克光也在《中国历史上的鼠疫》中,记载过多起发生于18世纪中期云南鹤庆等地的腺鼠疫情形。
19世纪起,外国鸦片大量涌入中国,进而带动了云南居民种植鸦片的泛滥,相对便宜的价格让产自云南的鸦片很容易在两广地区找到市场。受战乱影响,广东的商人迫切希望开辟新的交通路线,此时北海的重要性就日益彰显。
在此背景下,1876年北海开埠,并早早地出现了汽船运输,甚至还开设了许多通往香港乃至海外的路线,这让北海成为云南、广西以及中南半岛客货运输重要海路集散地的同时,也加大了疫情扩散的可能性。
果不其然,鼠疫疫情迅速蔓延,广东南部的廉州、雷州和高州等府在1890年以前已受到传染;1891年,鼠疫在距离广州不到300公里的吴川县流行;1892年4月,广州爆发鼠疫,恩平、南海番禺等地亦受到波及……不久之后,香港就出现了鼠疫患者,拉开了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序幕。
鼠疫给香港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仅1894年,香港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为2485人,然而多方面证据都表明,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如此。例如,很多香港居民在患病后,因不愿“客死他乡”而选择离开香港回到广东老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路上就已不治身亡,这些都未纳入香港的官方统计。
在此期间,港人惧鼠疫若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大量人口纷纷逃离香港,共计约8万人,几乎占当时香港总人口的1/3,而香港的商业也因此而凋敝,市面萧条,工作乏人,全然不复此前的繁荣盛景。
此后多年,香港依然深受疫情困扰,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手段所限,当时还没有治疗鼠疫的特效药,现代西医治疗鼠疫所采用的抗生素如链霉素、四环素、氯霉素、磺胺类药物等特效药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发明的,而鼠疫疫苗中的减毒活菌苗到1908年才开始使用,它对腺鼠疫有着较好的免疫力,不过对肺鼠疫效果欠佳,但也足以让香港在1909年以后的发病率明显降低,这已是后话。
2
面对疫情的来势汹汹,当时的香港政府迅速地审时度势以采取应对措施,而他们的努力也着实收获了不小的成效。
具体而言,香港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统筹协调:
其一,出台《香港治疫章程》,将疫情通告全港居民。
1894年5月10日出现首例鼠疫病例之时,政府便知此事非同小可,随即马上召集各部门集会商讨,进而制定出了《香港治疫章程》,作为纲领性文件来指导整个香港治疫事宜,该文件刊登在5月12日的《香港政府宪报》上,其中几条关键内容如下:
凡有人在港内或别处来港患疫毙命者,其尸骸须在本局所定之专处埋葬,至埋葬如何慎重之处,仍由本局随时谕行;
凡人知有人患疫或类似疫症者,须即赴最近之差馆或官署报明,将情照转会局,以便办理;
凡患疫之人迁徙医船或别限所,本局委有人员办理,如非有本局或本局所委之员及奉有执照医士之命,不得擅行迁徙,既经奉命,其迁徙应如何慎重办理,仍由局随时谕行;
凡在有疫邻近及本局所定界限地方,本局时委人员逐户探查,以视屋内情形果否清洁,并查有无患疫或由疫致死之人,如屋内污秽不洁,该员即饬令由本局所委之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洒以解秽药水,务期尽除秽恶,如屋内查有尸骸,则立即将其移葬,倘有患疫之人,则如例迁徙医船或别限所调查。
从发现首例病患到制定出周密的治疫章程,香港政府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反应之迅速令人赞叹。而从该文件的内容上看,同样较为完备系统,这使得香港的救治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对于最终控制疫情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还格外重视危机爆发时的信息沟通,通过政府公告和各路媒体来向全社会发布病疫情况。
例如,政府部门先后在5月11日、5月29日、5月31日、6月9日、6月23日和8月28日发布公告,及时与香港居民进行沟通,尤其是在5月29日,香港总督罗便臣正式宣布香港为疫区,并告知民众,政府已采取有效手段隔离与医治病患,着力破除谣言,消除大众恐慌情绪。
再如,自5月5日起,香港《申报》就肩负起了及时通报香港疫情的重要任务,其中5月报道疫情11次,疫情高峰的6月几乎是每日报道,7月报道13次,如此高效的报道离不开香港政府的有力支持。
事实证明,由于信息透明度极高,各种谣言和留言不攻自破,民众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稳定,相关的应对措施也就变得格外高效。
其二,想方设法救治染疫病人。
对患者实行隔离治疗成为各方共识,然而,当时香港的医院并没有针对传染病的病房,床位数量更是有限,再加上患者人数实在太多,使得医院无计可施。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政府下令将湾泊在港内的轮船“夏珍尼亚号”作为临时的隔离医疗场所,但凡感染鼠疫的病人都要送到该船接受西医治疗,从而缓解了医院的压力。
不过,由于鼠疫传播速度极快,患者数目与日俱增,而香港的医护人员有限,分身乏术。为此,香港政府多次向外埠请求援助。据当时《申报》刊载:“……新患疫症者有48人,染疫而死者76人,在港医生不敷诊治,是以请上海工部局延聘医生六人附船前往,分派医院医船,俾病者得以药到病除”,“英官致电驻日之英国水师提督,欲延聘西医来港,藉以诊治”。这些都是救助病患、抑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的正确途径。
除了上述两方面之外,香港政府还及时封锁了疫区,主动搜查隐藏的患者。对于可疑病人进行观察,对于暂时不能确诊的患者,则由士兵看管,以免随处走动扩大传染。同时,各部门还着手对疫区进行消毒清洁,人手短缺时,港府从部队调来几百名士兵一起检查疫区并进行消毒工作。这些工作人员“当疫症初起时,差役查搜屋不遗余力,竟有终日奔走越十点钟之久或十五点钟之久而未得稍息者”。也正因为如此,疫区的环境得到了迅速改善,并较为有效地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对于最终控制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述实践也为中国其他疫区提供了极佳的参考范本。
3
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能促成人类自省,由此引发一系列变革,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尽管这种作用并非来自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基于生存的本能。
当鼠疫得到控制之后,为了防止悲剧重演,香港政府痛定思痛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比如,他们组织各方专家进行了鼠疫专项研究,积极探索病源、了解病因,其中以法国传染病专家亚历山大·耶尔森和日本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最为知名,他们证明了香港爆发的鼠疫多为腺鼠疫,耶尔森还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鼠疫病原体的学者;另外,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医学博士辛普森赴港对疫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后,提交了一份《香港鼠疫爆发和长期流行的原因与治疗方法建议的报告》,其中对香港鼠疫长期存在和反复发病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影响深远;
再如,香港乃至全中国,都逐渐建立起了近代意义上的鼠疫应对机制,并开始全面接受与采用西方的医疗技术,以及加强城市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使鼠疫这一曾经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整治,而人类发展史上也终于出现了对抗鼠疫的胜利曙光——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几乎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鼠疫。
这场发生于香港人与鼠疫之间的“短兵相接”,是全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上,极为闪亮的一笔。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尽管已是126年前的事情,但至今仍极具教育意义。
而今“妖雾”又重来,可这次绝不一样。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是:此刻的疫情,要远逊于126年前的香港鼠疫,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医疗技术、防疫条件和动员能力,却又远胜于当年。更何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管任何的艰难险阻,我们都因这样的团结一心、勇敢拼搏而挺了过来。
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本和底气所在。
新春佳节已至,春天的脚步渐行渐近,而新春孕育着生机,新年亦承载着希望。
尽管过程可能并不容易,但最终结局如何,你我都应该坚信不疑。
参考文献:
1、彭海雄,《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基于19世纪香港社会变迁的考察》,2005;
2、崔艳红,《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鼠疫与港英政府的应对措施》,2010。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