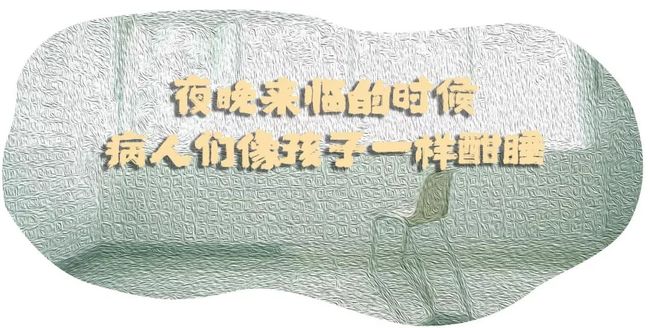我在医院精神科工作,目睹了骨肉的分离
在很多都市人的记忆里,精神病院或某些医院的精神科早已不是医院的代名词,它们的名称甚至所在地址都在不知不觉间幻化成一种符号。一旦被提及,不是谈话双方相视一笑的心照不宣,就是一种暗中带刺的“恶语相向”。
一些影视艺术作品对“精神病”的包装,让越来越多的人忘记了,它不过是这个世界上困扰人类健康万千疾病中的一种。因为不甚了解,人们对这些符号充满畏惧。
我们走访了某家小有名气的医院的精神疾病科,和一些医护人员及病人家属们聊了聊,希望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疯人院”,而个中滋味,就留待大家品评。
—
小L是这家医院精神科的见习护士,她告诉我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初衷非常单纯,“我就是想了解一些精神疾病方面的案例和治疗方法,学校里学的东西太书本了,我想给自己增加一些临床经验。”
但即使是在医学生的小圈子里,小L的同学们也对她的这段见习充满好奇,“大家虽然没有外人那些常识性的偏见吧,但因为我们科的病房都是封闭式的,即便是患者家属都无法随意出入楼层,需要医务人员检查身份,所以知道我在这里见习的朋友们都嘱咐我要注意安全。”
“我其实是觉得大家对精神科的定义过于狭隘了,那些出现在电视剧里的,会被看作是‘疯子’的患者,代表的仅是精神科里的重症疾病——精神分裂症而已,除此之外,我们的病区里还住着很多情绪障碍患者(如:躁狂、抑郁)、心因性精神障碍患者(受到某种精神创伤后出现急慢性情绪行为障碍)、人格障碍患者、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异常患者(如:癫痫导致的精神障碍、脑补感染及肿瘤所致的精神障碍)。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很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精神状况,即使是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在专业治疗后也会趋于平缓。”
小L告诉我们,在她见习的这几个月里,接触比较多的是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患者和轻度的精神分裂患者,“没有一般人想得那么恐怖啦,轻度的精神分裂主要是存在妄想症和幻听,他们就是时常自言自语而已,并不会对周围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电视剧里演的把人绑在床上的情况她也见到过,“这种就是躁狂症犯了,我们得在当时把他们控制住,我刚去的时候,有个中年男性患者被保护性束缚后力气依然很大,我们几个人绑他一个,绑好之后他还能带动床……”她当时条件反射性地往后退了两步,事后才为自己那一刻的恐惧有点自责。
对待患病程度严重的患者有时要采取电疗法,医生说几次电疗就能使病人消除自杀的念头,病情也会随之好转,但小L在和患者实际接触的过程中还是对这一疗法持保留态度,“倒不是安全或疼痛的问题,我站在病患的角度会觉得丧失短期记忆对他们来说挺残忍的。有的病友说话说着说着就不记得十分钟前的事了,如果是我的话,爸妈看到我这个样子,得有多难受啊……”
小L所在的病区每天都有专门的家属探视时间,有些病人的家属即使白天上着班也都坚持不辞劳苦地赶来,有些面孔则是隔三差五地出现一次,让她比较难受的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病人反而很少有人探视,人到暮年,被遗弃在了这样一个和外界世界多少有点隔绝的地方,“陪伴”他们的只有非亲非故的医护人员。
每逢夜晚,病区所在的大楼都会迎来久违的宁静,“和普通的医院没什么分别,我反而挺喜欢值夜班的时光,病人们会像孩子一样酣睡,我有时候在想,对他们来说,能够享有一场安眠,也总好过在嘈杂的世界里被动接收着那些来自外界的噪音吧。重症病的病房有时会有一些声音,那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有的时候能听到他们说梦话,虽然听不太懂,但也算感知到一些他们的喜怒哀乐了。”
作为护士,小L最常感受到的还是病人们对“出去”的渴望,“出院只是最基础的,这些进来过的人,要如何重新融入社会才是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有的医生会直接叮嘱患者,出院以后要想当个“正常人”,就得隐瞒自己的这段病史,“我觉得这其实是社会的问题,而非病人的问题,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情况稳定下来之后,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分别,他们应该享有慢慢回归正轨的权利,就像得了其他病治愈出院的人一样,你难道就因为人家之前生过病就要另眼相待了吗?”
—
在小L的讲述中,频繁提到一对每天来探视女儿的夫妇,他们的女儿在高考这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在小L的引荐下,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妈妈,她和我们聊了聊这些年在给女儿治病过程中心态上的一些转变,以下是阿姨本人的自述:
我是在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的那年才知道,这病是分单双向的,单向的还算是精神障碍范畴,双向的就要被归为重性精神疾病的范畴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她爸爸对抑郁症的了解少之又少,我们哪知道有那么严重啊,都不觉得是种病,以为就是小孩子快考试了,心理压力太大。她最开始就只是变得没以前那么爱说话了,每天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我们的交流也仅限于吃穿层面的。我和她爸爸没太当回事吧,就在情绪上开导过她几次,跟她说放轻松之类的,毕竟18岁了,也是个大姑娘了,应该学会自己调控自己的情绪。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悔,如果我们能早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让她及时接受治疗,也不会被抑郁症折磨这么久,更不至于误了今年的高考……
从最初的情绪低落,慢慢的,她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焦虑和厌世,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坏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拒绝同我和她爸爸进行任何交流。
我们真正感到恐慌是在一个周末,女儿在房间睡觉,我和她爸在书房用电脑,很无心的,我那天要找一个前几天浏览过的网页资料,顺势点开了浏览器的历史记录,这不点不要紧,一点吓一跳:这都是什么啊?满屏关于“死”的搜索记录……还有很多关于“厌恶世界”、“想要自杀”的字眼,我当时就瘫在椅子上懵了,缓了两三分钟才把她爸叫来看。
那天晚上我们俩一夜都没合眼:我哭了一晚上,她爸爸查了一晚上资料,我们都有预感女儿是得了某种精神疾病,但当时就一个念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治好她,我们要把自己的女儿救回来。
在背后做足功课的同时,我们也一点点增加着对她的关心(怕一下子关心太猛让她不适应),住院之后她有过一小段时间的自我否定,虽然未必都告诉我们,但我一有机会就告诉她,“你现在所有关于自己的负面想法,都跟你的个人能力没关系,你只是生病了,但这个病就像感冒一样,是可以治好的。“
很多人都会把抑郁症和抑郁情绪混为一谈,包括我们之前也是,但医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抑郁已经形成一种病症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可以自我调控的情绪了,而是一种生理上的病变,是激素分泌的生理性疾病。
女儿今年放弃了高考,但我和她爸现在都非常平静,因为真的有看着她一点点好起来的样子,也就是在那时,我们都意识到为人父母最重要的并不是指着儿女功成名就或盼着他们给自己养老送终,健康平安,就是每一位父母最大的心愿。
我们也再不会用“疯子”、“傻子”、“神经病”之类的字眼去形容任何人,只有亲身体会过那种无能为力的痛苦,才会明白这些词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恶意中伤”。
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好,已经准备再过几个月就重返校园回归同龄人的生活了,我和她爸爸虽然时不时地有点担心,但总体上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更像是我们一家三口共同战胜的困难,就算这些东西卷土重来,我们作为家人也还是会继续陪伴下去。
同时,也呼吁大家能多一些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更多地去体谅和关心那些处于病痛中的人,他们很多时候有苦难言,只能慢慢学着和病痛共存。
—
如果说有家人陪伴的病人尚且是幸运的话,那最令人心疼的,可能是那些仍在独自挣扎的“异类们“。
下面的故事,来自一位在精神科工作的医生,虽然事情距今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但那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他还在家乡所在的小城工作,在那个镇上的医院里,他曾遇见过一个男人。
男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穿着老旧但干净,操着一口三句只能听得清楚一句的方言,在一个平凡无奇的午后跌跌撞撞地闯入了精神科的领地。
坐班的医生和病人都被吓了一跳,起先以为他是来看病的,就耐心告诉他需要先去排队挂号,排到自己才可以进来。男人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让人听不懂的方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冒冒失失地就往医生跟前递。
医生扫了一眼,并未明白他的用意,只好又重复一遍,“先去排队挂号”,语气显然有些不耐烦了,外面那么多人等着看病呢,甭管你是病患还是家属,都得按流程操作。
男人大概不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冷遇了”,好不容易说了一句能被听懂的“谢谢”就退了出去,蹲在走廊的一角,攥着照片,怯生生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个护士看不下去了,走过去试图和他交流,刚开始他还是一个劲地把照片往护士手里递,但当护士真的想要接过照片时,他却又不给了,死死地攥着照片的一角,好像生怕护士把照片里的人抢走一样。
经过几轮反复而艰难的“沟通”,大家总算明白了这个男人的来意:
照片上的另一个男人,是他哥哥,和他一样的矮小黝黑,他们来自北方的一个山村,几年前,哥哥突然疯了,狂躁、摔东西、自言自语,变得混混沌沌,村里的人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全都躲着走。
在那样一个偏远山村里,疯子就是疯子,人人都害怕疯子,除了弟弟。只有在弟弟眼里,哥哥偶尔是安静的、平和的,每每那时,他就会喂哥哥吃一点热饭,给他换下脏了的衣服,想从那张仿佛一夜老去的脸上找到一点笑容。
直到后来有一次,哥哥又“发疯”了,冲进了别人家里砸东西,不知是谁叫了村里的几个壮汉,蜂拥而上,把哥哥带走了。
从此,那个疯了的男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村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疯子,但在弟弟的记忆里,那是自己的哥哥。
那几年,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去寻找他,他不知道哥哥被送去了哪里,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他,还是那么执拗地独自一人走出了山村,在外面一漂就是几年。
刚开始是乱找,后来有人告诉他,不知是打趣还是话里有话地劝他放弃,“你哥进精神病院了”,可他显然把那句话当了真,挨个把当地的精神病院和各医院的精神病科跑了个遍......
只是过了几年,便没人能分得清,疯的是他哥哥,还是他自己......
这件事成了医生心里的一个胎记,每每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他的心便会隐隐作痛。
医生告诉我们,很多病得不那么重的抑郁症患者在求诊时都会提到一个现象:周围人多多少少都对他们患病一事持怀疑态度,“你就不能不那么矫情吗?好好生活吧,别作践自己了。“
而等到他们真的出现一些失常举动时,人群又会失忆一般地表现出惊恐,“这就是个疯子吧,我们离他远一点,自己有病都不知道去看,真是......”
但世界上哪有什么与生俱来的疯子呢?
无非是来自外界的眼光和深不可测的人心,将他们一点点推向了那个名为“不正常”的深渊罢了......
但陪伴与爱,
才是疗愈病痛的良药啊。
(作者案:疾病是一个永恒严肃的话题,为了保护患者家属、医生以及医院的隐私,我们对部分采访内容进行了一定的模糊与取舍,可能某些部分的描述在专业医生看来,会有一些“不专业”,但我们希望大家感知的是一种态度,感谢所有采访对象的支持与配合。)
采访、撰文:Peter Peach、Holly
编辑:Holly
图片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