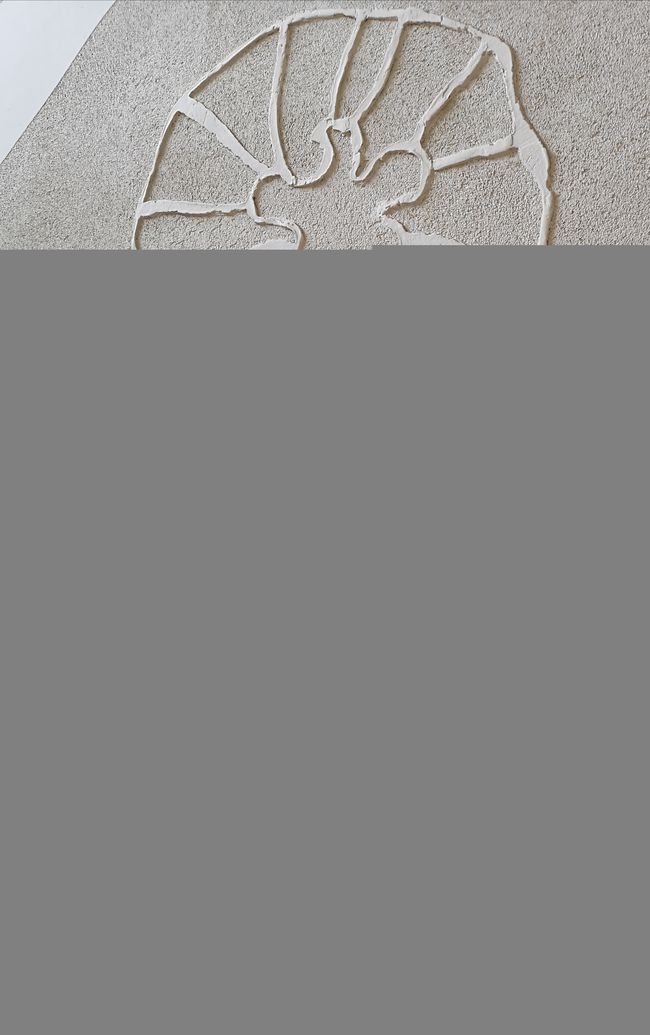图片里面的这个玩意儿,英语叫jellyfish,中文意思是水母,又称为海蜇。近日里,英文老师讲到海洋生物课文时,介绍了它。
多年前在帕劳群岛游览,与女儿在水母湖里潜水,带着照相机的护套,给五彩斑斓的水母拍照。那些水母都是无毒的,在阳光灿烂的照耀下,于纯净浅绿的水中翩翩起舞,阿娜多姿,非常美丽,让人觉得十分惬意和浪漫。
但是,我非常怕这个东西。
有一年夏天,在青岛海里游泳,不幸地被其蛰过脸部,开始没有当回事儿,但是,且不说疼痒难忍,一夜没睡成安稳觉,一照镜子,简直严重破了相,即使过去了十几个小时,依然不见缓解,又痒又痛。熬到天亮了,到了爸爸所在的疗养院去治疗,擦了擦消毒解疼的药水。护士说,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治疗,恐怕没有明显疗效。
这样疼痒并举的痛苦情形,持续了好多天。
回到北京,第一时间就到北大第一附属医院就诊。那个上了岁数的神经科的女主任看了我的脸以后,先给开了一些擦洗的外用药水和内服的解敏药片,而后请我留下,希望我帮她一个忙。之后,陆陆续续,好几位来自神经科和皮肤科以及外科的大小医生,都先后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脸伤,其中还有一位医生,手拿装有微距镜头的相机,对我的伤口拍了多张局部照片。
不过,人家倒是事先跟我商量了,我也没拒绝,问了问一些细节,回答是,从前只在书本中看见过,但临床却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和典型的蛰伤,采录的病理相片,将发表在未来的有关医学论文里。那个起初给我看病的女大夫,自我介绍是留美的医学博士后,对我问诊的态度最为详尽认真。这些看似会诊研讨的事项也都是她在组织,其他的大夫都挺听安排的。
想了想,医生要做科研,作为病人,能当个活标本,留下有意义的第一手图片资料,以提高增进我国相关领域的医学科研水平,也是一个善举,而且,作为一名公民,有责任为公益事业做一回奉献,只是,我有点儿顾虑,反复叮咛要求说,照片里千万不能留下整个面孔,万一让熟人认出来,多糗啊,挺伤自尊的。
女主任当时也都满口答应了。
那几天,无论走到哪去,见什么人,为避免误会,都得主动解释一下——这个伤口是怎么回事,等等;又因为蛰伤还不能捂着,须得敞开了见阳光、透空气,恰恰又见不得人,只得尽量猫在家里,不敢出门吓唬群众。
那一周末,北师大哲学院有特别心仪的课,于是就硬着头皮、鼓足勇气去上课了。记得那天刚刚走进北师大主楼电梯里,一个同班的哥们儿盯着我,看了半天,终于没有忍住,用我能听见的声音嘟囔了一句:“嫂子下手,怎么这么重啊?”
本来不想搭理他,后来一看电梯上几个人都在窃笑,于是就在下电梯之前回敬了他一句——也算是就坡下驴地自黑说:谁让咱人品不好的啊!
问题不在于他人的少见多怪,我的嘴脸确实是挺恐怖的。如果是年龄接近的朋友,也许看过一部描写意大利烧炭党的老片子——《牛虻》,里面的主人公亚瑟那张伤残刀疤脸,若跟我比,也许还要逊色些,一个是近在眼前的活物,另一个是画面里的角色,当然,我来得更恐怖和真实一些。
课堂上,老师还特别介绍了octopus(章鱼)cuttlefish(乌贼鱼)和squid(枪乌贼)等相近的其他几个单词,我却立即记住了水母,并且潜意识里还在念叨着:在中国叫做海蜇。虽然,在海里它是一个厉害角色,若被打捞上来,据说用生矾加以处理,就会是很好的一道下酒菜。
过去若干年,我只是在餐桌上见过它,吃过无法计量的次数了。这个东西,加上黄瓜丝,放点儿“辣根儿”(山东特产的芥末),的确是美味!既然不忌口,贪吃了人家的生命肉体多年,积累了那么多的“罪孽”,也就没有资格抱怨了,此乃一个因果报应吧!
不过,它给予我的惩罚真的是够严厉的。据那个专家大夫说,这是神经系统中毒,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弄不好会长期不省人事,甚至有生命危险的。
后来,伤口慢慢恢复愈合了,我也渐渐地咂摸过味儿来。这个看似平常的外伤确是非同小可——我经历了一种难以忘怀的特殊的苦痛折磨。
据当地的朋友说,那几天,青岛有的成年人也挨蛰了,疼得像小孩子一样哇哇地哭。我呢,虽然始终没有落泪,但是,从那时起,在心里记住了它,怕了它,一提及之,就毛骨悚然。
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体验吧!
哈哈,为了一个小单词,说了这么多的话!这个词,我当然是记住了——jelly fish!
于我而言,它不是水母,而是海蜇!
师大铁陀写于2019年3月3日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