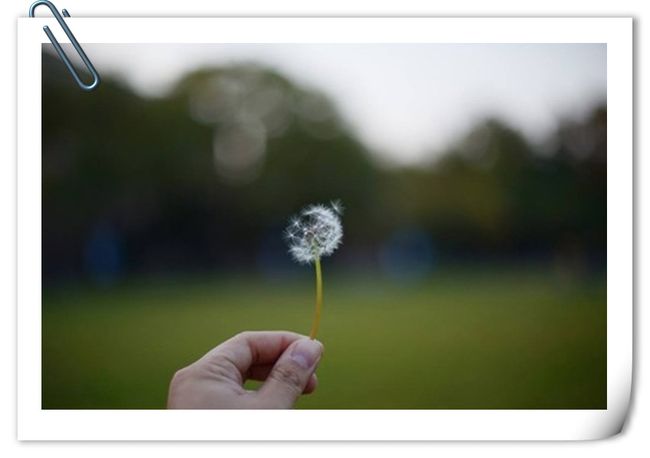(一)
“把头”这个绰号是我父亲在开滦煤矿井下采煤区当安全检查员时工人们偷着给他起的。父亲去世十七年了,偶尔见到他当年的老伙计、当年的小青年说起父亲,“把头”这个称呼还是父亲的代名词。
对"把头”这个绰号,我心里特别腻味和反感。
第一次听到,是哥哥下班回家和母亲嘟囔父亲:“我爸咋那狠啊?把人都得罪光了,难怪人家叫他把头!“ 我接话问了一句:“把头”是啥?哥哥和父亲在一个采区工作,见我问,没好气地回答说:“知道旧社会的矿主雇佣的打手不?咱爸就是!”
我当时挺不解的,父亲就是采煤区的安全检查员,怎么和“把头”连一块了?厨房做饭的母亲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爸就是死心眼、一根筋,班上工人做窑(井下采煤)有违章的、不听指挥的,让你爸逮着了,一点面子不给,要么送矿上办学习班,要么罚人家钱,狠着呢,整天因为这个伤人挨骂,活该!
母亲的唠叨让我对父亲也产生了怨气,但我们都不敢对父亲露出不满,一家人都怕他,脾气火爆,性子倔强的父亲在家就是皇上,班上的事谁要多嘴非骂人不可。
那时,“把头”这个绰号像鱼刺一样,卡在喉咙里让我特别不舒服,不理解父亲的不近人情,自己落不着好还背着骂名,同时更讨厌背地叫我父亲“把头”的那些人。
记得有次在街上,碰到父亲的老伙计刘文林大叔和一个年龄比我大不多少的小伙子,刘叔向小伙子介绍我,没想到小伙子脱口说出:“哦,“把头”的老闺女,我应该叫你妹子还是侄女啊!”我当时就急眼了,憋在心里好些天的火没处撒呢,一步窜他跟前大声地吼起来:“你爸才是把头呢!再说我爸一句试试,挠死你!滚蛋!”也许是我当时的架势太吓人,刘叔拉着那个人疾步的离去了,边走边叨叨着:这丫头咋了?火气这大呢?
气鼓鼓回到家看见父亲在吃饭,我楞眉楞眼地冲着父亲喊了句:“爸,快别干安全员了,你那么狠管人家,都膈应你,我都跟着上火!”一旁的母亲也跟着我的话嘟囔父亲:在班上当你的老板子多好,非得当这个破安全员,伤人挨骂不落好!父亲立马眼珠子一瞪:“哪爱骂就骂,只要我下井看到违章的,该逮还是逮!怕了就不是“把头”了!”
看到父亲真生气了,吓得母亲和我蔫蔫地躲开了。父亲的犟脾气是出名的,他看准的事非干不可,他要是觉得有理,一干到底。
(二)
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儿童团,当过县委地下交通员,残酷环境磨炼了父亲的坚强意志,对党忠诚,无私无畏。父亲文化低,性子耿直,解放后的1952年,放弃在县委工作的机会,非要到窑坡(现在的古冶矿区)上班挣钱养家,这一干就是30年。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工作在井下采煤一线,每天起早贪晚,风雨不误,从不旷工,肯吃苦,不惜力。从小工、到老板子,从组长干到班长,一步一个脚印,遵章守纪,踏实认真,并且也很较真儿。
担任采煤区里的专职安全检查员,父亲的较真劲儿发挥到了极致。罚过自己的徒弟,抓过要好的老伙计,有人说他不近人情,还有人说他咬死理,但父亲不认,他总说,井下干了这么多年,看到过无数次的伤亡事故给家庭带来的痛苦,自己深有感触,有啥比守护安全和生命更重要呢?
记忆中,父亲井下受过伤,差点要了命,那是父亲心中的痛。
还是在井下当大班长时,有两个小青年违章作业,父亲看出了危险,立刻制止并上去处理,没想到上面的煤塌了下来,把父亲埋住了,越埋越深,眼看就埋到了脖子,吓得小青年浑身发抖愣愣地僵在那,不知道怎么救人,就会哭,幸好有个叫刘贺义的老板子有经验,带着几个人把父亲救了出来。
父亲腰受了伤,不能动弹,身上砸得好几处出了血,但他坚持不要救护车,并且不住医院,嫌太闹腾。拗不过父亲,领导和几个工人用排子车拉着他去医院治疗一下,没有大碍就送回了家。
我放学回来,一眼看到躺在炕上的父亲脸色苍白,闭着眼睛,胳膊上缠着雪白的绷带,才换下的窑衣堆在地下。母亲眼睛红红的像刚刚哭过,我害怕了,悄悄问母亲咋了,母亲小声告诉我父亲差点没命。
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恐惧,那种害怕失去父亲的恐惧感让我瞬间手脚冰凉,我静静地看着父亲,很心疼也很难过。后来听母亲说,那几个送父亲回家的工人一再感谢父亲救命之恩,要不是他发现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担任区里安全员的那些年,父亲更加执着,更加凿死理。骂他的人有,说父亲顽固不化,不近人情,整天就知道查隐患、查“三违”,就是一个“犟把头”。但更多的人理解父亲,支持父亲,称赞父亲是硬骨头安全员。在父亲心里,安全重于天!
(三)
对父亲的真正理解,是我参加工作后,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不再腻歪和反感“把头”这个绰号,渐渐地,我从心底里接受它、认可它,父亲的这个绰号,在我心里就是一种神圣的使命。
父亲退休后,我顶替父亲参加工作,被招进采煤区当了一名核算员。
报到的第一天,赶上了区里开安全会,会后我看见好几个工人耷拉着脑袋进了小会议室,里面的安全区长、安全员轮流数落着那几个人。我有点好奇,扒着门缝看,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采面、支架、冒顶、抓车等是啥意思,但我听明白了这几个工人下井违章被逮住正在挨批。
只见有个胖老头领导,后来知道他是抓安全的苏宝顺区长,说着说着激动了,指着一名工人骂了起来:“你妈了个巴子的,现在知道害怕了?你不想想,真要出事,全区跟你吃挂落儿不说,你妈你爸咋办?让他们痛苦后半辈子啊?!你必须去办班,学规程,还得罚款、扣奖金,让你小子以后长记性!”
过一会,没人的时候我问苏区长:“违个章就处罚这么狠啊?批评一顿就得了呗!”老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丫头,你刚上班,不懂井下出事的危险性,区里从严管理,也是让每个工人学规程、懂规程,按章做窑,这样才能少出事故。”
过几天聊天提及父亲时,他们都熟悉他,称赞父亲是够格儿的安全员,我脱口说了句:“我爸那活干得让人膈应,有人叫他“把头”,我忒不爱听!” 老区长肖春华人特好,扯着大嗓门对我说:“老闺女,咱矿上就需要你爸这样铁面无私、敢抓敢管的“把头”安全员,把头,把头,把住安全头道关,松是害,严才是爱,懂不?”
听老区长幽默的解释“把头”的含义,我开心的笑了,也懂了,父亲真是不容易,父亲真的了不起。
(四)
怎么都想不到,几年后的我也学着父亲当了一次女“把头”。
那是矿上组织的一次井下班组长骨干北戴河休养二日游,需要工会干部带队。因单位人手紧,领导想让我去,又怕就我一个管财务的女同志不好带这帮老板子,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带着整整一百个老爷们坐着两辆大轿车开进北戴河职工休养所。出发前领导要求我,让他们吃好、玩好、休息好,但中午一定不许喝酒,保证安全回来。
因为有前车之鉴,酒后海边游泳出现死亡事故,午饭前我一再告诫大家不要喝酒,以防万一。
可仍有个别老板子耍小聪明,偷着自带白酒。我眼睛不停地扫着这十桌人,发现有的拿着各种颜色矿泉水瓶慢酌慢饮,不对劲,肯定是酒!我疾步跑到厨房拿起一个大水舀子,伸到每个桌子前,表情比较严肃:“别藏了,把酒倒出来!快点,别求我,就是不许喝!”
有的人见我伸着胳膊立在桌前不走,不好意思地把酒倒在水舀子里,也有的拧上瓶盖送回了招待所,但有一个老板子急了,骂骂咧咧:就喝咋了?这也算违章?你个小丫头片子吃饱撑地没事干,一边呆着去!我也急了:你这就是违章,敢喝,回去我就扣你奖金!一把抢过满满的矿泉水瓶,把酒直接倒在地上,空瓶一扔走了。
只听见身后有人说:“这家伙雷子,也忒狠忒厉害点吧!” 还有难听的话,但我不生气,我也不后悔自己这样做,心里还偷着得意,想想父亲,那时得挨多少骂啊?我挨这点骂也值得!
(五)
父亲去世17年了,一直想提笔写写父亲,以此告慰父亲逝去的亡灵,想说的话很多,却无从下笔。
这些天,想写父亲的欲望特别强烈,坐在桌前,轻击键盘,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禁不住泪水盈眶。父亲很普通,可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用坚实的臂膀,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父爱如山;父亲很平凡,在井下一线,父亲像卫士,履职尽责,守卫着矿山的安全,父亲对矿山的爱,厚重朴实。
作为女儿,对父亲了解的不多,交流的也少,他在井下一呆就是三十年,工作上的不顺与烦心,从不给我们讲,再多的苦楚也是往自己肚子里咽,我那时很少与父亲坐下来,听他聊聊班上的事,现在想想我这做女儿的很内疚。那时,只看见父亲早出晚归,春夏秋冬,每天拎着干粮袋上班下井,下班回家,很少休息过,即使有病,也是吃点药就上班。
记忆中最深的就是父亲经常带回家的窑衣,很脏很重,有时抖落出很多的小煤渣子。母亲知道父亲爱干净,总是一件件用搓板把窑衣洗好,破洞的地方一针针缝补好。那时觉得父亲很辛苦,每天下井,脏、累不说,关键是危险大,有时一听到街上救护车刺耳的警鸣声,母亲和我们就特别害怕,担心父亲井下出事。
父亲在井下工作了三十年,没有豪言壮语,不会夸夸其谈,但他深深地懂得,安全生产,与每个矿工、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只有管得严才能少出事故,少流血,人平安,家庭才幸福,矿山才和谐。父亲用自己的行动,默默诠释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矿山的爱,履行着煤矿安全卫士的职责。
我为父亲骄傲,我爱我的“把头”父亲。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仅以此帖祭奠父亲,愿父亲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