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后的“情色”动画片,只能用高级来形容
每天一条独家原创视频
创作出了史上第一部陶瓷动画《海公子》, 片长15分钟,豆瓣评分8.4分, 网友幽默留言: “木偶和粘土总演电影, 陶瓷表示不服,于是也演了一部。 ”
 《海公子》瓷雕塑定格动画 2014
《海公子》瓷雕塑定格动画 2014
耿雪在工作室中
制作而成的定格动画, 片中唯美、色情、惊悚,交织在一起。 从没有人以这种角度展现过陶瓷, 看过的观众纷纷惊叹, 动画片还可以这样拍! 耿雪是吉林白山人,
央美毕业后,留在大学教书, 同时继续自己的创作。
 《金色之名》泥塑定格动画 2019
“陶瓷动画第一人”之外,
她也用泥塑拍出最新动画《金色之名》,
受邀参加201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
作为中国馆的四位艺术家之一展出。
汇集了耿雪近4年作品的个展,
正在北京筑中美术馆展出。
疫情期间,不能去到现场,
通过一条的视频“云看展”吧。
自述耿雪 编辑叶荔
《金色之名》泥塑定格动画 2019
“陶瓷动画第一人”之外,
她也用泥塑拍出最新动画《金色之名》,
受邀参加201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
作为中国馆的四位艺术家之一展出。
汇集了耿雪近4年作品的个展,
正在北京筑中美术馆展出。
疫情期间,不能去到现场,
通过一条的视频“云看展”吧。
自述耿雪 编辑叶荔
 点击观看《海公子》定格动画预告片
点击观看《海公子》定格动画预告片
定格动画《海公子》 :
陶瓷版的聊斋鬼故事
《海公子》是2014年,我的研究生毕业创作。
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七八年的陶瓷。每次给作品拍照时,我发现拍的图像可能比雕塑本身还强烈,而且特别好看。就想不如直接拿这些图像,做成定格动画。

中国文学中有一个比较奇特的脉络:志怪、志异系列。比如特别早的《山海经》,唐人的传奇笔记,宋代的《太平广记》,到了清代就是《聊斋》,都非常有意思,有的很短但又讲得很有趣,也会影射现实。
《海公子》是《聊斋志异》里的一个短篇,只有十来行,讲的故事意犹未尽。有一个张生,到了东海的一个岛上游玩,他感到寂寞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女子。张生跟这个女子喝酒,相处很亲密,女子突然大叫,“海公子来了”,就消失了。然后出现了一条蛇,开始追张生,缠着喝他的鼻血,张生想起身上的毒狐药,才把蛇弄死了。
为《海公子》设计的分镜脚本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导演,做道具,打光、拍摄。
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设计、制作了100多件瓷器。为了方便拍定格照片,人物是有关节的,就连场景里的植物,也都做成关节的,每个枝条都在摆动,非常逼真。
我当时倾心于早期的一些动画作品,没有电脑技术,完全是手工劳动。
 《海公子》被豆瓣网友打出8.4分的高分,网友留言:“《聊斋》里的‘鬼气’,被光洁空灵的瓷人表达得恰到好处”,“陶瓷所带来的听觉、视觉,甚至有触觉,妖艳、诡谲、寒气渗着骨头缝钻进心里。”
《海公子》被豆瓣网友打出8.4分的高分,网友留言:“《聊斋》里的‘鬼气’,被光洁空灵的瓷人表达得恰到好处”,“陶瓷所带来的听觉、视觉,甚至有触觉,妖艳、诡谲、寒气渗着骨头缝钻进心里。”
我们常说陶瓷有一种“玉质之光”,非常温润,尤其像以前龙泉釉的那种青色。在灯光下,陶瓷表面会形成一种流动的光感,我在拍摄中特意利用了这个“光点”,不断地有光影变化,表达不同气氛。让观众可以感受到陶瓷的性格和气质。
《海公子》当时拍了可能有1万多张照片,陶瓷的人物有大有小,小的10厘米、5厘米,大的就是头跟真人一样。
在陶瓷的领域,可能大家并没有这样去看待过陶瓷;而在影像领域,人们也并没有这样去拍过一个动画片,我觉得这样的事才有意思。
耿雪接受一条采访 景德镇是一个“野生”的课堂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最初学习雕塑基本功,2005年开始去景德镇学习传统陶瓷工艺。
 早期陶瓷雕塑作品 创作于2007年
早期陶瓷雕塑作品 创作于2007年
2005年,我在央美的雕塑系,因为一个课程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趟景德镇。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景德镇的陶瓷。景德镇,全世界只有这样一个样本,说短了也有1500年的历史,而且它没有断过,一直到当代。
刚到景德镇时,有一个地方我特别爱去,叫樊家井。家家户户都在仿制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陶瓷,不同的样式、釉色、花纹,比去一个博物馆看到的东西还要多,非常野生。我也向当地的老师傅请教,怎么成型,用什么泥、什么釉,有几十道工序。
第一次做陶瓷,我就非常喜欢,烧出来也很有成就感。当时我学的是雕塑,做过一些人体,就把它跟陶瓷日用品结合,做了一些瓷碗、果盘、酒盏,在里面装进一些“小人儿”。
好多人看到了都说我做的是小女孩,其实根本不是。
大家对女性创作者往往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从学生时代,我就不想要“女艺术家”的标签,所以有点刻意地去创作男性的身体,或无性别特征的人体。
在景德镇的学习,就是对传统的一种学习。





左滑查看更多
陶瓷雕塑《〈韩熙载夜宴图〉的一种表述》2006年
本科毕业创作,我做了《〈韩熙载夜宴图〉的一种表述》。里面那些瓷器小人,头跟身体的组装方法,用了“模件化”的组合,类似古代陶俑。
原画里女性的角色本来是唱歌、跳舞的侍奉者,但是我把她们变成穿得很体面;而男性官员反而变成裸体的状态。传统绘画里,古人往往按人的地位和性别来决定人物的尺寸,男的大、女的小,官职大的人大,官职小的人小,在我的作品里,男女尺寸都是一致的。
在个展开幕前调整作品《苏格拉底的广场》
我希望在作品中跟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比较深的联系。
当时2000年出头,整个当代艺术的气氛还是西方视角主导的,西方人来收藏,大家做的主题也多是身份、权力、性别。
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能真正地从自己的土里,长出一棵大树。 后来我在《聊斋》里找到了想要的故事。 2014年我尝试制作定格动画,便有了后来的三部影像作品《海公子》《米开朗基罗的情诗》《金色之名》。

影像装置作品《米开朗基罗的情诗》 2015年
《米开朗基罗的情诗》: 走到镜头前,亲吻了泥人《米开朗基罗的情诗》,是我2015年的影像作品。影片中,我走到了镜头前,像一个做雕塑的“演员”。不借助任何工具,把泥土不断雕塑成一个人体。
甚至最后,还给这具没有生命的躯壳,吹了一口气,仿佛给予了它生命。


影片配的字幕是米开朗基罗的十四行诗。原来的主题是米开朗基罗向他的同性爱人表达炽热的情愫。
米开朗基罗,是每个学雕塑的人的经典。2011年,我在意大利看到了他的原作。上面全都是石头工具留下的痕迹,我站在雕塑的前面,就好像能看到他在我面前工作,声音都能直接穿透过来打动我,非常震撼。
我在这个作品里做雕塑的手法,与米开朗基罗的做法正好相对应:他用工具,我是用手;他凿大理石,我推揉的是很柔软的泥土。我的表演,像是跟米开朗基罗对话。
点击观看《金色之名》定格动画预告片 《金色之名》: 现实的悲悯,与希望的未来
现在我是个新手妈妈,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新作动画《金色之名》,整个拍摄、制作就是在孕期时完成的,这也让整个作品有了不一样的意义。片中主角全部是手塑的泥人,在片长600秒的时间里,浓缩每一个微小生命的一生。

 筑中美术馆展览现场
筑中美术馆展览现场
这次在筑中美术馆,观众可以在十余米长的屏幕上,观看《金色之名》的完整影像:比真人还大的脑袋,粗糙不堪的躯体,撼动人心。
影片是由两个世界组成 ,其中“黑白世界”,其实是在隐喻我们的现实。
用泥土来表达肉身,这些小人物,不断地劳作,没有尽头,有一点无意义的感觉。但是人们就会持续地甚至不惜牺牲很多东西,一直去做这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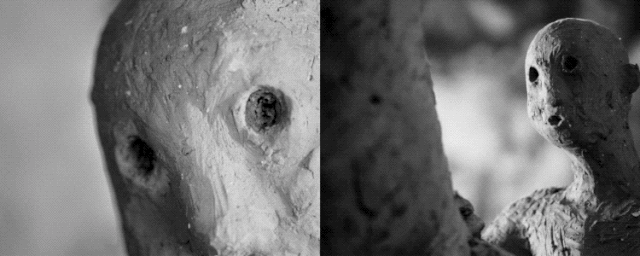
我用的泥土不是细腻的陶瓷的瓷土,它有沙粒、杂质,但是刚好可以表现,人在这世界上的经历。
小人们表面粗糙,眼睛张得很开,看起来“麻木而本真”。他们时不时互相起了冲突,有时候很暴力,镜头一转,又是生老病死的场面。

其中有一幕,一群小人上一个高台去献祭。这个画面我特意留了铁丝,没有修掉,让人感受一种被操纵的感觉。
影片中还埋了一个隐藏的线索,就是声音。像是一种宇宙音,声音噼噼啪啪的,那个“时间”是不断地飞速地倒流,就像不断地在流逝的过往一样。
黑白世界的最后,出现了一叶金色的船帆,像一个希望,或者是福柯说的“愚人船”,载着疯癫者和病人。
这个影片在展出的时候,展厅的地面上还有4个“管道”,观众需要俯下身子,才能进入“金色世界”的影像:悬浮翻滚的小人、无垠的落满金光的宇宙……这可能是我们向往的未来。
黑白是对现实的悲悯,而金色给人带来希望,两者形成对比。
《金色之名》制作花絮,素材来源:巩明春
拍《金色之名》的整个过程,花了近半年时间。当时我在北京租用了一个朋友的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团队。
定格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所有拍摄需要的泥人道具,都是现场手捏,大家常常从白天持续工作到深夜。因为泥土模型你等一下它就变干,要不停地给它喷水保湿,水多了它又断裂开了。
布光、摆位、定型、拍照,有很多的挑战,前后拍了9000多张照片,最后做成动画。
耿雪在展览现场调整模型,这些小人是根据《金色之名》中的泥塑翻模而成的青铜雕塑,大小不一,刻意营造一种皮影的戏剧效果
科技的颠覆下, 还得跟着自己生命的节奏去创作《金色之名》的创作契机,是因为我受邀参加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展览。这年双年展的主题是:一个“有趣”的时代。
这个“有趣”是带引号的。因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世界的变化之大,而科技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人的寿命变得很长,人可以不死,人的爱情可以跟虚拟的机器发生关系,不再需要一个真实的伴侣。
——这些对我们以往所有的文化艺术,是有颠覆性的。
以往所有的文艺创作,都离不开生死、爱情的主题。它的一个前提是:生命是有限的,人是有疾病、痛苦的。如果人连最基本的这些东西,都因为科技的进展,被消解掉了的话,其实未来是什么,我们很难说得清楚。
我是在这样一种感受里面,去构思《金色之名》这个故事的。在创作之前,我也有跟我的老师徐冰讨论,“金色世界”就是想表现一种我们未知的、未来的世界。

我拍的影片跟比较商业的动画片肯定还是不一样。我的创作会包括自己的写作、编剧,自己画分镜头,在《金色之名》的创作过程中会和团队一起去设想怎样拍摄、有专业的导演刘大鹏帮忙,他是我的同学。
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科技,在推动人类进步的作用上,可能比艺术创作要大得多。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很关注新的东西,但在创作技法上,我用的还是一种传统的手工方式。艺术创作急不来,有它自己的规律。
不可能去把自己作为机器人一样更新,我们还是一个肉身,要跟着自己生命的节奏。
鸣谢:筑中美术馆
部分图片由耿雪、奕来画廊提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