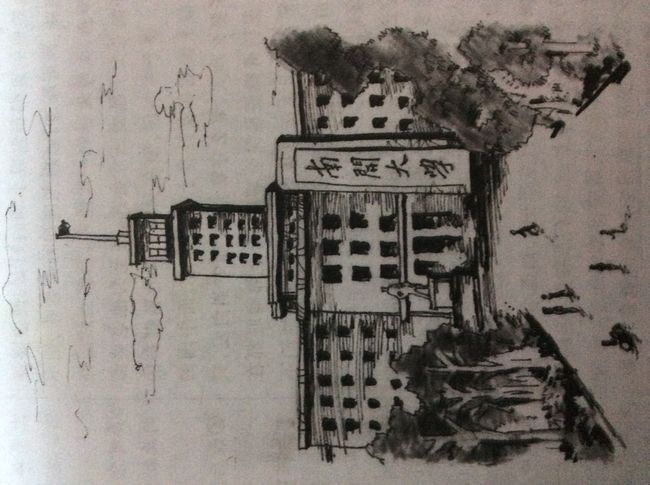我的校友,国际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说:"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十年前我初踏进这个校园时,其实颇有些不以为然天津大街上众多骑着自行车雄赳赳气昂昂向前冲的中年阿姨吓住了初来乍到的我。她们普遍喜欢烫大卷花头,描卧蚕眉,涂烈焰红唇,起风时用黑纱巾兜头包住脸防沙尘。我非常讶异距首都咫尺之遥的大城市,怎么会如此不时尚,以至于对南开也连带着起了鄙薄之心,料想它会与天津城给我的第一印象一样,保守,自得,土气,与时代的脚步总慢着半拍。
那时候,除了校友中出了周恩来,我对南开几乎一无所知。
确切的说,我大学生涯的起点是校本部两公里开外的迎水道校区,也就是合并前的天津对外贸易学院所在地。此地名曰"王顶堤",地理位置上似乎已近市郊。有附近居民养的大白猪三不五时跑到校门口,骚扰一下站岗的警卫。从大门口进去,一座教学楼,两栋宿舍楼,食堂和操场各一,一眼几可望尽,其貌不扬的弹丸之地,让人对象牙塔的各种美好想象幻灭得连一丝火星都不剩。更不用说毗邻的水产仓库总是十分慷慨一有点儿小风便让海产品的腥咸味道大肆弥漫,导致大一的我写给高中同学的信老是透着股咸带鱼的寒碜味儿。
就在这个地方,我度过了我的18岁。参加了N个社团的校区分部,与同宿舍的五位美妞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大一暑假举行的军训中学会了走漂亮的正步,并且首次对小强这种微型家畜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
原谅我主观上对于这一年记忆的信手涂抹。它当然没有如此不堪。相反,它和大多数人的18岁一样,明媚,灿烂,如同一年中最美好的某个清晨一样甜蜜且脆弱。只是在那时,我的确并未对南开产生多么深厚的感情。要知道,我18岁那年,南开大学已经80岁了,与它同出一脉的南开中学已是百岁高龄。那时候,我不知道一座鄙旧的思源堂,凭吊着南开初创时的筚路蓝缕;不知道大中路上辞旧迎新的校钟,记载着南开抗日烽火里的辗转求存;不知道西南联大的巅峰时刻,南开曾与北大,清华风云际会,共筑伟业;也不知道面前这座劫波度尽总是从容沉静的校园其实卧虎藏龙,有许多声明如雷贯耳的学术大家于此默默奉献。凭我浅薄的识见,实在无以知晓它皮肤的褶皱拓写了多少历史的纹理,它看似老迈的躯体内又沉淀着多少智慧的精华。在我18岁的眼里,它只是不够华美稍逊风骚,在世纪之交泥沙俱下的洪流中比起善于扬名立万的高校甚至显得默默无闻。我对它,除了发自本能的对母校的依恋,还总是若有似无地,带点淡淡的失望。
后来,我搬回了校本部,并在这真正意义的南开校园里,一呆就是5年。
5年,就算成小时就4万多个,一个让人惊愕的丰腴的数字。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想我一定会仔细分配,小心安排,让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它恰如其分的用度,不留半点虚掷与遗憾。
真的,我不止一次设想过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用足够多的时间沉浸在于所有可及的课堂与讲座,再听素衣华发的叶嘉莹先生从瘦小的身体里发出韵致铿锵的声音谈诗论词,纵情吟咏;看一袭白衣的范曾先生怡然自得的咬着烟斗,慢条斯理地讲大美无言,大音希声。我一定会有充分的耐心和澎湃的欲望,老老实实背诵老师从广袤无边的古典文学园地中精挑细选的每一篇华章,爱上于古人幽微情感中推敲大智慧的快意。我一定能聚精会神忘情于物外,在新图书馆浩如烟海的百万典籍中,一一捕捞"必读书目"上密不透风的名字。我一定会有足够的热忱,去完成对一个社团的专情,无论是去辩协意会舌战群儒的周恩来,抑或到剧社遥寄成长于斯的曹禺
如果可以重来,我想我会再多几次,用脚步丈量从宿舍到教室那段芳草伶仃绿树成行的小路。我会在波光粼粼的新开湖畔多坐几个下午,让嫩绿的垂杨柳枝随着微风,一下一下,含笑带怯似地抽打在肩膀上。我会多到文科楼上几节自习,在午后煦暖的阳光里,把书页轻轻翻动出欣悦的微响和悠然的墨香。我会至少去一次旧图,借上两本绝没可能用上的理科图书和练习册,只为在那的借阅记录上留下我来过的证据。我还想去拜访一次思源堂边那座静谧小楼"宁园"的主人,假如他未曾在一个冬日溘然长逝。在国际数学界,他是人们敬仰的大师,是"微分几何之父",可我们见到暮年定居于此的他,总是慈雅而亲和。拜访过他的学生有人在背后恭敬地叫他"太爷",说"太爷"院子里的墙上还挂着金华火腿,"太爷"在冬天喜欢穿着旧式棉袄,躺在床上晒会太阳。
我总是觉得,如果可以重来,我会发现一个不同的南开。我会早早地觉悟,抹去对它的所有误读,从它素朴淡泊的外表之下发现一种优雅超然的态度和光华内敛的锋芒,像如今这样,领悟它不事张扬却胸怀沟壑的独特气度,为此倾倒,终生不渝。
多么希望,一切都不只是如果。
很久以后,2005年夏天,我拿着打印装订好的毕业论文成稿来到相伴数年的文科楼,在门口的仪容镜里看到了一个与进校时截然不同的自己,这才恍然意识到,那平静如流常被我肆意挥霍的校园生活已潜移默化着重塑了我的气质,在其上密密打下了仅属于南开的印记,而我对南开的情感,也在某个难以确定定位的时点发生微妙的转折。我深信这是一种相互的陶铸与儒染,那朝夕相对的两千多个日夜。我有点明白以往被我不齿的言情剧对白为什么会拥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我知道之前,我已经爱上你了——原来后知后觉的感情的确客观存在着。可我,已经要离开了。
那个6月的傍晚,我像个失了心的魂,在主楼到文科楼那段路上反复游荡,脑子里满满当当的只有一个念头:也许这辈子,我再不能在这些教室里,心无旁骛地,单纯地,满足地,做个学生,听老师讲上一课了
一段全新的旅程即将展开,无数次在想象中模拟过的,无比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准备开始大段大段地铺陈,我却在连气息都稔熟的校园里茫然地停住脚步,心中充满眷恋。
离校后千里南下,到沿海经济特区的新闻界闯荡,几年中遇到许多人。每与人言及南开,所得多是美誉,而严谨,务实,勤勉,善思,几乎不约而同的成为了他们眼中南开人的群体特征。我不由庆幸自己在最美好的年华里,能得到一份如此丰厚的滋养,也因此明白,一所学府帮它的学子锤炼怎样的品格,原来比教给他们多少知识还来得重要。
今年年初,调回北京工作的我终于得了机会故地重游。站在有着美妙弧线的东门外,毛泽东题写的"南开大学"四个金字在久违的北方冬季阳光里熠熠闪烁,我忆起十年前爸妈陪着我,拖着大包小包,沿大中路从还没重建的老东门一路走到体育馆注册的情景。"十年"这个单是想一想就要教人后背发凉的词,轻易地洞穿了我。
我拿出手机,打给留校任教的老同学:在南大商店门口碰头好么?
他说,好的。俄顷,他又打回来,急急道,别介,你还是在东门等我吧,南大商店已经没啦!
那一瞬间,我有些怅然若失,而后想起校歌里唱的,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大概意思就是,时不我待,要不断追求进步。南开的骨子里,是涌动着这么一股子新陈代谢旺盛的激情的,我不能自私地要求它永远是我记忆里那让我刻骨铭心的模样。
这一次,从西向东,走过如流云一般优美舒卷的东方艺术系大楼,走过顶天立地的周恩来塑像,走过端凝庄严的主楼,走过各具特色的化学楼,范孙楼,伯苓楼,圆阶,走过刻着"智圆行方"的钢塑,热闹依然的西南村市场,走过拔地而起的新学生的宿舍,新物理大楼,APEC研究所,一直到白堤路上的西门口。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师傅掉头,从学校里面再穿行一次。
路上行人不多,三三两两,都迈着从容的步子,一如既往。司机把收音机调到正播着的频道,呵呵乐着,踩油门的脚一路加劲。
我说,师傅,麻烦你开慢一点。
慢一点,再慢一点。我打开车窗,十年前的风扑面而来,牵扯着新图的书香,三食堂的炊烟,还有浴园热烘烘的水蒸气味儿,从我的头发中汩汩流过。乐群路,敬业路,五虎路,大中路。14宿,实习餐厅,鸿鹄书店,旧图书馆。每一处恍如昨日又恍若隔世的旧景都让我有与故交久别重逢的哀矜与欣喜。经过马蹄湖我竟然在素灰色的冬天里闻到一池荷花绽放的清香。遥望着湖中央的周恩来纪念碑,我觉得不能找到一种表达,可以比他那句所有南开人都耳熟能详的话更贴切——我是爱南开的。
本文刊登于2009年3月《萌芽》杂志下半月刊的第487期,新概念作文
原文刊载于本书的30-31页,原题目:《我爱南开,和我最美好的年华》
作者:王越(第一届新概念一等奖,现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驻京记者)
我高二那年读到此文,第一次对大学生活有了无限的憧憬,后来无数次重读,又带到大学,最后又完整的带回东北家中,每每读来,感触都不同。因为此文,我对南开的认同增加到不知道什么程度,甚至说自己已经把南开当作自己从未读过的母校,一见到南开人,我会倍感亲切的与其谈起南开的点点滴滴,甚至有的南开人竟然惊讶的认为我比他真正的南开人更了解南开;第二个影响,就是这篇文章影响了我大学生活的情怀,怎样珍惜大学的岁月,怎样与其告别,我都受到这篇文章的神韵之传。所以,当我再一次翻到这篇文章重读之际,我下定决心,将这篇长文,一字不差的打成电子版,以供日后重读,再者纪念即将搬家的近百年名校。毕业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爱西安,和我最美好的年华》,其写法就是参照此文,情怀虽减,但真情不变。
愿读完此文的后来人,珍惜你生命中最最美好的学生时代,珍惜那些美好的年华。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唯有紧紧的抓住时间,光阴溅落之后,才不至于老泪纵横……
半夏长安编辑
2016年2月2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