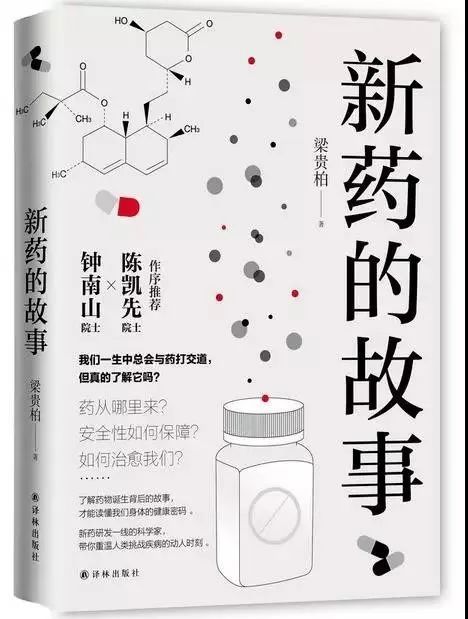钟南山:药物创新是艰苦的历程,这本书能让我们体会其真谛

IDG君写在前面:
疫苗是如何研发出来的? 为什么不能加速这个过程?
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疑问。新药研发,耗时耗力。 一盒小小的药剂来之不易,背后是一套成熟强大的制药体系。 疫情当下,你我有必要了解,一种新药物是怎样问世的,中间会经历些什么…才能明白我们一直以来所面临的的挑战,人类为之付出的努力,以及背后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的创新精神。
今天就摘取梁贵柏所著《新药的故事》一书中的一个片段,为你讲讲人类与细菌抗争的历史。
作者 |梁贵柏
钟南山院士在《新药的故事》一书的序言中写到:“药物创新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什么是创新的动力?我相信每一个原药创新的科学家,在研究开始绝不是先想到这个药研发出来后会对他带来多少利益,而是出自对“未知的未知”或“已知的未知”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对广大患者,特别是完全无助、在当时无药可治患者的强烈责任感。科学家对未知的好奇心,永远是他们执意追求的动力……我们可以从这本新药研发历史的科普书中体会到创新的真谛。”
《新药的故事》的作者梁贵柏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长期致力于中美医药界的交流与合作。他从一位一线科学家的专业视角出发,讲述十余种对人类健康产生深刻影响的新药的故事。
他在书中写到:尽管一粒药片的成本只有几毛钱,但药厂在研发过程中的投入却是天文数字。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开发一种新药的耗资超过10亿美元。所以,在制定药价时,大药厂必须考虑其专利保护的年限以及市场的需求,以期收回成本并有盈余。最后的药价与药片的生产成本基本上是无关的,只有这样,制药公司才有实力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新药研发,我们才有希望攻克那些还在威胁人类健康的癌症和其他疾病。
掠过天际的黑天鹅
药物研发与所有科学研究一样,都是在探索未知的世界。
但是“未知”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已知的未知”,一类是“未知的未知”。
已知的未知有很多,严格来讲,每一个科学家的工作都是在试图发现某一个或者几个已知的未知。所有立项的新药研发也是一样,都是在寻找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要找什么,有靶点,有目标,不管最后找到或者不到,都属于已知的未知。
这里包括研发或承重可能出现的多重事件,比如心率紊乱、肝胆代谢酶受阻、肾功能受损等,尽管这些结果都无法预见,因为我们实现知道这些情况有存在的可能性,并且一定会去可以筛查,如果它们一旦发生了,项目团队也都有应对策略。
那么未知的未知有多少呢?答案是不知道。纳西姆·塔力布在《黑天鹅》里把这种未知的未知比作“黑天鹅”。在18世纪欧洲人发现大陆之前,他们见过的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所以在当时欧洲人眼中,天鹅就只能是白色的。知道欧洲人发现澳洲,第一次看见黑天鹅之后,就颠覆了前任从无数次对白天鹅的观察中所归纳出的而一般性结论。
这些黑天鹅是不可预见的,它们一旦掠过天际,便会影响巨大。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中不断飞过的各种生物里面,时不时就会有无人知晓的、真正的黑天鹅,其中有一些招摇过市,能立刻引起轰动,还有很多悄然略过,只给我们留下短暂的一瞥。
而机会总是留给慧眼识珠的有准备之人,他们能抓住那些一闪即逝的机会。
就像青霉素的发明,就是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这个发现是人类生存和致命细菌(又称病原菌)的长期斗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青霉素被发现之前,细菌的感染让人谈虎色变。肢体上一个小小的创伤常常因为感染而不能愈合,最后只能截肢,如果不及时的话,很有可能会夺去患者的生命。
1928年,英国伦敦大学圣马莉医学院(现伦敦帝国学院)细菌学教授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室的地下室发现,他前几天忘了加盖子的细菌培养皿中,长出了一种蓝绿色的霉菌,而在这些蓝绿色的霉菌孢子周围,细菌的生长被抑制住了,形成了一个无菌的圆环。弗莱明教授敏锐地判断这些蓝绿色的霉菌孢子里一定含有某种抑制细菌生长的化学物质,他将其称为“青霉素”。
这个很偶然的发现引起了细菌学家们的注意,但是由于没有实用的生产线路,包括弗莱明教授本人对于青霉素的研究都曾一度中断。直到1938年,牛津大学的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伯利斯·钱恩和诺曼·希特利领导的团队成功地从青霉菌里提炼出了抗菌的化学物质——青霉素,才使得这一重要发现造福于人类。
为此,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弗莱明教授是第一个注意到青霉菌落的周围有个圆环的人吗?从记载来看也不一定是,但在他之前,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只黑天鹅。弗莱明觉得这些亮环里一定有些什么奇妙的东西,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寻找,我们才有了突破性的抗菌药——青霉素。
没人能准确预测下一只黑天鹅在何时出现,但发现和捕捉下一只黑天鹅的人,一定是有准备的人。
人类和细菌的永恒战争
细菌的历史比人类长很多,它们是这个星球上的老住户了,人类整个历史上都有细菌的亲密陪伴。但是,在农业文明以前,人类与细菌基本上还是能和平共处,因为那时人口密度很低,零星的细菌不可能有机会大面积地快速传播。直到谷物和牲畜的驯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定居的村落逐渐发展到集镇,先前零星的细菌感染在高密度的人群聚居地有了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再碰上传染性强的细菌,就可能会发展成可怕的瘟疫。
早在公元430年前后,就爆发过人类历史上著名的“雅典大瘟疫”,持续了近4年,导致近半数的希腊人惨死,哀鸿遍野,几乎摧毁了希腊城邦。到了20世纪初,寻找抑制和杀死细菌的方法和药物已经成了医药研究的大热门。
1943年,在默沙东制药的支持下,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赛尔曼·威克斯曼从他的实验室里发现了链霉素。链霉素的问世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因为那是当时唯一能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
随着青霉素、链霉素等多个天然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在与细菌的竞赛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细菌感染大多数能很快被控制住。但好景不长,这个优势是短暂的,人类刚从传染病和瘟疫的阴影里走出来,稍稍喘了一口气,细菌对这些抗生素的反击战就已经初见成效——具有抗药性的变异细菌被发现了。
抗药性或耐药性(Drug resistance)是指药物治疗疾病或改善病人病症的效力降低,这是进化论的有力佐证。细菌基数足够大,基因的分布极广,而且各种变异出现得又很快,绝不是几种抗生素就能赶尽杀绝的。
研究结果表明,在青霉素使用之前,对青霉素有抵抗力的细菌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在没有使用青霉素所带来的“自然选择”的压力环境中生存,它们的优势不能体现出来,只能维持在“劣势物种”的低水平。
青霉素的问世,给没有抵抗力的正常细菌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极少数有抵抗力的“劣势”细菌活了下来,并且把这种耐药特性遗传给了它们的后代,产生了有抗药性的变异细菌。
一代又一代,随着变异不断发生,能产生抗药性的变异“被选择”了,抗药性也越来越强,给人类的生存和医药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当各大药企的研究人员都在不断摸索,不断碰壁时,1976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从一种链霉菌的发酵液里发现了一个新型的天然抗生素——噻烯霉素(Thienamycin),随后被定义为碳青霉素类抗生素,这正是医药界所苦苦寻找的新一代抗生素。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类抗生素应该和有抗药性的细菌一样,也早就存在了,但从筛选技术上讲,只有在抗药性的细菌被“选择和富集”了以后,能够杀死这些变异细菌的抗生素才有可能被发现,因为它们反过来也被这些新型的耐药细菌所“选择”了。
这一次,我们学乖了。我们无法阻止抗药性的出现,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的发生,延长抗生素的使用周期。因此,为了延缓针对碳青霉素有抗药性的细菌变异被选择和富集,一些国家对这些新型抗生素的使用做了非常严格的控制,以保证其疗效,避免滥用。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滥用抗生素会恶化抗药性的问题?这主要是一个轮次的问题,细菌每隔几个小时就繁殖一代,使用抗生素越频繁,细菌被选择的轮次也就越多,抗药变异的富集也就越快,抗药性就越强。
如果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已有抗药性的细菌就会自动退化,失去抗药性。因为保持“抗药”很消耗能源,这些细菌反而成了累赘,繁衍了几代以后就被边缘化了。
尽管如此,或早或晚,在多种抗生素的持续压力下,超级细菌还是跟我们面对面了。
超级细菌并不是单纯地指某一类细菌,人们一般把对几乎所有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细菌统称为超级细菌。这个大家族的成员还在不断地更新,越来越多。
面对这场人类和细菌的持久战,制药人肩负重任。
小结
变异自始至终存在,进化永远不会停止。新药研发的历史也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斗争史,随着医药领域的科研人员不断活跃在研发的第一线,为了人类的健康事业持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部人类的历史将会被一直书写下去。
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坚持与执着是创新者最重要的素质。在本书提到的创新药物中,有哪个不是通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创制成功的?
愿你我带着科学家们这份对“已知的未知”,或“未知的未知”的好奇心砥砺前行,越走越远。
END
你还不能错过:
不要陷入温柔安乐窝的陷阱 | 对话IDG资本首席畅想官刘慈欣
 进化永远不会停止
进化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