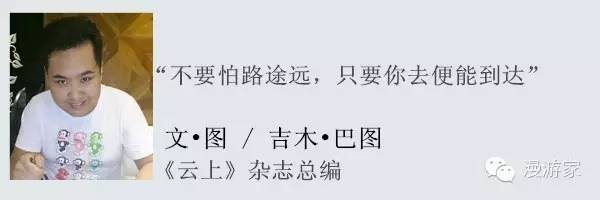- java cas aba问题_Java CAS操作的ABA问题
自考大三学狗
javacasaba问题
CAS介绍比较并交换(compareandswap,CAS),是原子操作的一种,可用于在多线程编程中实现不被打断的数据交换操作,从而避免多线程同时改写某一数据时由于执行顺序不确定性以及中断的不可预知性产生的数据不一致问题。CAS操作基于CPU提供的原子操作指令实现,各个编译器根据这个特点实现了各自的原子操作函数。来源维基百科:C语言:由GNU提供了对应的__sync系列函数完成原子操作。Windo
- 焦点父母课堂洛阳第二期第23天分享
耿丽娟
今天中午一家人吃过饭,看天气挺好,大姐就提议去三清洞玩,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我们便驱车前往,到达目的地停好车,就开始爬山,道路两旁好多卖玩具小吃的,孩子又控制不住跟我商量想买玩具,但是这次拒绝了孩子并跟他讲了道理后,孩子也欣然接受了,并高高兴兴的开始爬山了,也没有像之前不给买就开始不高兴抱怨了,聚焦每天一小步,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 刘洺松成长记17
向着太阳歌唱啦啦啦
刘洺松今天105天啦!上午,妈妈带你去医院测评了,医生阿姨为你做了各项评估,测试得分为94分,正常。是不是所有妈妈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超人呢?在妈妈心中,你就是superboy.永远是superboy.刘洺松健康快乐长大,爸爸妈妈爱你!
- 2019.2.4-2.10周复盘
幸福快乐的小熊熊
一健康管理这周有三天走的挺多。二财务风险信用卡,花呗还款。三家庭经营春节期间,家人都有聚会,家庭氛围总体还是比较和谐的。四人际社群grace阅读营自告奋勇报了打卡提醒员。小鹿老师电影群,很幸运的中了育儿课程。五学习成长听释若老师写作课,最后时刻完成第2次作业。六休闲活动这周除了和家人朋友聚会。就是完成作业,看了春晚。本周收获这周能完成第2次作业,对自己也有了信心。试着培养一个微习惯,小到不可能失败
- c语言如何宏定义枚举型结构体,C语言学习笔记--枚举&结构体
搁浅的鲎
c语言如何宏定义枚举型结构体
枚举枚举是一种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它用关键字enum以如下语法格式来声明:enum枚举类型名字{名字0,名字1,。。。,名字n};枚举类型名字通常并不真的使用,要用的是大括号里面的名字,因为它们就是常量符号,它们的类型是int,值则依次从0到n。如:enumcolor{red,yellow,green};就创建了3个常量,red的值是0,yellow的值是1,green的值是2。当需要一些可以排列
- 钉钉 Ubuntu x64 版本安装与应用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钉钉是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企业通讯和协作平台,集成了即时通讯、日程管理等功能。本Ubuntux64版为64位Linux系统用户提供了专属的安装包。通过简单的命令行安装步骤,用户可以享受到支持窗口缩放的便捷应用体验。该软件包已经经过测试,确保兼容Ubuntu系统,并随附readme.txt文件以指导用户安装。1.钉钉应用简介钉钉是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企业通讯与协同办
- Arduino小车遥控器构建指南
轩辕姐姐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本项目基于Arduino微控制器平台,实现通过蓝牙设备对小车进行远程控制。它结合了硬件搭建、编程和无线通信技术,适用于电子爱好者和初学者。项目中,Arduino板作为控制中心,接收蓝牙模块的指令来控制小车的运动。项目包含“蓝牙指令文件”处理通信和“材料的清单”详细列出所需硬件组件。学习者通过PPT指南进行硬件搭建和编程,最终实现小车的遥控操作。1.Arduin
- Spring框架整合Redis哨兵模式的实战教程
轩辕姐姐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Spring框架作为Java企业级开发的重要组件,与Redis高性能键值数据库结合,特别是在其哨兵系统支持下,能实现Redis服务的高可用性。本文详细阐述了如何在Spring项目中整合Redis哨兵模式,包括依赖添加、配置哨兵系统、创建连接工厂、配置RedisTemplate以及异常处理等关键步骤。通过整合,可以确保应用数据存储和缓存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适用于需
- 企业级3D TLC?看英特尔专家怎么说!
weixin_33691817
也许有人会说,3DNAND有什么好说的,三星早在前年就发布了3DV-NAND,就是基于3DTLC设计的,48层,单Die容量256Gb;此后,SKHynix、东芝/闪迪、Intel/美光等豪门都开始涉足3DNAND产品。但需要提醒的是,在这里谈论的是企业级产品市场应用。考虑到频繁读写,以及企业级应用场景对可靠性、稳定性的需求,专业人士指出,这是完全不同的市场。顺便说一句:企业级闪存产品应用,2DM
- 《降E大调夜曲,作品55之2》
Zoe周0919
肖邦简介:《降E大调夜曲,作品55之2》此曲具有即兴曲式船歌的风味。乐曲开始第一个音像山巅上高高挂起的一盏明灯,随后的颤音像明灯在闪闪发光,照亮了前进登顶之路,此情此景也可以说是肖邦高贵的气质及其光辉形象的体现。曲调明朗秀丽,具有船歌的优美安祥;对答式的双重旋律,非常甜蜜和谐。像是肖邦的不幸得到了亲人的同情和安慰,也是肖邦喜悦心情和高贵气质的体现。创作背景:肖邦《降E大调夜曲,作品55之2》,作于
- 《解忧杂货店》——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芝麻开门呼
浪矢老爷爷创造了这样一个温馨动人的现实乌托邦世界——解忧杂货店,无论你问出多么不可思议的问题,隔天都能在牛奶箱里找到答案。书中讲述了5个不一样的故事,围绕着丸光园和杂货店大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找到重叠的那道线。每一封回信里的人们如迷途的羔羊,站在人生岔路口,为了抉择而犹豫。他们有的纠结继续参加比赛还是陪伴恋人最后的时光,有的纠结是否同父母一起逃跑过着隐居的日子,有的纠结要不要
- USB (四)基于 STM32 USB的开发
文章目录官网demo基于官网demo考虑的事情usb代码的架构及接口USB数据流程USB中断枚举复位挂起唤醒usbdevice收数据以MSC为例usbdevice发数据以MSC为例应用处理流程其他描述符官网demo软件代码在官网是存在的:STSW-STM32046开发板对应的是:en.stm32_f105-07_f2_f4_usb-host-device_lib\Project\USB_Devic
- Gitee和GitHub的主要区别
Botiway
FlaskWeb云计算giteegithubpython
Gitee和GitHub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服务器位置与访问速度GitHub:服务器位于美国,全球用户访问速度较快,但国内用户可能遇到访问缓慢或不稳定情况。Gitee:服务器在中国,国内用户访问速度更快,稳定性更高。用户群体与社区GitHub:拥有全球最大的开发者社区,用户遍布世界各地,国际化程度高,汇聚了大量知名开源项目和顶尖开发者。Gitee:主要面向中国用户,社区以中文为主,更符合
- 香煎鸡排,看大厨石天冬怎么做?
78348647e955
第三集:香煎鸡排石天冬与苏明玉第一次相遇,当霸道明总和憨厚厨子相遇,在餐厅开始萌生不可描述的爱情故事。香煎鸡排1.鸡腿去骨成鸡排,在鸡排的横切面上划上几刀,使得腌制更入味。2.准备腌制的配料,洋葱切丁,指天椒切丁,香菜。3.腌制加入适量啤酒、盐、糖、胡椒粉、橄榄油,和鸡排一起腌制30分钟。4.热锅倒入橄榄油,大火鸡排两面煎至金黄即可。
- 自恋母女间的十根毒刺
谭知汶
在自恋母女间存在着致命的十根毒刺:第一根毒刺:女儿总是想得到爱和赞许,但是却永远无法取悦母亲。你会在很多电视剧看到过女儿在生气抓狂哭的时候讲:“为什么我怎么做你都是不满意!这就是女儿总想取悦母亲,但她永远无法令母亲满意!第二根毒刺:母亲更在意事情看上去好不好,而不是你感觉怎么样。母亲在孩子出门之前会给你收拾得漂漂亮亮,她是为了好看,但至于你穿这身衣服跑步舒服不舒服,她压根不管。甚至在你找男朋友时,
- 第二章 父与子
克雷
哥哥和姐姐的婚姻奶奶埋葬在离部落十多里远的一座山丘上,这是族人传统的埋葬之地。从这里往下看去,也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雪原,就像在家里一样。示罗希望奶奶能有灵魂,在这个美丽的山丘上和很多逝去的先人的灵魂一起,永远不会孤单。生活还要继续,生活在小部落的人们还要和大雪严寒抗争。虽然羊羔还在不断冻死,狼群还在不断袭击牧场,但是人们互相救济,互相援助,终于阳光开始强烈起来,大雪也被驱散,部落山岗平台上那棵硕大的
- 元气森林哪个口味好喝?最好喝的口味不容你错过
氧惠购物达人
元气森林现在口味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达到了10款左右,还不断地有新口味推出,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选择自己适合的口味。购物、看电影、点外卖、用氧惠APP!更优惠!氧惠(全网优惠上氧惠)——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抖客+淘客app!2023全新模式,我的直推也会放到你下面,送1:1超级补贴(邀请好友自购多少,你就推广得多少,非常厉害),欢迎各位团队长体验!也期待你的加入。氧惠邀请码888999,注册就帮你推广
- CVE-2005-4900:TLS SHA-1 安全漏洞修复详解
Nova_CaoFc
运维日常技术博文分享安全linux服务器运维
前言在信息安全日益重要的当下,任何微小的加密弱点都可能被攻击者利用,从而导致数据泄露、流量劫持或更严重的业务中断。本文将结合实际环境中常见的Nginx配置示例,深入剖析CVE-2005-4900(TLS中使用SHA-1哈希算法)的危害,并提供完整、可操作的修复流程。一、什么是CVE-2005-4900漏洞CVE-2005-4900定位于TLS协议中使用SHA-1作为消息认证和签名哈希算法的安全漏洞
- 一架飞机正副机长是母女,获赞最酷飞行员母女照
露露的甜生活
和妈妈一起工作的感觉怎么样?美国这对母女的工作照最近在推特上曝光,被网友直呼是「史上最酷母女照」!达美航空这班从洛杉矶飞往亚特兰大的班机,由WendyRexton担任正驾驶,而在她身边的副驾驶正是女儿KellyRexton。航空大学的校长JohnR.Watret也是这班机的乘客,上飞机没多久,便听到隔壁两个从驾驶舱参观回来的孩子说「开飞机的是一对母女」。身为航空校长的他,有感于这种情况相当难得,于
- 从近日爆红的“猫爪杯”看星巴克的“网红”营销策略
爆米花POI
最近星巴克又又又火了,起因是一款长相呆萌可爱的星巴克“猫爪杯”爆红于网络。有人竟然为了一款杯子通宵排队,更有甚者在店内大打出手。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款价值上千(某宝上搜索许多店家标价1000+,官网已断货)的杯子究竟长啥样:图片发自App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款非常有创意,很有少女心的杯子。这是星巴克樱花系列商品之一,是当季流行元素。首先,这款杯子的设计的确很走心,一下子抓住了一批女孩子们砰砰跳动的
- 类风湿关节炎的关节症状
刘本胜老师
主要对称性侵犯小关节,尤其是手关节,其次是趾、膝、踩、肘、肩等关节。可分为滑膜炎症状和关节结构破坏的表现,前者经治疗后有一定可逆性,后者很难逆转。1.晨僵病变的关节在静止不动后可出现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僵硬,活动受限,如胶粘着的感觉,适度活动后逐渐减轻,尤以晨起时最明显,称为晨僵。约95%以上的类风湿关节炎病人,可出现晨僵,晨僵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可作为判断病情活动度的指标。2.关节疼痛和肿胀往往是最
- 2022年2月13日中原焦点团队中27第272天分享
流星蜗牛
当我对孩子说:"无论怎样,你在妈妈心目中都是最棒的!"我无法体会孩子的感受。当孩子说:"无论怎样,你都是我最好的妈妈!"我的心里突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酸楚,虽然孩子是照猫画虎,却也是真挚的爱!想想,好像从来没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无论怎样,我都是最棒的女儿、学生、妻子、朋友等等",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做到最好,证明我是最棒的那个诸多身份,最终。
- 前后端分离场景下的用户登录玩法&Sa-token框架使用
两种方案的token、用户登录信息都存储在redis中!!方案一该方案是前端把token和token有效期一起加密存储到浏览器的localStorage中,每次请求时调用前端的getTokenIsExpiry()获取token并检查token是否过期,过期则remove并跳转登录页,这样前端有个问题就是前端也要知道token的有效期,需要和后端的token有效期保持一致,而后端则提供两个拦截器,分
- 洛谷二分查找题目详解
方俊涵
算法c++数据结构
B3881[信息与未来2015]拴奶牛题目描述有n头奶牛,有k个木桩,每个木桩有一个位置,一个木桩上只能拴一头奶牛。由于奶牛好斗,所以在拴奶牛的时候,要求距离最近的奶牛的距离尽可能大。例如n=4,k=6,木桩的位置为0,3,4,7,8,9,此时为下图。OllOOllOOO034789有许多种拴牛方案,例如:0,3,4,9:此时最近距离为1(3,4之间);0,3,7,9:此时最近距离为2。输入格式三
- Spring7个事务传播行为和5个隔离级别
青秋.
springjava数据库
传播行为事务传播行为是为了解决业务层方法之间互相调用的事务问题。事务方法A被事务方法B调用,就要指定事务如何传播,是两者共用同一事务还是另起一个新事务。图解spring中七种事务传播行为终于有人讲明白了_spring七种事务传播行为-CSDN博客1.REQUIRED@Transactional注解默认使用就是这个事务传播行为。如果当前存在事务,则加入该事务;如果当前没有事务,则创建一个新的事务。2
- 随笔21
菜菜菜小姐
今日的关键词:人生若只如初见。最近常常在想这句话,人与人的相处真是很奇妙。我觉得距离感和分寸感真得很重要。可能大概是因为我开始社恐了吧。“社恐”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可能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一点都不像,恰恰相反,在外人眼中我大概是“社交牛逼症”的那一位。其实,只有自己才最了解最真实的自己,成年后的生活,每一个外人所了解的自己都只是我们想让别人看到的自己。这两年,总会有朋友说学习碰到学校的同事,都是我是
- STM32之TB6612电机驱动模块
如愿小李单片机设计
stm32嵌入式硬件单片机
目录一、模块概述二、模块简介2.1模块特点2.2电气特性2.3模块接口说明2.4结构与工作原理2.5原理图设计2.6实际应用注意事项三、硬件设计3.1硬件组成3.2硬件连接四、软件设计4.1开发环境配置4.2关键代码实现4.2.1PWM初始化(PWM_Init)4.2.2GPIO初始化4.2.3电机控制函数4.2.4主函数五、功能实现与优化5.1基础功能实现5.2高级功能扩展5.3性能优化建议六、
- 我深深地沉醉于你的黑白魅力中!系列十三
可爱的布老虎
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明心zyl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作者海伦-凯勒,美国盲聋哑女作家,她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每个人都有累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每个人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候,那么我们想想她吧,我们的遭遇一定比她好。她在19个月的时候,因为高烧不退,而失去了视力和听力。我们无法体会她的痛苦,但我们可以想像一下眼前一片漆黑,耳边一片寂静,如果是我,那我
- 天才嫡小姐 第三百八十五章 人如其名
天彤小说
绝品炼药师更改书名为天才嫡小姐文/天彤“还是决定带他们出来呢?”月莲双眼发亮的问。“你能解除契约之印?”相耀陶挑着眉反问着。“小事一桩。”“那……如果是解除几百人的契约之印呢?”相耀陶挑着眉再度反问。月莲顿了顿道:“你想带那么多人出来?”“那契约之印,有让人实力增强的效果,不然,应该可以再更多。”相耀陶冷着脸道,此时的他,一点也没有之前那玩世不恭的样子,要是盛元化看见,一定会以为是认错人。“怪不得
- PHP,安卓,UI,java,linux视频教程合集
cocos2d-x小菜
javaUIPHPandroidlinux
╔-----------------------------------╗┆
- 各表中的列名必须唯一。在表 'dbo.XXX' 中多次指定了列名 'XXX'。
bozch
.net.net mvc
在.net mvc5中,在执行某一操作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各表中的列名必须唯一。在表 'dbo.XXX' 中多次指定了列名 'XXX'。
经查询当前的操作与错误内容无关,经过对错误信息的排查发现,事故出现在数据库迁移上。
回想过去: 在迁移之前已经对数据库进行了添加字段操作,再次进行迁移插入XXX字段的时候,就会提示如上错误。
&
- Java 对象大小的计算
e200702084
java
Java对象的大小
如何计算一个对象的大小呢?
- Mybatis Spring
171815164
mybatis
ApplicationContext ac = new ClassPathXmlApplicationContext("applicationContext.xml");
CustomerService userService = (CustomerService) ac.getBean("customerService");
Customer cust
- JVM 不稳定参数
g21121
jvm
-XX 参数被称为不稳定参数,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此类参数的设置很容易引起JVM 性能上的差异,使JVM 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当然这是在非合理设置的前提下,如果此类参数设置合理讲大大提高JVM 的性能及稳定性。 可以说“不稳定参数”
- 用户自动登录网站
永夜-极光
用户
1.目标:实现用户登录后,再次登录就自动登录,无需用户名和密码
2.思路:将用户的信息保存为cookie
每次用户访问网站,通过filter拦截所有请求,在filter中读取所有的cookie,如果找到了保存登录信息的cookie,那么在cookie中读取登录信息,然后直接
- centos7 安装后失去win7的引导记录
程序员是怎么炼成的
操作系统
1.使用root身份(必须)打开 /boot/grub2/grub.cfg 2.找到 ### BEGIN /etc/grub.d/30_os-prober ### 在后面添加 menuentry "Windows 7 (loader) (on /dev/sda1)" {
- Oracle 10g 官方中文安装帮助文档以及Oracle官方中文教程文档下载
aijuans
oracle
Oracle 10g 官方中文安装帮助文档下载:http://download.csdn.net/tag/Oracle%E4%B8%AD%E6%96%87API%EF%BC%8COracle%E4%B8%AD%E6%96%87%E6%96%87%E6%A1%A3%EF%BC%8Coracle%E5%AD%A6%E4%B9%A0%E6%96%87%E6%A1%A3 Oracle 10g 官方中文教程
- JavaEE开源快速开发平台G4Studio_V3.2发布了
無為子
AOPoraclemysqljavaeeG4Studio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今天我们最新的JavaEE开源快速开发平台G4Studio_V3.2版本已经正式发布。大家可以通过如下地址下载。
访问G4Studio网站
http://www.g4it.org
G4Studio_V3.2版本变更日志
功能新增
(1).新增了系统右下角滑出提示窗口功能。
(2).新增了文件资源的Zip压缩和解压缩
- Oracle常用的单行函数应用技巧总结
百合不是茶
日期函数转换函数(核心)数字函数通用函数(核心)字符函数
单行函数; 字符函数,数字函数,日期函数,转换函数(核心),通用函数(核心)
一:字符函数:
.UPPER(字符串) 将字符串转为大写
.LOWER (字符串) 将字符串转为小写
.INITCAP(字符串) 将首字母大写
.LENGTH (字符串) 字符串的长度
.REPLACE(字符串,'A','_') 将字符串字符A转换成_
- Mockito异常测试实例
bijian1013
java单元测试mockito
Mockito异常测试实例:
package com.bijian.study;
import static org.mockito.Mockito.mock;
import static org.mockito.Mockito.when;
import org.junit.Assert;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org.mockito.
- GA与量子恒道统计
Bill_chen
JavaScript浏览器百度Google防火墙
前一阵子,统计**网址时,Google Analytics(GA) 和量子恒道统计(也称量子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偏差,仔细找相关资料研究了下,总结如下:
为何GA和量子网站统计(量子统计前身为雅虎统计)结果不同?
首先:没有一种网站统计工具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出现该问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不同的统计分析系统的算法机制不同;(2)统计代码放置的位置和前后
- 【Linux命令三】Top命令
bit1129
linux命令
Linux的Top命令类似于Windows的任务管理器,可以查看当前系统的运行情况,包括CPU、内存的使用情况等。如下是一个Top命令的执行结果:
top - 21:22:04 up 1 day, 23:49, 1 user, load average: 1.10, 1.66, 1.99
Tasks: 202 total, 4 running, 198 sl
- spring四种依赖注入方式
白糖_
spring
平常的java开发中,程序员在某个类中需要依赖其它类的方法,则通常是new一个依赖类再调用类实例的方法,这种开发存在的问题是new的类实例不好统一管理,spring提出了依赖注入的思想,即依赖类不由程序员实例化,而是通过spring容器帮我们new指定实例并且将实例注入到需要该对象的类中。依赖注入的另一种说法是“控制反转”,通俗的理解是:平常我们new一个实例,这个实例的控制权是我
- angular.injector
boyitech
AngularJSAngularJS API
angular.injector
描述: 创建一个injector对象, 调用injector对象的方法可以获得angular的service, 或者用来做依赖注入. 使用方法: angular.injector(modules, [strictDi]) 参数详解: Param Type Details mod
- java-同步访问一个数组Integer[10],生产者不断地往数组放入整数1000,数组满时等待;消费者不断地将数组里面的数置零,数组空时等待
bylijinnan
Integer
public class PC {
/**
* 题目:生产者-消费者。
* 同步访问一个数组Integer[10],生产者不断地往数组放入整数1000,数组满时等待;消费者不断地将数组里面的数置零,数组空时等待。
*/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eger[] val=new Integer[10];
private static
- 使用Struts2.2.1配置
Chen.H
apachespringWebxmlstruts
Struts2.2.1 需要如下 jar包: commons-fileupload-1.2.1.jar commons-io-1.3.2.jar commons-logging-1.0.4.jar freemarker-2.3.16.jar javassist-3.7.ga.jar ognl-3.0.jar spring.jar
struts2-core-2.2.1.jar struts2-sp
- [职业与教育]青春之歌
comsci
教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之歌............但是我要说的却不是青春...
大家如果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给自己以后创业留一点点机会,仅仅凭学历和人脉关系,是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去的....
&nbs
- oracle连接(join)中使用using关键字
daizj
JOINoraclesqlusing
在oracle连接(join)中使用using关键字
34. View the Exhibit and exam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ORDERS and ORDER_ITEMS tables.
Evaluate the following SQL statement:
SELECT oi.order_id, product_id, order_date
FRO
- NIO示例
daysinsun
nio
NIO服务端代码:
public class NIOServer {
private Selector selector;
public void startServer(int port) throws IOException {
ServerSocketChannel serverChannel = ServerSocketChannel.open(
- C语言学习homework1
dcj3sjt126com
chomework
0、 课堂练习做完
1、使用sizeof计算出你所知道的所有的类型占用的空间。
int x;
sizeof(x);
sizeof(int);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x1;
char x2;
double x3;
float x4;
printf(&quo
- select in order by , mysql排序
dcj3sjt126com
mysql
If i select like this:
SELECT id FROM users WHERE id IN(3,4,8,1);
This by default will select users in this order
1,3,4,8,
I would like to select them in the same order that i put IN() values so:
- 页面校验-新建项目
fanxiaolong
页面校验
$(document).ready(
function() {
var flag = true;
$('#changeform').submit(function() {
var projectScValNull = true;
var s ="";
var parent_id = $("#parent_id").v
- Ehcache(02)——ehcache.xml简介
234390216
ehcacheehcache.xml简介
ehcache.xml简介
ehcache.xml文件是用来定义Ehcache的配置信息的,更准确的来说它是定义CacheManager的配置信息的。根据之前我们在《Ehcache简介》一文中对CacheManager的介绍我们知道一切Ehcache的应用都是从CacheManager开始的。在不指定配置信
- junit 4.11中三个新功能
jackyrong
java
junit 4.11中两个新增的功能,首先是注解中可以参数化,比如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assertEquals;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org.junit.runner.RunWith;
import org.junit.runn
- 国外程序员爱用苹果Mac电脑的10大理由
php教程分享
windowsPHPunixMicrosoftperl
Mac 在国外很受欢迎,尤其是在 设计/web开发/IT 人员圈子里。普通用户喜欢 Mac 可以理解,毕竟 Mac 设计美观,简单好用,没有病毒。那么为什么专业人士也对 Mac 情有独钟呢?从个人使用经验来看我想有下面几个原因:
1、Mac OS X 是基于 Unix 的
这一点太重要了,尤其是对开发人员,至少对于我来说很重要,这意味着Unix 下一堆好用的工具都可以随手捡到。如果你是个 wi
- 位运算、异或的实际应用
wenjinglian
位运算
一. 位操作基础,用一张表描述位操作符的应用规则并详细解释。
二. 常用位操作小技巧,有判断奇偶、交换两数、变换符号、求绝对值。
三. 位操作与空间压缩,针对筛素数进行空间压缩。
&n
- weblogic部署项目出现的一些问题(持续补充中……)
Everyday都不同
weblogic部署失败
好吧,weblogic的问题确实……
问题一:
org.springframework.beans.factory.BeanDefinitionStoreException: Failed to read candidate component class: URL [zip:E:/weblogic/user_projects/domains/base_domain/serve
- tomcat7性能调优(01)
toknowme
tomcat7
Tomcat优化: 1、最大连接数最大线程等设置
<Connector port="8082" protocol="HTTP/1.1"
useBodyEncodingForURI="t
- PO VO DAO DTO BO TO概念与区别
xp9802
javaDAO设计模式bean领域模型
O/R Mapping 是 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对象关系映射)的缩写。通俗点讲,就是将对象与关系数据库绑定,用对象来表示关系数据。在O/R Mapping的世界里,有两个基本的也是重要的东东需要了解,即VO,PO。
它们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一个VO可以只是PO的部分,也可以是多个PO构成,同样也可以等同于一个PO(指的是他们的属性)。这样,PO独立出来,数据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