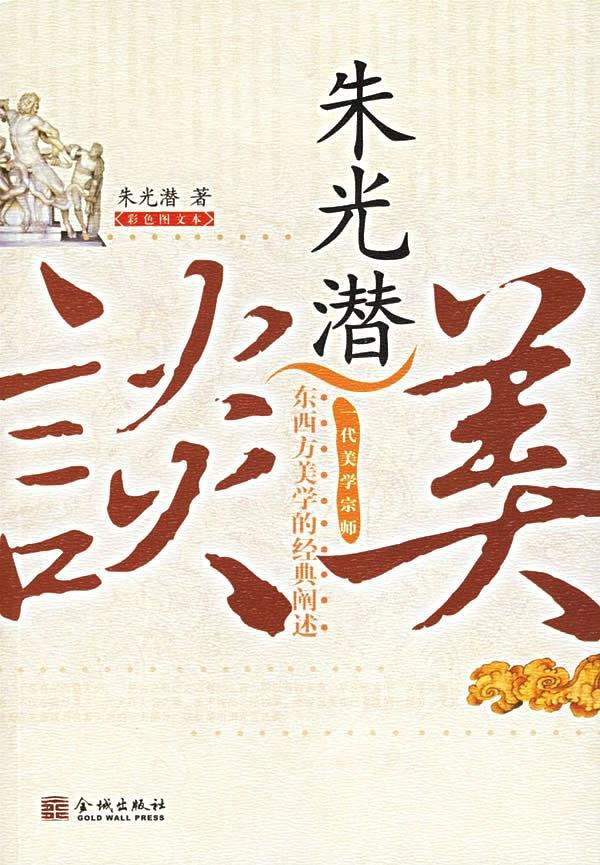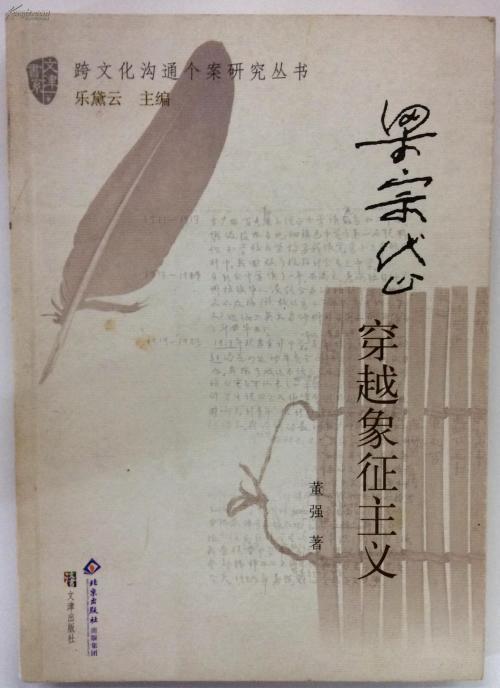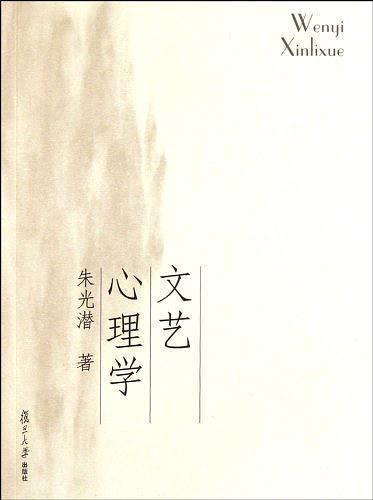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
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
前言
1932年朱光潜出版了《谈美》,1936年出版了《文艺心理学》,1943年出版了一直是其“心中主题”的《诗论》。这几本书奠定了朱光潜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谈美》被朱光潜称作《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 ,其中的观点在《文艺心理学》被进一步确认和扩充《诗论》的初稿在同一时期(1931年)也已写就。对 上述文本间的差异,朱光潜除了表示《文艺心理学》较之《谈美》增订了部分章节外,只主动谈论了其对克罗齐美学的态度的变化。但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会发现朱光潜未提及的一些极其重大的改变,譬如对象征观的局部修正:《谈美》认为寓言(allegory)属于象征(symbol), “最普通的托物是‘寓言’……‘拟人’和‘托物’都属于象 征” ;《文艺心理学》却放弃寓言,承认寓言与 象征的本质差异‘寓言’大半都不能算是纯粹的艺术,因为寓言之中概念没有完全溶解于意象,我们一方面见到意象,一方面也还见到概念” ,《诗论》更未提及寓言。那么,在上述承袭几乎相同的思想立场、具有内在互文性(in- tertextuality)的著作之间,为何竟出现如此微妙 却又鲜明的文本差异和思想分歧?朱光潜又为何要修正自己的象征观?《文艺心理学》乃至 《诗论》中其他部分的变动与扩充是否又与这种修正相关?揆诸中国现代美学史,本文认为这应与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和梁宗岱的象征论争有关。朱梁二人在欧洲留学时相识,关系密切,朱光潜早有将二人的私下辩论形诸笔墨的 提议,因此,这场论争不仅在公共领域正式开启了二人之间的思想论辩,成为日后的崇高之争、直觉与表现之争的滥觞,而且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围绕“象征”这一美学核心概念而展开的论争,影响甚大。事实上,二者对象征论的不同理解,源于其哲学基础的根本差异,亦即康德之先验唯心论与谢林之绝对唯心论 的对立。本文将互文性视角出发,通过文本细读,详细梳理象征论争,然后追溯至朱梁二人的哲学根基,对象征论争提出新解。
一、
谱系考察:
互文性视野下的象征论争
1926年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聚焦‘‘象征”,提出象征与兴的关联性,但未进行系统论述,仅归为一种抒情的表现手法和含蓄的美学风格。同时,他虽认为‘‘兴”奠基于不同对象的共通性,却未能阐明“共通”的内涵。周作人对“象征”的泛论无法令朱梁二人满意,朱光潜认为周氏是专注小品文创作的‘‘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 者” ,梁宗岱则暗讽周氏忽视诗歌中的宇宙意识和“普遍的永久的基本原理”,是‘‘谦避一切玄谈,以平淡为隽永的兴趣主义者”。但周作人确也为朱梁二人之后对“象征”的阐释作了铺垫:朱光潜重新思考了象征与兴的关系,并探究了在周作人处语焉不详的“比’“兴”之运作机 制;梁宗岱系统论证了 ‘‘象征即兴”,并着力挖掘被周作人忽视的形而上学维度。
具体而言,朱梁二人的象征论述具有高度互文性。朱光潜在《谈美》中对象征展开讨论,包含了日后成为论争焦点的两个美学命题:第1, ‘‘比’“兴”属于象征;第二,象征境界是‘‘即景生情,因情生景”。梁宗岱通过《象征主义》一文 进行了回应。虽然朱光潜之后未曾公开具名回应梁宗岱的批评,但在《文艺心理学》乃至《诗论》中,相关论述不仅悄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已然显露出他对梁宗岱的隐秘回应。因此,基于互文性,通过对二人观点的谱系学考察,象征论争中隐微曲折的实情或可得以澄清。
(一)在《谈美》中,朱光潜指出类似联想将性质类似者“嵌和在一起”,包含“比”和“兴”,还产生了 “拟人”与“托物”。拟人是将物变成人, “一切移情作用都起类似联想,都是‘拟人’的实例”,托物是将人变成物“最普通的托物是‘寓言’ ”。基于此,朱光潜提出其象征论的核心观点:
‘‘拟人”和‘‘托物”都属于象征。所谓‘‘象征”就是以甲为乙的符号。甲可以做乙的符号,大半起于类似联想。象征最大的用处就是以具体的事物来代替抽象的概念。……象征就是免除抽象和空泛的无二法门。 象征的定义可以说是:“寓理于象”。梅圣俞《续金针诗格》里有一段话很可以发挥这个定义:“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意含蓄,方入诗格。” 这意味着:第一,由于托物属于象征,因此寓言属于象征;由于象征起于类似联想,因此‘‘比” ‘‘兴”属于象征。第二,象征不是任意比附,象征物(symbol)与被象征物(the symbolized)具有类似特征。第三,象征是“寓理于象”,抽象的“理” 寓于具体的“象”中。但也存在几个问题:第一, 如何理解“寓理于象”?是具体意象“代替”抽象概念,还是具体意象“承载”抽象概念(文以载道),抑或概念与意象融合?第二,象征与寓言是什么关系?寓言能否归属于象征?第三,象征和 ‘‘比’ “兴”的关系如何?梁宗岱的批评正是直接针对这些问题:
首先,象征的特征是“融洽或无间”与‘‘含蓄或无限”,融洽是情与景、意与象融合,含蓄指意义的无穷,因此,象征‘‘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它所赋形的,蕴藏的, 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 邃,真实的灵境”。
其次,象征不是寓言,但优于寓言,二者泾渭分明。寓言‘‘把抽象的意义附加在形体上面,意自意,象自象” 象征融合概念与形象,‘(意义)完全濡浸和溶解在形体里面” ;寓言间接诉诸理解力,限制想象,象征直接作用于想象与感觉,激发想象。朱光潜混淆了象征与寓言。
最后“比”是寓言而非象征,因为它割裂了概念与形象,而且只是修辞学的局部事体。相反,象征与‘‘兴”相似“依微以拟义”,主观与客观、特殊与一般是同一关系。朱光潜虽将兴归入象征,但未能区分比与兴的本质差异。
在此可见,梁宗岱对象征特性的概括,与朱光潜此时的看法并不完全对立,但在实现这些特性的方法论(象征还是寓言、兴还是比)上,二者存在严重分歧,这正是梁宗岱所谓‘(朱光潜的象征观)骤看来很明了;其实并不尽然” 的原因所在。
在《文艺心理学》乃至《诗论》中,朱光潜隐秘地回应了梁宗岱的批评,既有明显的让步,又多借完善论述来维护个人立场。
第一,朱光潜补充解释了受梁宗岱质疑的 ‘‘寓理于象”指出它是‘‘概念应完全溶解在意象里,使意象虽是象征概念却不流露概念的痕迹”。但由于朱光潜认为‘‘寓理于象”可能被误解为用意象来表现概念,导向类型(type) 说,而且他更重视情感与意象的融合,因此《文艺心理学》提出“情见于词’,《诗论》更用“情趣” (feeling)替换“理”,用“寓情于象”取代“寓理于象”。这一观点就此确定为其美学的核心观 念,曰后被重申,如“文艺先须有要表现的情感, 这情感必融会于一种完整的具体意象(刘彦和所谓‘事’) 。
第二,在寓言与象征的关系上,一方面,朱光潜修改先前对寓言的论述,不再坚持寓言属于象征,反而表示寓言不同于象征。虽然他未像克罗齐那样将寓言完全排除于艺术之外,却承认寓言不是纯粹艺术,因为寓言中的概念与意象分立。 这等于接受了梁宗岱的批评。另一方面,梁宗岱认为寓言与象征的差异还在于寓言的基础是想象,而想象作为一种心理联想“最容易起幻觉或错觉”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对想象、幻想与联想之关系的澄清很可能是为了回应这一批评。从朱光潜的立场来看,梁宗岱混淆了 ‘‘想象”(imagination)与“幻想”(fancy),因为想象是“受全体生命支配的有一定方向和必然性的 联想”,是“融化的”(fused)联想,象征与被象征物融合,有助于产生美感,幻想却是主观的、偶然 的、“不融化的”(non-used)联想,阻碍美感。
第三,朱光潜拒绝梁宗岱的比兴二元论,指出比兴之分只在意象与情趣的侧重点不同(比重意象,兴重情趣),真正的契合是‘‘兴兼比”,而非梁宗岱的“兴”。他更从谱系学角度批判梁宗岱的本质主义,指出比兴二元论是后世所建构的产 物,归纳和分类缺乏谨严的逻辑“后来论诗者把它看得太重,争来辩去,殊无意味”。°半个世纪后的《谈美书简》更是通过强调“赋”中的形象 思维,否定了比兴二元论。但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那样,朱光潜将意象作为主观情感构造的产 物,实则否定了 ‘‘比”的客观基础,使‘‘兴兼比”等于主观移情,不得不面对梁宗岱的批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