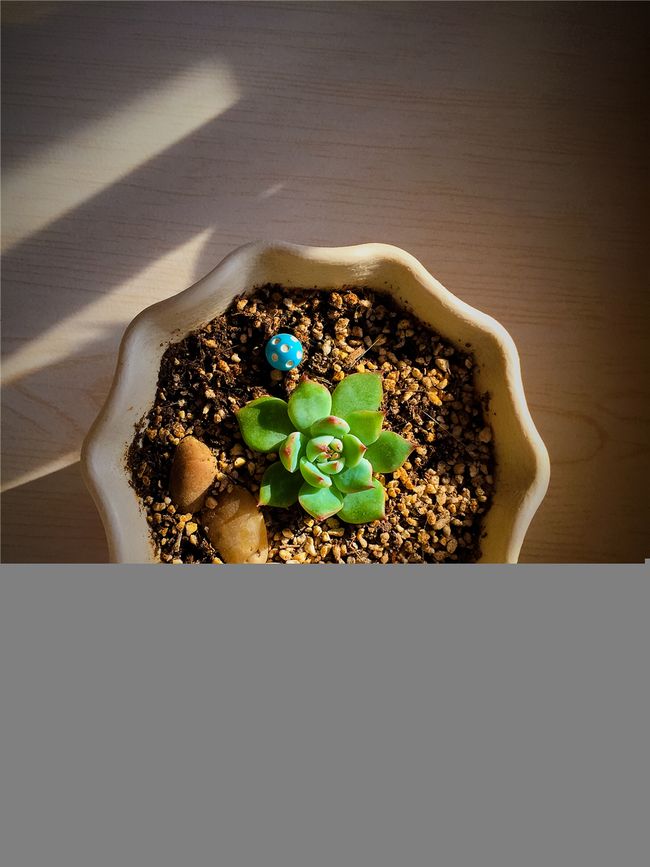熟悉的北京站前广场,雨后有些凄冷,但进站、候车的人不减。形形色色的人,如同花色各样的伞,看得见伞面,看不清人心。有小孩在哭泣,有老人在叹息,有情侣在吻别;有人颠沛流离,有人匆忙离去,有人安然落脚,只是谁也不知道会在这里飘荡多久。
或为生计,或为理想,或为感情,每个人都能给自己的到来或离开,找到一个可以自我安慰且心安理得的理由,即便这个理由曾让你热血沸腾,抑或是撕心裂肺。但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不分好坏,没有对错,也无须评判。如同许多隐藏在光环和粉饰背后的真实,不可理喻,也无法言说。
小C跟我说:“北京就像一个无底洞,很多人在这里努力奋斗一辈子,到头来依然只能抬头望天,让苦水和眼泪回流。”听完我心里一阵寒意,赶忙裹紧外套,这个时候耳机里传来老狼的歌声:“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
南方,此刻应该还很温润,从北方逃离的候鸟,是否已经找到了各自的栖息之地。
安妮宝贝在《眠空》里说:时间最终会带来解脱,重要或者不重要的事物,在最后纷纷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写《得未曾有》时,她改名为了“庆山”。
而我也在等待时间,等待事物褪掉光彩外衣,等待污浊而膨胀的现实显露。我知道,终有一天,从这里进站后,我不再买返程的票。从此抹掉记忆,就像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格式化掉6D里的SD卡。
那些我们曾经企图逃避和摆脱的枷锁,早已被抛掷在远行的路途里,未作停留,亦不能醒转。走过的这些光阴,繁华世态也好,寻常日子也罢,这座城市留给北漂人的念想,能有几何?不过,一场生活。
就像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克·克里南伯格所说:“人生之旅不再只是一条航线了,并且无所谓对错。这就是解放。”
小D问我:你从PR圈转入甲方,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说没有本质区别,方案稿件照写,加班照常,活动照做,出差还是没有。该维护媒体关系的照维护,该发红包表示谢意的照发,该找外围发稿的照找,该刷阅读评论数等KPI的照刷,该不爽的还是不爽。唯一的区别在于,你会深入到一个行业里边,接触到整个行业的运作流程和营销模式。成为行业专家的同时,你也会发现这个领域的诸多内幕和真相,有时可能会多到你连《明天会更好》都不敢唱给自己听。当然了,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印在名片上的身份标签和title不同于以往了。
小D接着问我,在PR圈的这些年,令你印象或感触最深的是哪件事?我带着问题,闭上双眼,开始拨弄自己心里的那根回忆之弦。时光倒转片刻之后,我慢慢睁开眼睛,告诉小D,初入行不久,有一件事让我触动颇深,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无奈和身不由己。
那时我有一个高帅富的领导,在一次宴请客户谈合作的餐桌上,大家都喝得有些微醺时,客户的老总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跟我领导说:“你要是多喝一杯,我就给你多加50万的预算。喝多少,加多少。”然后,我领导迷离着双眼,注视着对方,二话不说,一杯一杯的往肚子里灌52度的五粮液,直到趴到桌下,不省人事。结果,领导第二天住了院,项目合同的金额从百万级变成了千万级。作为一个新成立事业部的领导,他用这种方式让我知晓什么叫工作与事业,生存与生活,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互掐。之后,领导每周末都会去趟同仁堂抓药,用来调理他伤得千疮百孔的胃,至今我都还能闻到他办公桌上浓烈的中草药味。
在圈里这么些年,打交道和熟悉的人里边,有客户端的CEO、总经理、总监、项目经理;有媒体端的总编、主编、编辑、资深记者、记者;有供应商端的摄影摄像、速记、活动搭建、导演、编剧、配音师、视频剪辑师、设计师、主持人、模特。与他们沟通交流的过程中,纵然增长了不少见识,但已经很难遇到一个可以与其交心,把其变成朋友的像小川一样的人。
正如大冰在《乖,摸摸头》里所说: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大家点头微笑,结伴一程。缘深缘浅,缘聚缘散,该分手时分手,该重逢时重逢。惜缘即可,不必攀缘,同路人而已。能不远不近地彼此陪伴着,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七年了,在这个说不清道不明感情的城市,除了加班,或从别的城市返回,或拍夜景,我极少会在夜晚出来领略它的繁华,美丽,喧嚣,熙攘,告别。这是北京刚下过雪后的第二个夜晚,我来到奥林匹克公园,单纯地看看夜色中的鸟巢和水立方。
这夜,很多人来到这里,或被拍,或跟拍,或自拍,留下影像,也是留下某一段回忆。在多年之后,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同样微凉清冷的夜,翻着旧照,或旧文,偶尔会想起有过的曾经,足以。
在南方过了20个冬天的小E说,“北京今年初冬的第一场雪来得太早了一些,小区里还没开始供暖,而且天空一直不见太阳,屋里处处寒气逼人,晚上冻得抱着男室友一起睡觉都不觉得尴尬了。”
我诡谲的看着小E,笑道:你终于得偿所愿。然后,我眼前冲出一群小E养的草泥马,蜂拥而至,怒目圆睁的盯着我看,接着飞驰而过。
从观赏红叶到飘洒于天地间的飞雪,相隔的时间着实短暂,但我却感觉极其漫长,漫长到我彻底忘了08年初来北京的第一场雪是什么时候下的。这个片段如同选择性失忆一般,连我梦里都没再出现过那个场景。
也许,在这个城市的所见所闻,就如同轮回里前生的事,被隔离在时光的背后,看得见,却摸不着,更无从与彼此对话。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北漂也好,留在故乡也罢,生命里来来往往的那些人,不过都是过客,何曾有过归人。
早上一场小雨,顺势打湿了这个冬日里接踵而至的雾霾,使得人心愈发阴冷潮湿。30载春秋,游离多个城市,出发,跋涉,抵达,回归,窥见众生相,阅尽路途风景,终究也只是相忘于江湖。
这么些年,我手持单反,走街串巷,不过岁月浪子,又岂知明日流落何处天涯。就如庆山之言:“隐秘而纯净的悲伤使生命成为盛器。”此句,独喜。
写上一篇小文时,时间是九月的最后一天,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秋的收获和喜悦的味道。如今来到11月,气温骤降,寒风凛冽,人心僵硬,我的多肉也停止了生长,而泰格和牛顿(家里的两猫)只迷恋床的温暖,不再与我嬉戏。庆山在她还是安妮宝贝时,在《清醒纪》里说:“写作,这将会是世间始终最为孤独的一项工作。就像一个人站在黑暗的舞台上,给自己设置的一束明亮光线。他由此看到自己,亦被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创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投影的不仅仅是自我,也许还有他企望中的世界,即使只是幻觉。”周末又接到新的图书公司的出书邀约,我在积累、沉淀和等待自己的那道光线。
去往798艺术区的途中,同属南方人的小C、小D、小E异口同声的跟我说:这个冬天的北京,真的好冷,没有阳光,满大街还笼罩着雾霾。看了你的这篇文,来自南方的我们感觉更冷了,就像小时候见到的寒风中的寒号鸟,冻得嗷嗷叫唤。
这个时候,一个定居南方的作家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我不会告诉你们,深圳此刻22度,穿着短袖的我,毫无压力,毫无冷意。”
听完我们瞬间挂断电话,然后马頔的声音从街边的咖啡店里传来: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摄影/韦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