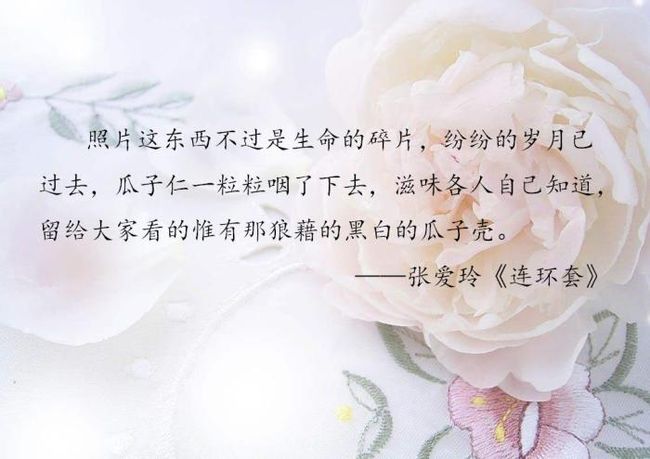张爱玲的短篇《连环套》,读到霓喜张嘴在街上骂骂咧咧撒泼的时候,就会想起《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曹七巧一辈子孤零零,年轻时嫁了个瘫痪在床没人气的丈夫,守了一辈子的活寡。
她把所有的未活过的青春旺盛精力,全部都用到操控摆弄她的儿女身上去。
霓喜是曹七巧和金莲的加强版。
她脾气执拗,一不顺心就和她身边的男人吵闹,愤然离家,再寻找下一张饭票。
最后一辈子都周旋在不同的男人身边,她给三个男人生了5个儿女,最终孤独终老,没能找到一张长期饭票。
读完她的故事,心里夹杂着五味杂陈,强烈感受到一种从心底涌上来的悲情色彩。
如果她的逞强使气不是用在和男人斗气上面,那她至少还能和第一任丈夫,那个印度男人雅赫雅平凡一生。
偏生她本性并不安分,又有极其强烈的自尊心。
她被牙婆子卖给开绸缎铺的雅赫雅时,还未成年,才14岁。
从不同年龄段的心理发展轨迹来说,那个年龄的她开始进入青春期,对于确立自我身份有着更为强烈的渴望。
我在想,她之所以这么折腾,大概是那个年龄段的心理发育并不健全的缘故。
许是因为她极其尴尬的身份,在绸缎店里上不上下不下,及至她后来嫁给了开药材店的窦尧芳,她这一辈子都被这种尴尬的身份所困扰与笼罩。
既称不上老板娘,又和雅赫雅同床共枕,生了两个孩子,比底下的佣人身份地位更高些。
只不过她所选择的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稍显极端,在雅赫雅面前勾搭别的男子,以此显示自己的交际手腕,让对方吃醋,继而雅赫雅对她更上心,让她做一个有身份的太太。
但她忽略了从别人的视角看待自我,雅赫雅当初将她买进门,无非是因为家里需要这么个女人,抱着省钱省事的想法就干脆买了一个,对于霓喜的身份问题,他并没有加以考虑。
初来的时候形容憔悴,个子也瘦小,渐渐地雅赫雅的绸缎铺子生意兴旺,她出落得美丽有风韵,绸缎铺里里外外的男子都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雅赫雅看她人才出众,又擅交际,有过想把她扶为正头妻的想法,但奈何她脾气暴躁,又怕一旦把她扶正,她越发得意上头上脸,就干脆把这层心思藏着,没有表露出来。
唯一的维持自尊心的方法便是随时随地的调情,在情色圈子里她是出了名的强者,一出了那个范围,她便是人家脚底下的泥。
用比较现代的说法来概括,她就属于“全封闭自体”,即她的心理发育停留在儿童阶段,她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看不到别人的存在。
就像张爱玲给这部小说所取的名字《连环套》一样,她就这样陷在对于自己的自恋里,凄凉了一生。
雅赫雅本来就知道她惯于把他身边的人招得七颠八倒,但碍于两人共同生活了十几年,而且也有两个孩子,他索性就睁一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
霓喜见他迟迟不把她扶正,按耐不住,索性用话挑明。霓喜怨怼起人来时,惯喜欢叉着腰,手指着对方鼻子,这种难看的骂人相活像乡村野妇。
不过她虽然被卖给了印度绸布商人雅赫雅,不缺吃,不少穿,近来也出落得异常有姿色,但她骨子里仍然是没有受过良好教养的乡下妇人。
她倒是让我想起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来,骂起武大来的架势活像要把对方生吞活剥了。
当她被大户施舍给武大时,她看武大那猥琐的形容,心里着实觉得憎恶。
“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奴端的哪世里悔气,却嫁了他?”
被武松呛白了两句时,就把这股子闷气找了个借口一股脑往武大身上撒。
“你这个混沌东西,有甚言语在别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也走得马,不是那腲脓血搠不出来的鳖。”
金莲恨死武大了,最大的不满足就是武大在容貌和财力上配不上她。
她闲来无事时,总喜欢坐在楼上嗑瓜子,然后把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往栏杆外放,引得一众浮浪子弟争相追捧。
金瓶梅中评价这类的女性: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几分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
换现代的话来说,也就是美女都想嫁给高富帅,如果没有实现这种夙愿,心中苦闷,就好似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般的颓丧气垒。
而霓喜对于雅赫雅倒没有不满,他白手起家,是个精明又热情的年轻人。
她贪恋着他的年轻美貌,也贪恋着他这片偶尔可以结识上流人物的小小地盘。
内心的不满足也只有雅赫雅没有给予她一个正当的身份罢。
金莲和霓喜她们对于伴侣不满足的地方,一个是性关系的不和谐,另一个是身份地位的不对等。
总体来说,她们都是心理发展有所缺陷的人。
这种“全封闭自体”的女性,如果她们的心理发育到客体水平,即能够意识到自己和对方是平等存在的人,既尊重自己的感受,也会关心对方的喜怒哀乐,在关系中实现良性互动,能够彼此妥协,却不背负纠缠,那她们的结局会幸福得多。
可惜,她们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缘故,其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奴性文化的束缚,让她们会纠结和在意更多关系之外的东西,譬如金钱,身份,地位。
其实,如果金莲和霓喜在现代社会,稍微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不把对于生活的所有寄托放到男人身上,那她们倒是能凭借内在的伶俐和嘴皮子成为很好的职业女性,一路从小白坐上去,成为职场白骨精。
生于男尊女卑的过去,浸淫在传统奴性的文化里,倒是枉费了一副好皮囊和一张善辩的利嘴。
在她们狭窄的视野里,所能倚仗的除了男人之外还是男人。
而且,霓喜和雅赫雅的对话总不在一个频道上。
雅赫雅把霓喜买来,只是单纯把她当佣人使唤和看待。他是精明的印度商人,如果这样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既能帮他洒扫庭院,又能帮他传宗接代,这又何乐不为呢?
而霓喜身上也有着年轻女孩子的较劲与执拗,偏生身边的男子都被她迷倒,雅赫雅却好似忽视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价值,她美貌又善应酬,作他的臂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可唯独雅赫雅不曾对她刮目相看,当着人不给她留面子,呼来喝去地,让她心里很是气愤和不平衡。
霓喜像一个没有耐性的小孩,在雅赫雅身上娇柔不了几分钟,就暴露出没有被满足的暴躁本性。
到老年的她,在给别人讲述她曾经在乡下的那一段历史时,最喜欢拿来打趣的就是她14岁那年被养母卖给印度人的那件往事。
她先和人家说卖了120元,随后又觉得太便宜了,自抬身价,改口说是三百五十元,又说是三百元。
她不大喜欢提起她幼年的遭际,篡改自己的过往,一会把它叙述的异常恐怖,说她曾经被广东乡下的养母如何虐待。
一会又把它说得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说她是珠江的蛋家妹,和雅赫雅的相逢充满水上情调。
金莲不像她自贬身价,虽然起初她是大户买回去学琵琶的小丫头,落后又被迫跟着武大,但她从来都是自视甚高的女人。
后来勾搭上西门庆,也是她有心存着进豪门的梦。
虽然没有取代吴月娘的当家主母的位置,但好歹也在西门府挣得了一个五姨娘的正当身份。
而霓喜虽然离开雅赫雅之后,她被药材铺的老头收容,后又跟了英国工程师汤姆生,但最终,她还是没能成为那些男人的“妻”,终究是个姘头。
这和她的暴躁脾气,要强的心性,以及内在的自卑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
曾经的她自己首先就把自己看扁了,喜欢把自己心里的阴暗想法强加给对方。
一生气,就不受控制地,先自贬身价地一番说叨:“你的意思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女人,你将来还要另娶女人,我说在里头,谅你也听不进,旋的不圆砍的圆,你明媒正娶,花烛夫妻,未见的一定胜过我。”
“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会子吃不了三天饱饭,就惯得她忘了本了,没上没下的!—你就忘不了我出身,你就忘不了我是你买的!”
这样两个人之间没有一点同情和了解,虽然他们在一起同床共枕,也有了孩子。
霓喜虽然总是施展她的女性魅力,但碍于当下还算顺风顺水的生活,她也是藏着掖着,只是调笑,并不上头。
米耳送给她的那枚戒指像充满魔力和妖术,“有棱的红宝石像个红指甲,在她的心窝上一松一帖,像个红指甲,抓得人心痒痒。”
她自认为还是个规矩的女人,和米耳调情的那一次。她体会了规矩女人偶尔放肆一下的那种隐秘的好处,那种禁忌的吸引是坏女人体会不到的。
回到店铺里,她在湛蓝的天空下留下了眼泪,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不甘心的念头:凭什么,她要把最热闹的这几年糟蹋在这片店铺里?一个女人,就算活到80岁,也只有这几年是真正活着的。
最终,惯于作妖的霓喜在撞见雅赫雅的相好,于寡妇来店铺里买绸缎的那一次,她索性丢开了,大闹了一场。
她把心里积攒的所有怒气通通发泄到于寡妇身上,于寡妇被她用绸缎布料狠命砸。
雅赫雅揪住她的衣领,啪啪几个耳光甩下去,毫不留情。此时,店铺里一片狼籍。
霓喜本打算拿孩子作要挟雅赫雅破镜重圆的筹码,最终,她的算盘落空了,雅赫雅给了她一点子补偿,就逼迫她离开了。
她和雅赫雅的故事是她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从少不更事到花季的年龄。
当离开雅赫雅的时候,她带着两个孩子,流落到寺庙里,无依无靠,又重新回到了缺衣少穿的凄苦日子,况且身边还带着两个拖油瓶。
如今自由身的她,豁开了这个口子,她就再不怕了。
挣扎着,一边期盼着雅赫雅来寻她,一边又期盼着会遇到一个上流人救她出水火。
她的进阶之路和金莲不同,她纯粹是运气,而金莲是心机和筹谋。
金莲和西门庆在王婆家约会过后,西门庆公务冗杂转身就把她忘记了。
虽然武大已经被他两谋害,她赤条条一个人行动自由。但想要成功进入高门府邸的西门府,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她日日在门首盼着,时不时央王婆拎点东西去西门庆家瞧瞧。
最后,她再次见到了西门庆,床帏里面,她就把西门庆吃住了。
霓喜等来了药材铺的老板窦尧芳,这个年届50的老男人。
搬到了药材铺之后,她的天地陡然一新,屋宇敞亮,上下人都认她这个半路杀出来的老板娘。
呼奴唤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她每日只要把自己打扮得美丽娇俏就行。
终于实现了在绸缎铺里梦寐以求的事,此时,她的心又开始不满足起来。
窦尧芳年纪太大,她暗地里和底下的伙计崔玉铭打得火热。
银钱在手,物质上很是宽裕,她的心却很狭窄。她吝啬给崔玉铭过多的钱财,又防备着窦尧芳的儿子将来掌管了家业,没有她的立锥之地。
变着法子,夺取药材铺的掌家大权。时不时骂骂咧咧底下的下人做事不仔细,糟蹋了她的银钱。
这样的处处与人作对的姿态俨然中年的曹七巧,她怕儿子长白在外面学坏,就哄骗儿子抽鸦片,以此绑住儿子在身边。
为了防止女儿被人骗,就不让女儿读书,也不让女儿社交,最后好不容易结识的一个有为青年,她硬生生对着人家说自己的女儿染上烟瘾很多年,把人吓跑。
旧社会的女人真的太可怕,心理的畸形除了她们本身吃过太多苦的缘故,还有内在产生的极大不安全感。
没有父母疼惜,没有丈夫疼惜,底下的下人鄙夷,身边的小姐妹总是她好的时候就巴结,她不好的时候就赶紧避之不及。
所以,当霓喜一旦获取到权利的时候,她对于外界是异常警惕的。
监视窦尧芳家里人和他的通信,责骂下人作践了她的东西,用美色和钱财笼络住她身边唯一向着她的人—崔玉铭。
就像老妈子背地里骂她的:“八辈子没用过佣人,也没见过这样的施排,狂得通没个褶儿!”
权利来临时,她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握得住,因为她的心胸狭窄得只能够容得下她自己。
后来,窦尧芳病死,她真的如下人所说的结局:“有一天恶贯满盈,大家动了公愤,也由不得老的做主了,少不得一条棒撵得她离门离户的!” 最后,她带着五个拖油瓶,灰溜溜离开了窦家的药材铺。
31岁的她脸部变胖了点,身上开始有了赘肉,但她还是竭力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为她寻觅下一段良缘做充分准备。
英国籍的单身汉汤姆生遇到她的时候,对方还没说话,只是多回头看了她两眼,她那溜溜的眼睛就懂了他要什么。
她以肚子里怀了他的孩子为借口,软磨硬泡,终于搬进了一间敞亮的房子。
但他作为一个体面的工程师,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这时候的她,反倒不再在意身份问题,只要每天可以坐在竹轿上,把一双脚搁得高高的,让她招摇过市,她就很满足。
畅意的日子一个接连着一个,融化在一起像五颜六色的水果糖。
她开始追忆起过往的恩怨,她要一桩桩一件件地,来个恩怨分明。
去到雅赫雅的绸缎铺子里买衣料,在他店铺里大闹一通。
在安定的生活里过了5,6年,她体重增加,目光变得呆滞,眼里闪烁出的一点子光辉,还是在她和故人叙旧的时候。
她顶喜欢吵架,只有吵架能够让她还感受到她年轻时的活力。
她邀请过往与她交恶的尼姑,开着小汽车在她们面前显摆。
这一切在汤姆生在英国结婚,并且带着他的太太来中国的时候,就开始走向结束了。
纵然霓喜吵吵闹闹,可她最终也还是无法逆转汤姆生的决定。
她轰轰烈烈的青春,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她的这几个孩子可以证明她过往的繁华。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关系模式,也就是“剧情”。
一辈子陷在“内在剧情”里面的女人,就像给心锁上了一个连环套,真的太过可悲和可怜。
我想,假如她生活现代,有一个比苏明玉还悲惨的原生家庭,但她至少还可以选择一个像石天冬那样极具包容心的伴侣,他是医治她伤口的一帖药。
她依然可以通过后半生,来领悟到生命的真相不是囿于外界的一切束缚,眼光,钱财,地位,攀比。
她没有必要因为雅赫雅的不在意,就硬要用自身美色的魅力来向他证明她是能够做他臂膀的。
她也没有必要牢牢把权利握在自己手里,让窦尧芳全家上下喘不上气。
她更没有必要为了在人前显摆,一味肆意挥霍和享受。
她应该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她的兴趣,奉献,事业,爱情。
大家都希望自己童年幸福,是心理健康的幸运儿。
可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童年都不怎么幸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创伤,各种内在剧情会使我们偏离真相,看不见真实自己的欲求。
但是没关系,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去认知自己的内在剧情,去觉察内在剧情不等于真实世界。
渴望看见,了解真实的自己,那么童年创伤再大,也一样能够过好日子,创造属于自己的幸运。
作者简介:糖鑫鑫,既写感性,又写理性思考。爱折腾,有随时拿起背包远行的勇气,人生重在体验。本科心理学,立志心理咨询师,最后在电影里找到了自己,追梦的第一步就是进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未来编剧。糖鑫鑫(sushanxin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