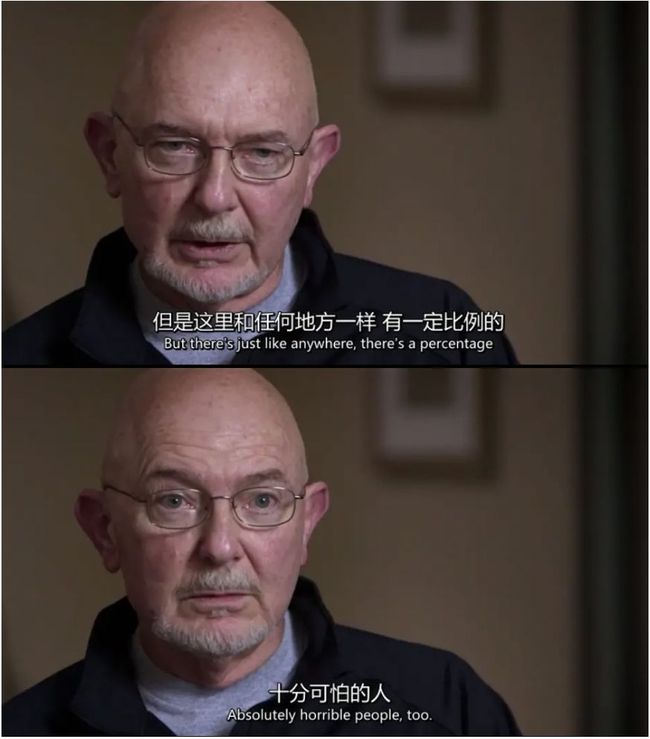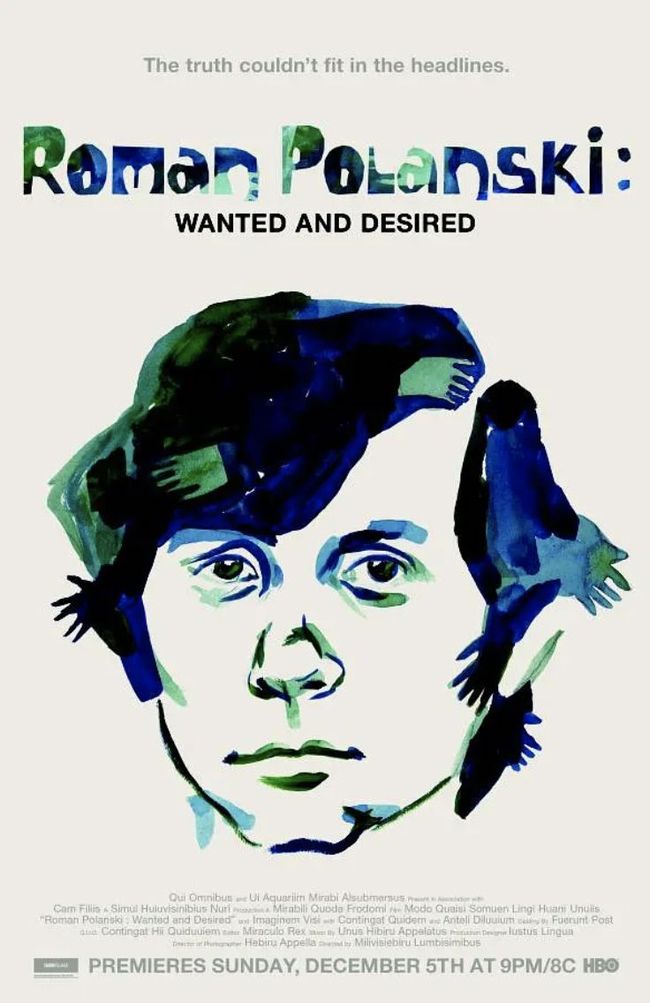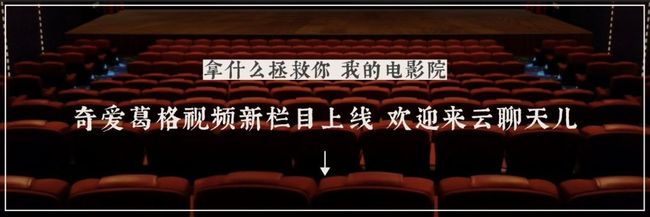电影恶魔终伏法,受害的何止女性!
从1966年到2016年,在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奖感言中,哈维·韦恩斯坦在三十四篇演讲稿中获得了赞颂或感谢,“上帝”得到的数字与此相当。他们两人仅次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四十三次。
2020年3月11日,曼哈顿刑事法官詹姆斯·伯克宣布,哈维·韦恩斯坦将被判处二十三年监禁,罪名为一级犯罪性行为与三级强奸。
从上述的几组数字中,已经可以看出很多信息了。这样的罪名,一般并不会获得如此体量的刑罚。伯克法官的重判,正是因为韦恩斯坦在数十年的从影生涯中,已经犯下了未被公诉的累累罪行。
与此同时,许多以“一码归一码”开头的论调,也会肯定韦恩斯坦一手打造的电影帝国。在近五十年的世界电影史上,他当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独立电影与亚洲电影的贡献,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哈维·韦恩斯坦的从影史与性侵史,无疑是相互交缠的。一篇《好莱坞报道者》的文章指出,韦恩斯坦在制作他的电影界首秀《炼狱》时,就已经性侵了当时的实习生瓦乔维克。她所描述的经历,与此后无数的受害者都如出一辙。
如今的瓦乔维克
韦恩斯坦置身的权力网络,让他得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电影眼界,也让他能够疯狂地倾泻自己的欲望。他推出的杰作越来越多,被他抛入深渊的受害者也日益增加。曾在好莱坞恣意翱翔的韦恩斯坦,同时成为了教父与魔鬼。
正因如此,韦恩斯坦的获刑,不但回应着那些女性受害者的控诉,也让我们得以去重新反思好莱坞的真实面目。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谈谈这二十三年刑期背后的复杂意义吧。
这场判决本身最直观的意义,恰恰是法律层面的。韦恩斯坦案的判决过程本身,就证明了性侵问题在电影界的复杂性。
首先,韦恩斯坦没有被定罪为最严重的“一级强奸”,他的罪名是稍轻的“三级强奸”。根据纽约的法律,一级强奸与三级强奸最重要的区别,除了年龄之外(三级为低于17岁,一级为低于11岁或13岁),就在于“暴力强迫”。
暴力强迫是一级强奸的代表特征,而三级强奸的同类特征则是“未经允许”。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强迫都应该算作是强奸。利用“电影大亨”的威压执行的强奸,与通过暴力达成的强迫,在强奸层面上本不该有轻重之分。
此外,本案的检察官琼·伊卢齐·奥邦和梅根·汉斯选择了两位身份特别的证人。事实上,这两位证人在遭遇韦恩斯坦的性侵之后,还与韦恩斯坦保持着联系,甚至还发生了性关系。
如果根据此前的案例,这样的选择十分冒险,因为她们大概率会被定义为“自愿”。
要知道,电影业内部的性侵,并不能仅仅依靠行为来判定。正如此前提到的“威压”那样,对于初出茅庐的电影新人来说,大亨的第一次成功性侵,很可能伴随着与胁迫、诱惑共存的长期性关系。对于这两位证人来说,这种长期关系很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检察官琼·伊卢齐·奥邦
无论是一级强奸的定义无法涵盖到的东西,还是这两位证人的身份,都让我们意识到电影业性侵的复杂性。因为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所以在具体的强奸行为之外,其实还存在着精神层面的压迫、引诱与攫取。
这种无法用具体行为涵盖的罪行,也存在于其他类型的犯罪之中。例如,在家暴案件中,许多家暴男的虐待是周期性的。他们在每次具体的虐待行为之后,常常会哭求妻子的原谅。
如果妻子在家暴的当时进行反抗、杀死丈夫,那么这大概率会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但是,女性往往不具有反抗愤怒男性的力量,所以她们常常只有趁男性休息或睡着时,狠心杀之、然后逃走。
在根据法条定义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算是正当防卫。但是,法官可以通过延伸规则的方式,利用“受虐妇女综合征”等缘由,给予无罪的判罚。在重视判例的英美法系,这就可以为此后的家暴案提供重要的武器。
同样地,在电影行业里,女性受到的性侵犯,也存在于复杂的权力网络与长期关系之中。除了性侵案本身举证困难的问题之外,这种行业内部基于权力关系的压迫,也理应受到与“受虐妇女综合征”类似的关注。
所以,检察官对于那两位证人的选择,其实算是一场赌博。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最终的胜利。法官这次的从重刑罚,无疑是#MeToo运动的重大收获,这对此后电影业的性侵案判罚,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
那么,电影大亨们是如何利用这套权力网络,实施一系列性侵行为的呢?追根究底,为何性侵在电影业能够如此猖獗?
要谈论这一点,就要先意识到韦恩斯坦这样的好莱坞上位者共享的东西:财富、一系列被称为“电影艺术”的作品,还有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宣传机器与公关机器。
事实上,可能没有人比电影人更会建构公众形象了。影像无疑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形式,在如今这个“正确”趋势兴盛的年代,很容易就能成为浪潮内部的代言人。毕竟,韦恩斯坦也曾推出过《狩猎场》,这是一部聚焦于美国高校性侵事件的影片。
《狩猎场》
此外,在《纽约时报》当时曝出首批性骚扰指控后,韦恩斯坦发表声明表示,他将在南加州大学为女导演设立一个价值五百万美元的奖学金基金会。结识库克、萨伦德斯等众多大佬的韦恩斯坦,可以轻而易举地摆平那些小范围事件——当然,#MeToo运动的声浪,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了。
在对付作为个体的受害者时,韦恩斯坦既有蜜糖又有皮鞭。他可以凭借自己在业内的地位,为电影业的新人们提供致命的诱惑;他也可以凭借麾下的人事部门与法律部门,扫除任何后顾之忧。
通过上述的一切,电影大亨们得以从召唤更多的信徒,也得以压迫入门的下位者。
正如评论家艾丽莎·威尔金森指出的那样,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在电影业中建构了一种近乎宗教的社群。与电影业一样,教会这类宗教场所内部的性侵案件,也是臭名昭著。
在教会的神父身旁,围绕着宗教性的灵晕,这既让受害者畏惧,也让他们感到迷乱。而对于电影业新人来说,韦恩斯坦这样的大佬,就是“电影艺术”或是“获奖影片”的代言人。那艺术的迷雾、独立电影推手的光环,令人震颤而眩晕。
是的,正像全文开头中的那则统计一样,对于他们来说,韦恩斯坦与“上帝”齐名。
结合这一点,我们难免会想起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波兰斯基事件。虽然罗曼·波兰斯基已然被定罪,他自己也已承认罪行,但在许多关于波兰斯基的文本中,他仍然被塑造成一个受害者。
区分作品与作者,可以说是基本的前提。但是,波兰斯基那名震影史的作品序列,与他那传奇般的电影作者身份,也让许多影迷混淆了现实中的罪行和电影中的“罪恶”主题。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宗教式的权力结构,仍旧是压迫性的。在施暴者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着阶序上的关系。
事实上,在电影业内部,绝大多数的压迫与侵犯,并不会表现为性。韦恩斯坦对于男性雇员的压榨与利用,或是他迫使他们服务于自身目的的方式,与他性侵害女性受害者的模式如出一辙。
一位前雇员在接受访谈时指出,“在韦恩斯坦的办公室,你会为一些最为奇怪的事情感到自豪——比如他一整天都没对你大喊大叫,或者说他没有公开地凌辱某些人(包括服务员、同事、导演或司机)”。
在韦恩斯坦的身旁,总会有那么一些又高又帅的男性助手。当然,韦恩斯坦对他们可能怀着矛盾的感情,或许有嫉妒、有憎恨,也有将他们掌控在手中的满足感。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了另一种程度的欺凌。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下位者的性别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正像在许多声名狼藉的教会性侵案中,神父同时将魔爪伸向了男童与女童。
韦恩斯坦案所披露的事实,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性侵情境与好莱坞的工作环境,其实是大体同构的。
意识到这样的权力结构之后,再来思考韦恩斯坦的影史贡献,无疑会得出颇为不同的结果。事实上,上文提到的宗教性与压迫性,也内在于韦恩斯坦的电影帝国之中。
韦恩斯坦创立的米拉麦克斯公司,缔造了独立电影的神话。据统计,他作为制片人和执行制片人的作品,在奥斯卡获得了二十二次提名,其中有六次获得了奖项。《性、谎言、录像带》和《低俗小说》都在当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时至今日,这两部影片依然是许多影迷的最爱。
彼得·毕斯肯德的《低俗电影》中记述道,韦恩斯坦为了减少《低俗小说》的开支,游说演员们减少片酬,毕竟“谁都知道独立电影是爱的奉献”。这难道不是一种宗教社群内部的“传教”策略吗?
在这本书中,还详细描述了他的态度:“我在从事上帝的工作,明星们应该多加节制,为提成而工作,并且共同分担风险,拿风险回报,就像他们替伍迪·艾伦和罗伯特·阿尔特曼做的那样。”
当然,许多曾与韦恩斯坦共事的人都表示,他是真的非常热爱电影,他也确实利用这种热爱,从某些方面推动了电影史的进程。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他或许错将“从事上帝的工作”,与“成为上帝”混淆了。
除了对于美国独立电影的贡献之外,他对于外国电影、尤其是亚洲电影的关注,也推动了世界电影文化的流通。
他曾在九十年代购买了李连杰、周润发、成龙等人的作品。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宫崎骏的《幽灵公主》在美国的上映,也与他息息相关。米拉麦克斯甚至还发行过“神奇宝贝”的剧场版电影。
不过,他对于电影的热爱,并不妨碍根据他自己的喜好“修改”这些作品。韦恩斯坦对于艺术电影的剪辑与配音,已经到了“臭名昭著”的程度。
他会在压迫性的权力结构中,随意处置自己的雇员,他也会为了特定的目的(例如顺应美国市场),“调度”他买到的电影。
譬如,他就重新剪辑了获得金棕榈的《霸王别姬》。时任戛纳评审团主席的路易·马勒非常愤怒:“这部电影在戛纳备受赞誉,但我在这个国家看到的完全不是同一部作品,它要比戛纳的版本短了二十分钟——不过让人感觉更长了,因为它毫无意义。”
此外,韦恩斯坦在获得《幽灵公主》的美国发行权时,导演宫崎骏还给他寄了一把武士刀,上面写着“不要剪”。
宫崎骏后来表示:“其实那是我的制片人干的。不过我也确实去纽约见了他,见了这个叫哈维·韦恩斯坦的男人,我受到了大量咄咄逼人的信息轰炸,他给我抛出了一堆剪辑上的需求。但是我最终打败了他。”
外在于韦恩斯坦权力结构的宫崎骏,拥有“打败”他的资本与风骨。但那些彷徨无措的局内人士,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影人们受到的侵犯,充其量只是作品层面的;但性侵受害者们遭受的伤害,或许将永远铭刻在记忆之中。
由此可见,哈维·韦恩斯坦的二十三年刑期,具有层次非常丰富的意义。它体现了电影界性侵在法律层面的复杂性,曝露了好莱坞的“性侵土壤”,甚至还证实了一系列宗教性、压迫性活动与电影业系统的同构。
在一场街头暴力性侵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辨识出施暴者与受害者。但是,当这一切发生在好莱坞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
原先赤裸裸的权力系统,被蒙上了“电影艺术”的光晕。或许有人要说,受害者似乎可以换取某种意义上的“回报”,但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场交易并不是受害者的本意。拒绝韦恩斯坦这些电影大亨的请求,无疑会招致残酷的报复。
这当然不仅仅关乎于性。韦恩斯坦想要的也可以是俯首帖耳,或是更努力的工作,甚至是帮他隐瞒性侵的罪行。而他采取的压迫形式,当然还有语言暴力或是高压的运营模式。当然,他会给你“回报”,绝大多数情况下,你都必须得要。
哈维·韦恩斯坦曾说,“我一生只为一个名叫‘电影’的大师服务。我爱电影。”
当然,人人都爱电影,才华横溢之人也不在少数。但韦恩斯坦“爱电影”、为电影服务的代价,就是让其他人为他的各种目的服务。
韦恩斯坦在长达五十年的颁奖礼上,与上帝收获了同等数量的感谢。而在年复一年的观众席上,坐满了像他这样行使权力的大亨、借他之力攀爬的上位者,还有迫于他威势而屈服的受害者。人人都爱电影,但她们或许更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爱。
韦恩斯坦的落网,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它所吁求的,恰恰是好莱坞的系统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