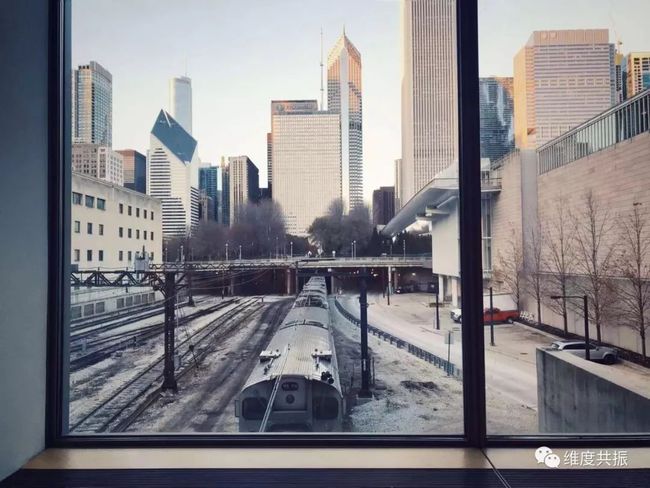“它拥有光和影,但它的光不刺眼,他的黑暗有着鲜明的轮廓。”
——费卢西奥·布索尼《关于莫扎特》
提及莫扎特,许多人眼前浮现的,也许是文艺复兴教堂壁画上小天使的天真模样。莫扎特给人的初步印象,华丽,诙谐,清亮,无忧无虑,不带任何阴郁哀伤的情绪——仿佛,他是永恒普照的阳光。
可是,莫扎特就是莫扎特。天才,也有着与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莫扎特的钢琴幻想曲。
记得第一首听的是《D小调幻想曲》(K397)。与往日印象中他活泼诙谐风格大相径庭,初听之时,我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莫扎特的作品。
微弱的琶音从低音最深处缓缓爬上来,触及到了高音再缓缓地退回去,像夜晚的海浪在黑暗中此起彼伏的呼吸,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稍稍沾湿了沙滩的边缘,又悄悄地退回,就这样默默重复着。
又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杵着一根弯弯曲曲的拐杖,独自一人迟缓的走在空荡荡的小巷里。深秋的梧桐叶铺满了小巷,老人踩在厚厚一叠的落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夕阳西下,他身后的影子越拉越长,余晖给他的拐杖,白发,布满皱纹的脸和双手染上了金色。
在几段琶音的酝酿之后,最后一个琶音似乎是犹豫着,试探着,爬上了高音的顶尖,在高处轻轻舞动着,愈来愈缓,愈来愈轻,直到那最高处的分解和弦像海市蜃楼一般一点点地消失在海与天的交界处,消失在寂静无声的黑夜里,消失在小巷的深处。
寂静几乎持续了数秒,忽而,高音处的琴音再次响起,或许是与寂静形成的对比,或许是音域的高与音色之轻的反差——那一音好似划破夜空的一颗流星,静悄悄,却又璀璨地落在沉寂的大地上。主旋律在同为高音域的伴奏下,被衬托得更为梦幻,它的脚步不再彳亍,伴随着缓慢却有规律的节奏,自由地在空中轻盈跳跃着。
继而,几个下降的强音突然打破了这片宁静,躁动不安的音符突然闯入。
一切宛如一个沉浸在回忆往昔的梦里,正要融化在曾经美好岁月里的人,下一刻天猛地一黑,他突然意识到,那些人,那些事,已经离开很久很久了。
惊醒了的他回味着已经在记忆里渐渐褪去色彩的梦,在短暂的反复之前那段温柔的旋律之后,一个飞快的急板音阶从高音飞流之下再一飞冲天。反复了之前强音开头的旋律之后,一个更广阔的急板音阶直入,再以一个半音阶从低处爬上来,接着又是那段梦境似的旋律……他似乎在和内心的矛盾作斗争,在冷冰冰的现实与梦幻里温暖的回忆里来回挣扎着。
最终,莫扎特没能将这首幻想曲写完,后世音乐家根据自己喜好给它谱写了结尾。然而,在我看来,它的精髓依然仅在于前面忧郁的小调穿梭于梦幻与阴郁的对比变换,对矛盾和挣扎心理如此细腻的刻画,温柔得那么脆弱,痛苦得那么深刻。
如果说,D小调里莫扎特描绘出梦幻的若即若离,那么他的另外两首C小调幻想曲(K396,K475)就将这种挣扎的情绪毫无保留地推向了高潮。
在K396中,连续近五分钟华丽的琶音结合着装饰音与颤音的缠绵之后,飞速的连奏猝不及防地划入,歇斯底里地奔腾着——它不像柴可夫斯基式忧郁的抒情,也不像贝多芬怒吼般的控诉——它是畅饮的狂欢里永远不会喝干的酒杯,是用之不竭却不会被拼命榨取的力量——莫扎特的宣泄是磅礴的,却也是节制的。
另一首K475中的对比更为鲜明。开始的很长一段里,迟缓得近乎沉闷的柔板里,偶然间几个跳动的音符,像是夹缝里透过的若隐若现的光亮,继而又消失在纯色的背景里。
然而,低重音和弦突然响起,仿佛一道闪电划过,如触电了一般的快板把之前的宁静全然打破,近乎挣扎颤抖着的八分音符撕破了岁月静好的景象,继而又像D小调幻想曲一样——与之前的梦幻一直交替着,矛盾地来回穿梭着,一瞬间直入青云,一瞬间又跌入低谷。
一生中仅有的三首钢琴幻想曲,将天才忧郁彷徨的一面叙述得淋漓尽致。
听惯了莫扎特活泼明朗的大调,听着忧郁的小调幻想曲,我倍感揪心——在“永远普照的阳光”背后,他也有自己的消极颓唐,也有复杂矛盾的情绪。
“他的灵魂纯净,但不漠然。
“他从来不简单,但也从不变得诡谲。
“他充满性情,但从不紧张。
“他是从不离开尘世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从不粗鄙的现实主义者。
……
“他没有鬼气或者超自然气息,他的现实主义是尘世的。”
之前写到过,莫扎特的音乐之纯净,以至于他的奏鸣曲,只有老人和小孩能够弹好。
这种近乎透明的音符质感,甚至让其作品成为众多钢琴家“最为望而生畏的艰难曲目”。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对此评论道:“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对于初学者太简单,对艺术家则太多困难。”
成熟了的演奏家放下心中的种种纠结杂念,抛离用指尖将音符戏剧化处理的习惯,返璞归真地演绎重现出莫扎特的纯粹,才是难度所在。
或许,这三首乍听几乎“不像莫扎特的”的幻想曲,是我开始真正喜欢莫扎特的理由。
近乎反常的风格,使我在那一刻受到了巨大的触动——我意识到,莫扎特,不只是世人眼里的天才,莫扎特的音乐,也不只是音乐。
《莫扎特传》中,萨利耶里因莫扎特的才华痛苦,嫉妒,却又无可奈何:“一页接着一页,好像他在听写一样。”
然而,萨利耶里或许没有明白的是,莫扎特的创作,不仅得益于上帝赐予的才华,更是源于他那颗一尘不染的真心。
莫扎特,没有乏味的教化,没有竭力的抗争,他是不带任何目的与方向创作的纯粹游戏者。
他的作品里不带有任何杂念,是最纯粹的叙述与抒发。
他的音乐表达了一种恰到好处的自在与安详,使失眠者安然入睡,使焦虑者愁绪散去,使倦怠麻木者清醒,使犹疑者果断。
艺术和消费品的差别,大概就在于这里吧。
只有用真心创作出的,才有可能被称之为艺术,才有可能跨越了时空触动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人。而一味迎合外界目光的产物,最多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娱乐产物——去芜存菁,才有孕育艺术的可能。
打动人心的,是澄澈的灵魂,是纯粹的人性,是真实。
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说过:“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再坚持练习,你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大提琴家。”
“他自己拥有各种性格,但只会担当叙述者和描绘者。”
“他给出答案,同时给出谜语。”
其实每个人都拥有各种性格,都可以担当叙述者和描绘者。可惜大多数人的灵魂负重累累,从胡乱挣扎的迷茫,直接跳跃到了不假思索的麻木。
我们潜移默化地,却又无可奈何地被世界改变着,在他人的目光里,慢慢把自己塑造成了被期待成为的模样,并不断安慰着麻痹着自己,这就是真实的自己。
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被一点点否定掉,人格也变得越来越单一,扮演的角色也逐渐固定,你继续安慰自己,这就是你在这个世界找准了的位置——铸造一个安全的躯壳,钻进去,躲起来。
康德说过,人,应该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可是,太多人把自己当作了手段,稀里糊涂地,在一片混沌中活着。
能打动人心的纯粹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却是流水线上的复制品。
“到处都是庸才。我代表全世间所有的庸才,宽恕你们的罪。”
在《莫扎特传》结尾,萨利耶里坐着轮椅被推去吃早餐,穿过精神病院的长廊,萨里耶利突然开始对路过的精神病人说话,又或许是自言自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长廊两侧精神病人们举止紊乱神情呆滞,疑惑地看着萨里耶利如同神父般地路过,并“宽恕庸才的罪过”。
此时此刻一副如此拧巴而诡异的画面,却配上了莫扎特《第二十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浪漫舒缓的音符倾泻而出,恬静又美好。
莫扎特 第二十号钢琴协奏曲 第二乐章
萨里耶利释然地仰起头,配着这纯净清澈的旋律,空中竟再次响起了电影中出现无数次的莫扎特魔性的放声大笑。
就像我之前《莫扎特传》影评里写道的:
无论是萨里耶利的嘲讽般地“宽恕”,精神病院作为的背景,莫扎特恬静的浪漫曲,还是最后那无比有穿透力的笑声,将一个天才对世俗的不屑嘲弄刻画到了极致——庸才如何地羡慕妒忌,奋力追赶,内心痛苦,彷徨,纠结,阴暗,污浊,这些统统与莫扎特无关——他的音乐就在那里,他不去理会世俗的浑浊,干净纯粹得那么持之以恒。